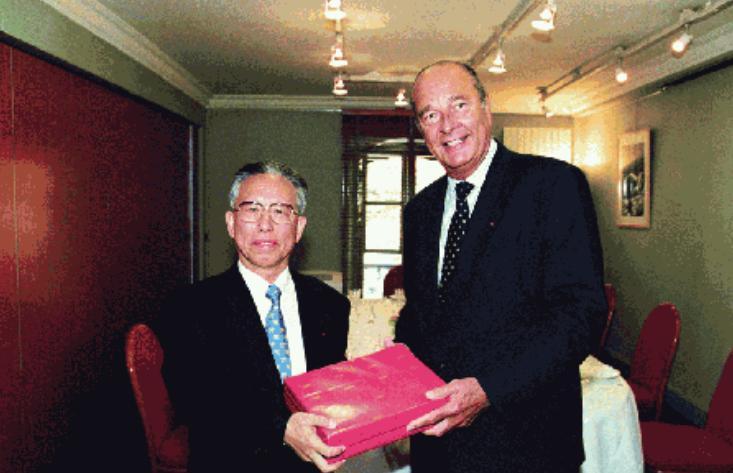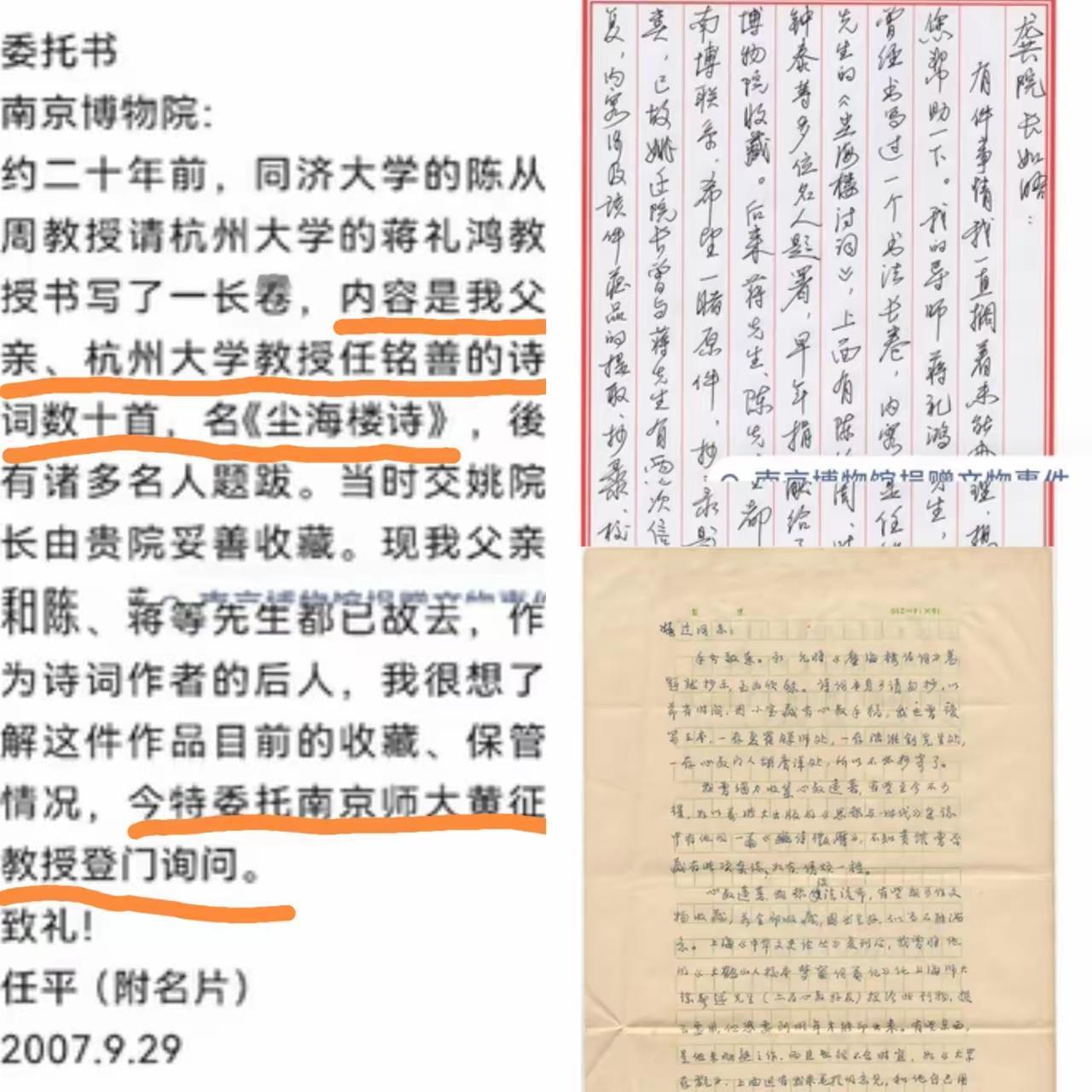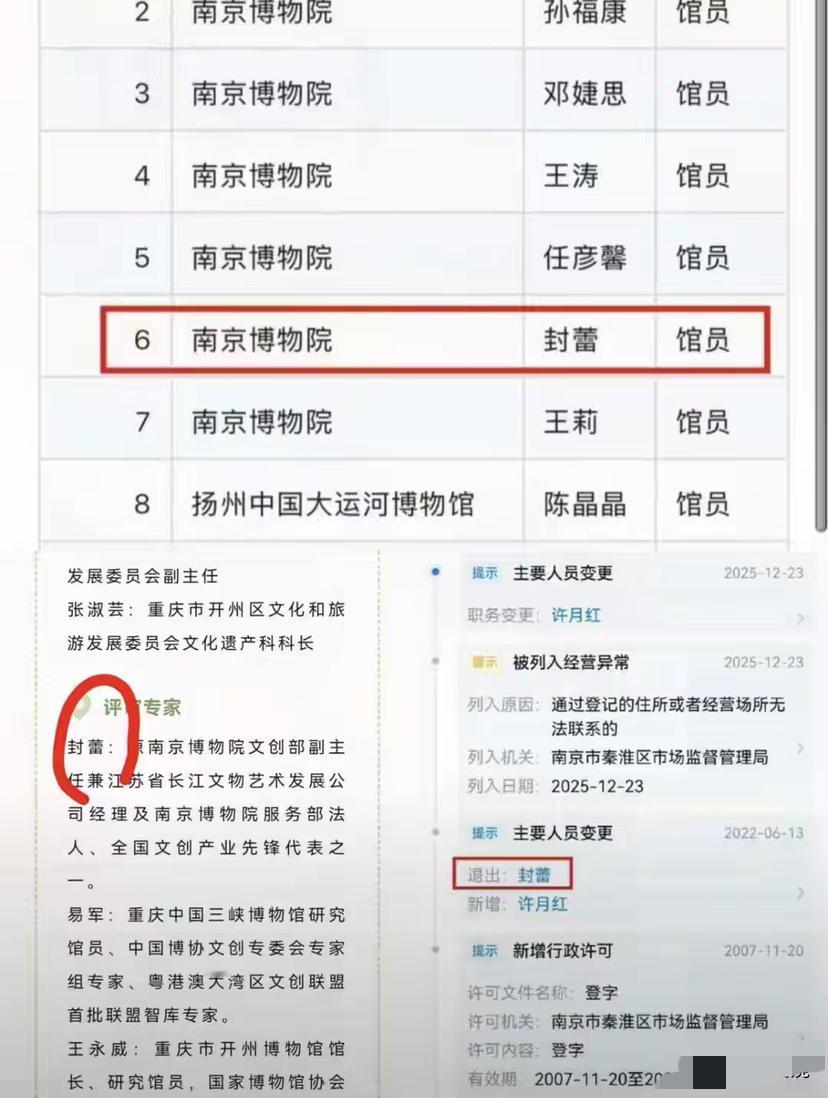1990年,马承源在香港的一家古玩店闲逛,看到角落里有一套青铜编钟。马承源问价,店主暗喜,直言道:“六万港币,你要的话五万。 九十年代的香港古玩市场,当所有专家和行家都在对着角落里那堆青铜疙瘩摇头嗤笑时,他们眼中的“嘲点”出奇的一致:这上面的铭文是“刻”上去的,按照那个年代考古界和学术界公认的知识体系,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只能是范铸成型,根本不可能出现刀刻技术,毕竟“西周无铁”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历史定论。 要在坚硬的青铜器上行云流水地刻字,没有高硬度的钢铁刻刀绝无可能,在行家眼里,这种“低级常识错误”简直就是造假者没做功课的证据。 偏偏就在这满场的嘲弄声中,马承源蹲下了身子,他透过那一层厚厚的灰尘与泥土,不仅隐约辨认出了“晋侯”二字,更捕捉到了一个常人难以察觉的逻辑悖论。 他上手敲击,那音律宏亮、纯正,严丝合缝地遵循着西周礼乐的规制,这正是最吊诡的地方:如果这是一个能将青铜冶炼和音律掌握到如此炉火纯青地步的顶级造假高手,怎么可能在“铸字还是刻字”这种连刚入行的学徒都懂的基础常识上犯错?除非,那个被所有人奉为真理的“常识”,本身就是错的。 这种反直觉的判断让马承源心跳加速,他深知这极可能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惊天发现,但在当时的场景下,表现出过度的狂热是古玩交易的大忌。 店主眼见马承源对这堆“废铜烂铁”感兴趣,心中暗喜,甚至主动从六万港币往下压价,殷勤地表示五万也能出手,只想把这堆占地方的东西赶紧甩出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行的朋友范季融,出于保护老友名声和钱财的初衷,他低声劝阻,生怕马承源打眼吃亏。 但马承源没有退缩,那种甚至可以说是“固执”的态度主导了这场交易,他甚至不敢过多还价,反而显出一种生怕店主反悔变卦卖给别人的急切,当下就要立字据留货。 正如预料的那样,这套编钟回到上海博物馆后,迎接它的不是鲜花,而是学界更为猛烈的质疑风暴,直到那通拨往北京的越洋电话被接通,真相的拼图才扣上了最关键的一角。 电话那头是正在主持山西晋侯墓地发掘的考古泰斗邹衡,马承源甚至还没来得及细说受到的委屈,只提到了编钟铭文讲的是“晋侯稣”追随周厉王征讨东方,且故事没讲完就突然中断了。 这个细节让邹衡在那头瞬间呼吸急促——原来,山西的考古现场刚刚遭遇过惨痛的盗墓洗劫,墓室大件已被搬空,只在泥土深处遗漏了两枚体型极小的编钟。 而那两枚残存的小钟上,刻着一模一样手法的铭文,且恰好也是没有开头! 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十四件大钟,与山西出土的两件小钟,无论在纹饰氧化程度,还是那曾经被视为“伪造罪证”的凿刻痕迹上,完全严丝合缝,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十六件编钟。 原本中断的铭文此刻连缀成篇,整整355字,详细记录了一场被历史遗忘的战争。 这套“晋侯苏钟”的问世,如同一声惊雷,不仅彻底洗清了马承源的“冤屈”,更狠狠修正了僵化的历史认知。 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凿刻痕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的冶炼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可以使用钢铁工具在青铜上刻字的高度,这一发现,直接将我国的钢铁冶炼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五百年。 信息来源: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