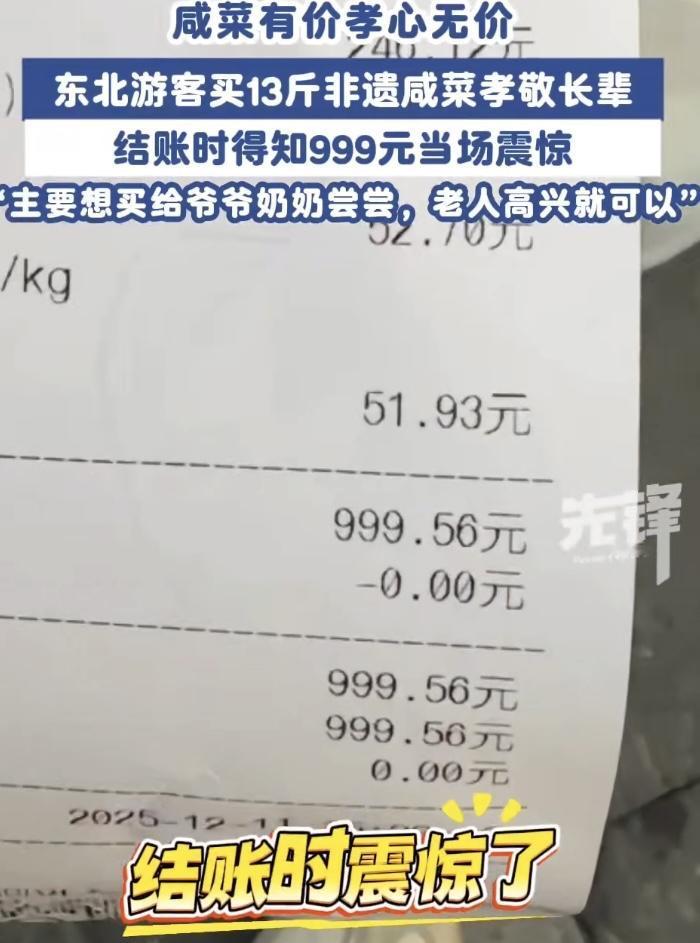我母亲的嘴巴,真紧啊。那一年,我十一二岁,有一天,母亲带我去镇上吃席,回来晚了。夕阳把路两旁的白杨树染成金红色,母亲牵着我的手,步子迈得比平时快。她藏在袖管里的手攥着个油纸包,里面是宴席上打包的肉丸子,油汁把纸洇出深色的印子。 我母亲的嘴巴,真紧啊。 十一二岁那年,镇上表姑家办喜事,母亲带我去吃席。散席时天都擦黑了,夕阳把路两旁的白杨树染成金红色,叶子在风里哗啦响,像谁在小声说话。 母亲牵着我的手往家走,步子迈得比平时快。她的手有点凉,掌心却汗津津的,我挣了挣,没挣开——后来才知道,她另一只藏在蓝布袖管里的手,正攥着个油纸包。 那纸包不大,方方正正,边角被油汁洇出一圈深色的印子,隔着布料,我都能闻到肉丸子的香。是宴席上最后那盘没吃完的四喜丸子,我亲眼看见母亲趁人不注意,拿干净的荷叶饼包了两个,又裹进油纸里,塞进袖管,动作快得像偷东西。 我当时没敢问。母亲脾气不算温和,却极少在外面红脸,那天她为什么要做这种“小气”事?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她才停下来,左右看看没人,把油纸包掏出来。纸已经被手汗浸得有点软,她小心地剥开,两个圆滚滚的肉丸子躺在里面,油光锃亮,还冒着热气。 “快吃。”她把丸子塞我手里,自己背过身去,对着槐树站着,肩膀轻轻晃了晃——后来我才明白,她是怕我看见她眼里的红。 那天的肉丸子真好吃啊,猪肉馅里混着马蹄碎,咬一口会流油,咸香里带着点甜。我吃完一个,把另一个递到她嘴边,她却摇头,“你吃,我在席上吃撑了。” 可我明明记得,她那天几乎没动筷子,光是给我夹菜,自己只扒拉了半碗白米饭。 你说,大人是不是都这样?把难嚼的日子自己咽了,把甜的都包起来,塞给孩子,还嘴硬说“我不爱吃”“我吃过了”。 后来家里条件好起来,我也带母亲去城里下馆子,点一大桌菜,特意给她点四喜丸子。她夹起一个,咬了一小口,慢慢嚼着,突然说:“还是那年你表姑家的丸子香。” 我没接话。夕阳把白杨树的影子拉得老长,金红色的光落在母亲的发梢上,也落在她牵着我的那只手上——那只手平时总在灶台前忙碌,指节上有常年洗菜留下的薄茧,此刻却把油纸包攥得格外小心,好像里面装着什么稀世珍宝。 现在想起那天的路,夕阳是暖的,母亲的手是暖的,连那油纸包上洇开的深色印子,都像一颗心——不说话,却跳得很用力。 母亲的嘴巴是紧,可她的爱啊,早从那油乎乎的纸缝里,漏了一路。
外婆很聪明,这六个子女里,她偏偏认准了最闷葫芦、性子最温吞的三舅养老,一头扎进了
【3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