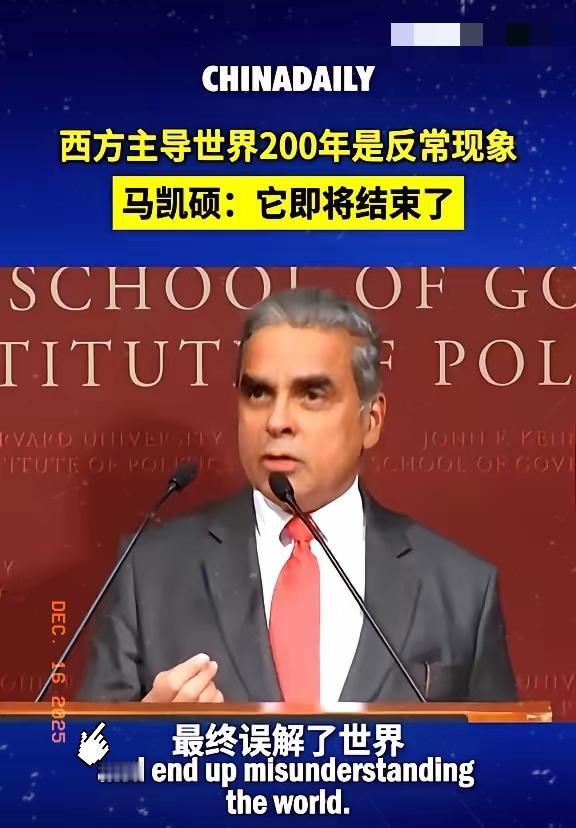我爸今天晚上跟我商量,他跟我妈年龄大了,想把他手上的钱给我姐俺两分了。我爸手上也没多少钱,有个十来万,他今天晚上跟我商量,想把这钱给我姐我们两个分了。他跟我妈他两今年70多了,不再种地后就靠着养老金和之前攒下的这点钱过日子,平时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晚上七点多,客厅的灯刚换了瓦数低的节能灯泡,暖黄的光落在爸的老花镜上,镜片反射出桌上搪瓷杯的影子——那杯子沿儿磕了个豁口,是他用了十五年的“宝贝”。 妈在厨房刷碗,水流声混着她哼的老调子,爸突然朝我招招手,“过来坐,跟你说个事。” 我挨着他坐下,他没看我,手指在搪瓷杯把儿上磨来磨去,磨得那层掉了色的蓝漆更显斑驳。“我跟你妈,”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比平时低半度,“这几年没再种地,手里攒了点钱,不多,也就十来万。”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他要问我是不是最近手头紧——上个月我换工作,他打电话时反复问“钱够不够花”。 “我跟你妈商量着,”他终于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露出那双浑浊却亮的眼睛,“这钱放我们这儿也是放着,你跟你姐俩,一人分一半,拿着。” 我盯着他手背上暴起的青筋,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他感冒不肯去医院,说“扛扛就好,省点钱给你姐娃买奶粉”,现在怎么反倒要把养老钱拿出来? “爸,你们留着啊,”我声音有点发紧,“养老金够花,你们自己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你那件棉袄都洗得发白了。” 他摆摆手,手背上的老年斑跟着动,“买啥新衣服,旧的穿着舒服。我们都七十多了,留着钱干啥?你们年轻人压力大,房贷车贷孩子学费,哪样不要钱?给你们,我们才安心。” 妈端着碗出来,接话时围裙还没解,“就是,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过得好,比啥都强。”她笑的时候眼角堆起皱纹,我才发现她鬓角的白头发又多了些,像冬天落在枝桠上的霜。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搪瓷杯往他那边推了推,杯底和桌面碰出轻响。那杯子里的茶早就凉透了,可我突然觉得,那点凉意在心里烫得慌。 后来我给姐打电话,她在那头哭了,说上周回家看见妈偷偷补袜子,袜底破了个洞,用同色的线绣了朵歪歪扭扭的小花。“咱爸咱妈啊,”姐哽咽着,“一辈子都在为咱们活。” 第二天我没提分钱的事,只是拉着爸去了镇上的服装店,给他挑了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妈一件红色的。爸试穿时胳膊抬得有点费劲,却一直咧着嘴笑,说“这衣服真轻快”。 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说:“其实那钱,我们存着也是想给你们应急。现在看你们好好的,比拿多少钱都高兴。” 我看着他走在前面的背影,背有点驼,步子却稳,像株在地里扎了一辈子根的老玉米,风里雨里都站着,却把最饱满的穗子全留给了身后的人。 晚上客厅的灯还是暖黄的,爸的搪瓷杯里泡了新茶,热气裹着茶香飘起来,模糊了他的老花镜。我突然明白,有些爱从来不用讲,就像这灯光,不亮,却够照亮往后所有的路。
我堂哥在巴基斯坦打工那会儿,稀里糊涂就跟当地一个姑娘好上了。哪知道姑娘全家知道后
【5评论】【1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