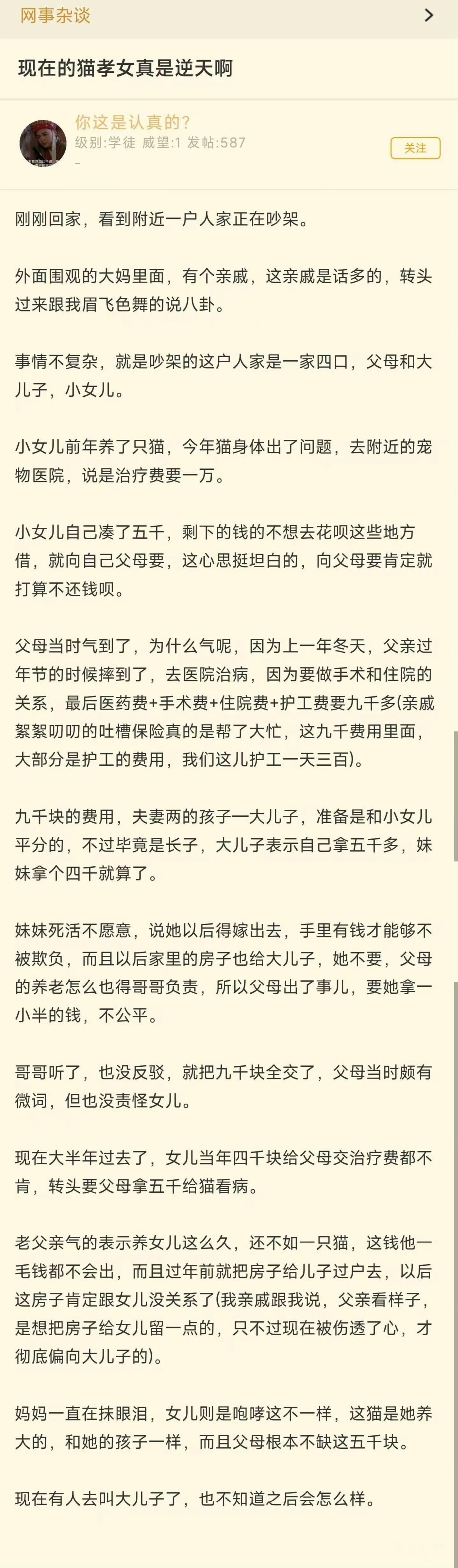我是姑姐,我结婚的房子全款买的,娘家拿了一半的钱,又出了家电家具,结完婚我把房子租出去收租,带着对象去娘家住,这一住就是十二年,期间生了俩孩子,我妈不工作了专门给我看孩子,娘家还给对象扶持一摊生意做,在娘家住油盐酱醋水电费都不花钱。 那年结婚,房子是全款买的。 娘家掏了一半积蓄,又拉着板车去家具城,把冰箱彩电洗衣机一件件搬上楼——那房子朝南,阳光好,租给小夫妻时,我特意留了主卧的窗帘,是妈妈挑的米白色,说遮光好,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我以后回去住不惯。 签完租房合同那天,对象拎着行李箱站在娘家楼下,搓着手问:“住这儿,会不会给咱妈添麻烦?”我拍他胳膊:“妈早把次卧收拾出来了,连你爱吃的辣椒酱都备好了。” 头一年住得拘谨。 我抢着洗碗,他抢着拖地,妈妈总把我们往客厅推:“去陪爸看电视,厨房油大。”直到某天我起夜,看见她蹲在阳台,借着月光缝我掉了扣的睡衣,针脚歪歪扭扭,像她年轻时给我织的毛衣。 第二年老大出生,是个爱哭的丫头。 妈妈把广场舞鞋收进柜子最底层,系上围裙就成了孩子的专属保姆——白天喂饭换尿布,夜里听见哭声比我还先坐起来,有次孩子闹肚子,她抱着在客厅来回走,凌晨三点还在给额头擦温水,我迷迷糊糊醒来时,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比孩子的哭声还让人心疼。 对象那时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没本钱,爸把存了大半辈子的定期取出来,又托老战友找场地、办执照,跑前跑后瘦了五斤,却在饭桌上笑着说:“年轻人就得闯,亏了爸给你兜底。” 这一住,就是十二年。 客厅的沙发换了三次,第一次是布艺的,被孩子用彩笔画得五颜六色;第二次是皮质的,被老大骑坏了扶手;现在这个是实木的,妈说“结实,能用到孙子娶媳妇”。 油盐酱醋从没让我操过心,每次打开厨房的抽屉,盐罐永远是满的,酱油瓶的标签朝外放,连洗碗布都挂在固定的挂钩上——那是妈十几年的习惯,她总说“顺手的事,不用记”。 去年冬天妈体检,医生说她腰椎不太好,不能总弯腰。 那天晚上我把孩子哄睡,悄悄去她房间,看见她正揉着腰看相册,里面是我结婚时的照片,她站在我旁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头发还是黑的。我突然想起,这十二年,她没买过一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却每年记得给我和对象买保暖内衣,说“贴身的得买好点”。 有人问过我:“在娘家待这么久,不觉得别扭吗?” 我指了指阳台晒着的被子——有我的碎花被,对象的格子被,两个孩子的卡通被,还有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被,它们并排晾着,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个个圆滚滚的拥抱。 其实哪有什么别扭,不过是她把“女儿的家”,过成了“自己的日子”。 上个月给妈买了个按摩仪,她嘴上说“浪费钱”,却每天晚上都用,还在家庭群里发消息:“按摩仪很好用哦,谢谢我闺女。”后面跟了个龇牙笑的表情,像个得了糖的孩子。 昨天老大放学回来,举着满分的试卷冲进厨房:“外婆外婆,你看!”妈正在炒我爱吃的西红柿炒蛋,锅铲停在半空,围裙上沾着点点番茄酱——还是那件旧围裙,边角磨破了,我好几次说给她换,她都摆手:“不用,这围裙吸油。” 油烟机嗡嗡响着,孩子的笑声混着鸡蛋的香味飘出来,我靠在门框上想:这十二年,到底是我赖在娘家不肯走,还是妈早就把我们的三餐四季,织进了她的岁月里? 或许,家人之间从来就没有“该与不该”,只有“愿意与值得”。 今晚我来洗碗吧,让妈也能在沙发上追两集电视剧,像她年轻时那样,脚翘在茶几上,磕着瓜子,不用惦记锅里的汤有没有熬好,不用操心明天孩子穿什么衣服。 就这一次,让我做那个“顺手的人”。
装修不能找年纪大的师傅。阳台柜子,一边放洗衣机,一边水池,结果大爷夫妻两做成这
【2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