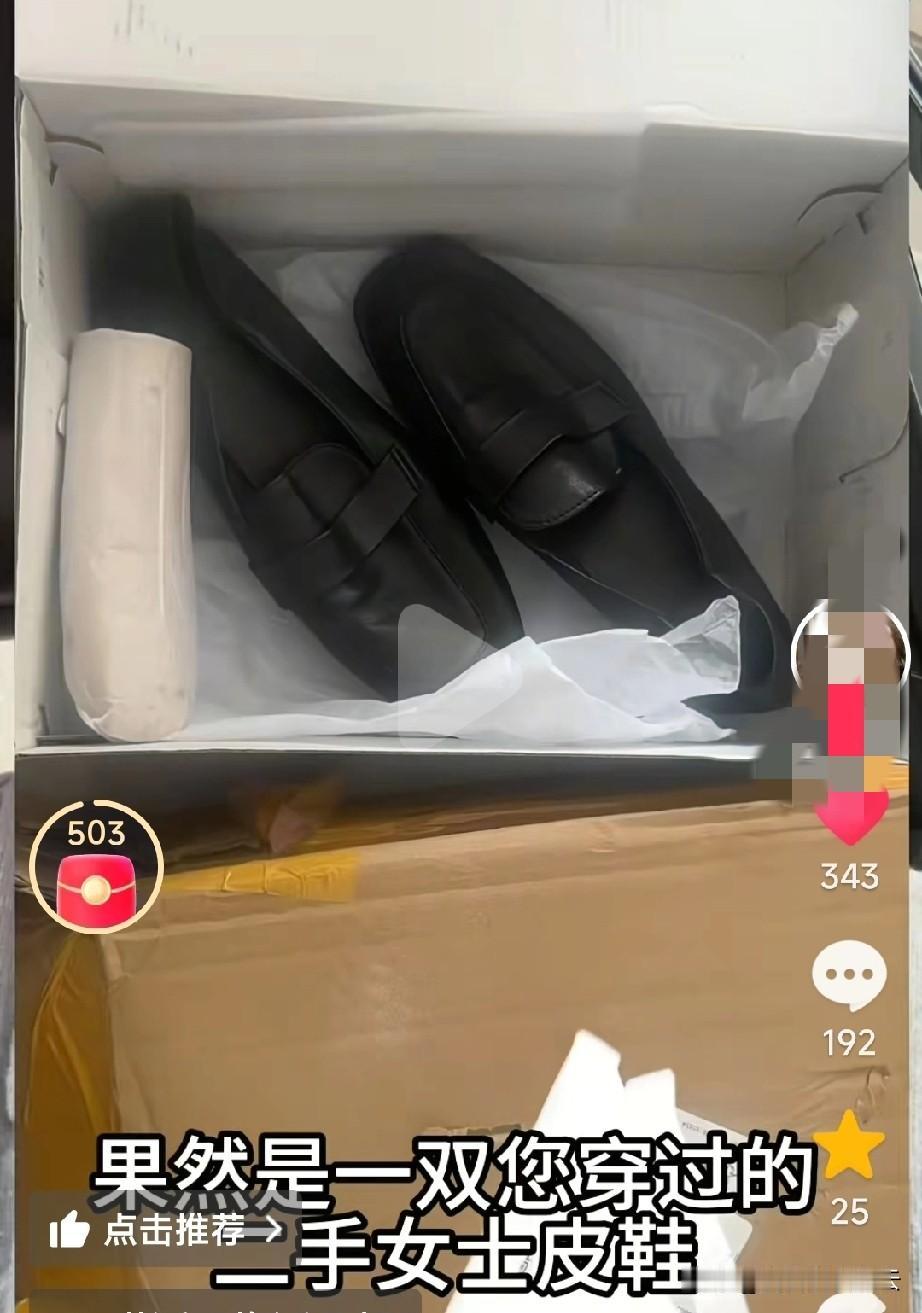1956年3月,山东临沂沂南县公安接到举报:有个卖烧酒和狗肉的老汉,经常在山里转悠,极为可疑。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56年春,沂蒙山的薄雾还没散尽,崎岖山道上便出现一个挑担老汉。 担子一头是封着红布的烧酒坛,一头挂着油亮的狗肉。 他走路不急不缓,却总在岔路口停下脚步,对着层叠的远山出神。 这般古怪行径很快引起村民警觉,消息传到乡公所时,公安员正泡开今春头一茬山茶。 三天后的晌午,老汉在青驼寺村外的老槐树下被拦住。 他安静地放下担子,从怀里摸出张泛黄的复员证。 公安员查验时,目光停在他脖颈下一道深褐色疤痕。 那是子弹擦过的印记。 掀开粗布衫,肋间、腹部的旧伤疤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老汉名叫郭伍士,山西人,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 他要找的是位救过他命的沂蒙母亲,只记得乡亲唤她“张大娘”,大约在桃棵子那片山坳里住。 1947年复员后,他放弃回黄河老家,用全部抚恤金置办这副货郎担。 九年里,担子换过三副草绳,鞋底磨穿十几双,把沂南大小山沟趟了不知多少遍。 这桩心事要回溯到1941年腊月。 那年扫荡来得急,郭伍士所在的侦察班在桃花岭遭遇日军。 为掩护电台转移,他引着鬼子往反方向跑,子弹追着脚后跟打进松林。 最后一颗子弹穿过腰腹时,他正扑向山涧。 醒来时天地素白,血在雪地上洇出朵硕大的山茶花。 他撕下绑腿扎紧伤口,朝着有炊烟的方向爬。 三里山路,从日头偏西爬到星子满天才看见村头那盏摇晃的风灯。 开门的是个绾髻的妇人,蓝布袄袖沾着玉米面。 那夜郭家土炕烧得滚烫,妇人用绣花剪子挑开冻在伤口上的军装,棉花和皮肉粘作一团。 她煨了花椒盐水,拿新棉布蘸着擦洗,每擦一下,昏迷的人就抽搐一下。 天亮前,村支书敲开木窗带来消息:鬼子在五里外扎营了。 藏身的地窖在红薯窖深处,入口掩着堆陈年麦糠。 郭伍士在这里躺了三十七天。 每天黄昏,地窖木板会掀开条缝,先吊下瓦罐小米粥,再是裹在棉絮里的草药包。 有回高烧说胡话,朦胧间看见妇人坐在地窖口,就着油灯挑他伤口里的脓。 那双手生着老茧,动作却轻得像羽毛拂过。 后来才知道,为找消炎的紫花地丁,她摸黑摔进沟里,左腿瘸了半月。 最险的是腊月二十三祭灶日。 一队伪军突然闯村搜查,脚步声停在红薯窖上方。 妇人突然放声哭骂,说自家腌的过年肉被黄鼠狼拖了,抄起烧火棍打得麦糠满院飞。 伪军啐着晦气离去时,几粒土坷垃正落在郭伍士额头上。 那晚的粥里多了指甲盖大的腊肉,妇人隔着木板说: “孩子,好好活着,等太平了给娘捎个信。” 这句承诺像种子埋进心里。 郭伍士伤愈归队时,对着土坯房磕了三个头。 此后的军旅岁月,他揣着这粒种子走过了鲁南战役、孟良崮硝烟。 直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花照亮北京城时,他在天安门广场的欢潮里想起那盏沂蒙山的油灯。 寻亲的第九年秋天,货郎担停在了桃棵子村石碾旁。 几个晒柿饼的妇人闲聊,说前庄张寡妇家来了外省亲戚。 郭伍士手一抖,酒提子“哐当”掉进坛里。 他沿着妇人指的方向跑,荆条筐滚下山坡都顾不上捡,跑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面前时,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老妇正在院里晒山楂片,听见动静转过身,眯眼打量这个气喘吁吁的外乡人。 “大娘,”郭伍士声音发颤,“您认不认得三十七年冬天,那个藏在红薯窖里的伤兵?” 老妇手里的笸箩“啪”地落地,山楂片滚了满地。 她踉跄上前,枯瘦的手抚上他颈间疤痕,眼泪滴在陈年旧伤上: “是虎子?伤在后腰的虎子?” 原来郭伍士昏迷时曾说梦话,念叨娘给取的乳名。 这声“虎子”像把钥匙,骤然打开时光锈锁。 当年英气妇人已成耄耋老妪,昔日重伤少年也染了鬓霜,只有那盏穿越战火的人性灯火,依然在岁月深处亮着。 郭伍士当真在桃棵子村住下了。 他把山西的妻小接来,在祖秀莲老屋旁起三间瓦房。 每天清晨,他挑着那副不再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一头装着赶集割的鲜肉,一头坐着嚷嚷要听故事的小孙儿,吱呀吱呀走向张寡妇家。 村里人都说,这家人比许多血缘至亲更亲。 1977年谷雨,祖秀莲在满堂儿孙环绕中离世。 七年后,郭伍士病重时,执意要葬在义母坟旁。 如今两座青石墓碑立在沂蒙山向阳坡上,一座刻着“慈母祖秀莲”,一座刻着“子郭伍士”,中间有棵山茶树,年年清明开得轰轰烈烈。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郭伍士:归来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