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位广西女子自称是毛主席的女儿,工作人员认为对方是骗子,毛主席却连忙表示:“让她来,我想见见她” 一九七三年,中南海门口来了个女人,带着广西口音,拎着个旧包,对警卫说自己是“主席的广西女儿”,要进去见毛主席。 警卫当场紧了神,这种认亲话谁都能说,照规矩先拦下再说。 她叫岑荣端,这话不是随口乱编。 几个月前,她从天山脚下和西湾河畔辗转写出一封信,托外交部的王海容转给毛主席,信里写着:“八年来,无论是在天山脚下,还是在西湾河畔,我都很想念您老人家,也非常想再见到您老人家……”最后落款:“您的广西女儿岑荣端”。 信送到八十岁的毛主席案头,他读完,想起的就是那个在舞池边上排队等他、身形敏捷的广西舞蹈演员。回信没有亲笔写,他把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赵淑琴叫来,让她给小岑写信,说主席请她春节来中南海做客,她爱人的家在北京,可以借探亲的名义进城一趟。 赵淑琴和岑荣端是老同事,常在中南海伴舞,很清楚两人的交情。 她在回信里转告主席的原话:“说你是他的广西女儿,等春节回北京探亲,就来中南海见他。”信一路转到广西,岑荣端拆开,心里那点“是不是被忘了”的不安一下就放了下来。 要弄清“广西女儿”几个字,只能把时间往前拨。 延安那阵子,干部们一天忙下来,人像绷紧的弦,有人提议晚上跳舞活动一下,这个习惯就一直保留下来,建国以后搬进了中南海。 院子不大,灯光一打,常见的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些身影。 陪他们跳舞的演员,每年从各文工团层层挑选,政审要过关,家庭情况也要清清楚楚。 一九三九年,广西贺县,一个农家生了个女儿,取名岑荣端。她爱看戏,台上转圈,她在台下学。十二岁时,广西第四十九军第一五四师文工团来地方挑人,看中了她,把她招进队伍,从此成了专业舞蹈演员。 抗美援朝战役爆发,上级抽人去部队当卫生员,她脱下演出服,换上白大褂,学打针换药,把对舞台的念想压到心底,那几年总觉得自己大概回不到灯光底下了。 一九五四年,一纸调令让命运掉头,她被调往沈阳空军文工团。 练功房里一排把杆,大家散场,她还在多压腿、练基本功。四年过去,她的名字出现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名单上,从地方进了北京,离中南海近了许多。 一九五八年的某个晚上,她第一次进中南海执行任务。 大厅里灯光柔和,刘少奇、朱德先到场。夜深一点,毛主席走进来,在场的人下意识站起身鼓掌,他摆摆手,让大家坐下,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歇气。 空政文工团的老同志把岑荣端领过去,介绍说是新来的,请主席一会儿同她跳舞。 毛主席点点头,人一散,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让这个有些紧张的广西姑娘坐下,问她是哪里人。听到“广西贺县”,他笑,说还是个“小老广”。再问名字,她怕“岑”听成“陈”“程”,干脆抓起他的手,在掌心写下“岑荣端”几个字。 毛主席看着这个生僻的姓氏,说百家姓里好像没有“岑”,又念了几遍她的名字,觉得“荣端”不太顺耳,就半开玩笑说,不如改成“云端”,像云一样。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后来真的把名字改成了岑云端。 乐队那边响起舞曲,两人走上舞池。 毛主席个子高,步子也大,她就悄悄把自己的步伐调快一点去贴合,从远处看还挺合拍。毛主席留意到了,觉得好玩,曲子一停,又问了几句广西老家和部队近况。 从那以后,她被点名进中南海的次数多了。 有时是舞会,有时是小范围联欢。 跳得久了,话也就多了,毛主席嘴里“广西女儿”的叫法越来越顺,这个称呼就这么落在她身上。 一九六六年,形势骤变,她离开北京,被派到天山脚下,又去了西湾河畔。岗位一换再换,信件少了,人心没断。 八年后,她写出那封信,把“天山脚下”和“西湾河畔”都写进去。 毛主席托赵淑琴回信之后,一九七四年春节,就有了中南海门口这一幕。 那天风有点冷,警卫看着她,自称是主席的广西女儿,脸上全是疑虑。她把情况一条条讲明,正纠缠间,赵淑琴从远处走来,一眼认出她,叫了名字。 警卫这才确认眼前人确实和院子里有关系,把门让开。 岑荣端走进屋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书。 有人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他抬头,笑着说:“我的广西女儿来看我了。” 临走前,她想约好下回见面的时间,毛主席说,三年来一次吧,工作忙,路也远。她摇头,说三年太长,不如一年一见。老人点头,两人伸出小指,在空中勾了一下。 一九七五年七月,她和赵淑琴按着约定再进中南海。 屋里光线有些暗,毛主席的身体已经很吃力,眼睛看人不太清楚,握手的力气也小了。 闲聊几句,他忽然提起两句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说,小岑、小赵是奇儿,自己老了。 她们怕耽误他休息,只待了半天就告辞。 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全国哀悼,广西派出首批民众代表赴京吊唁,代表里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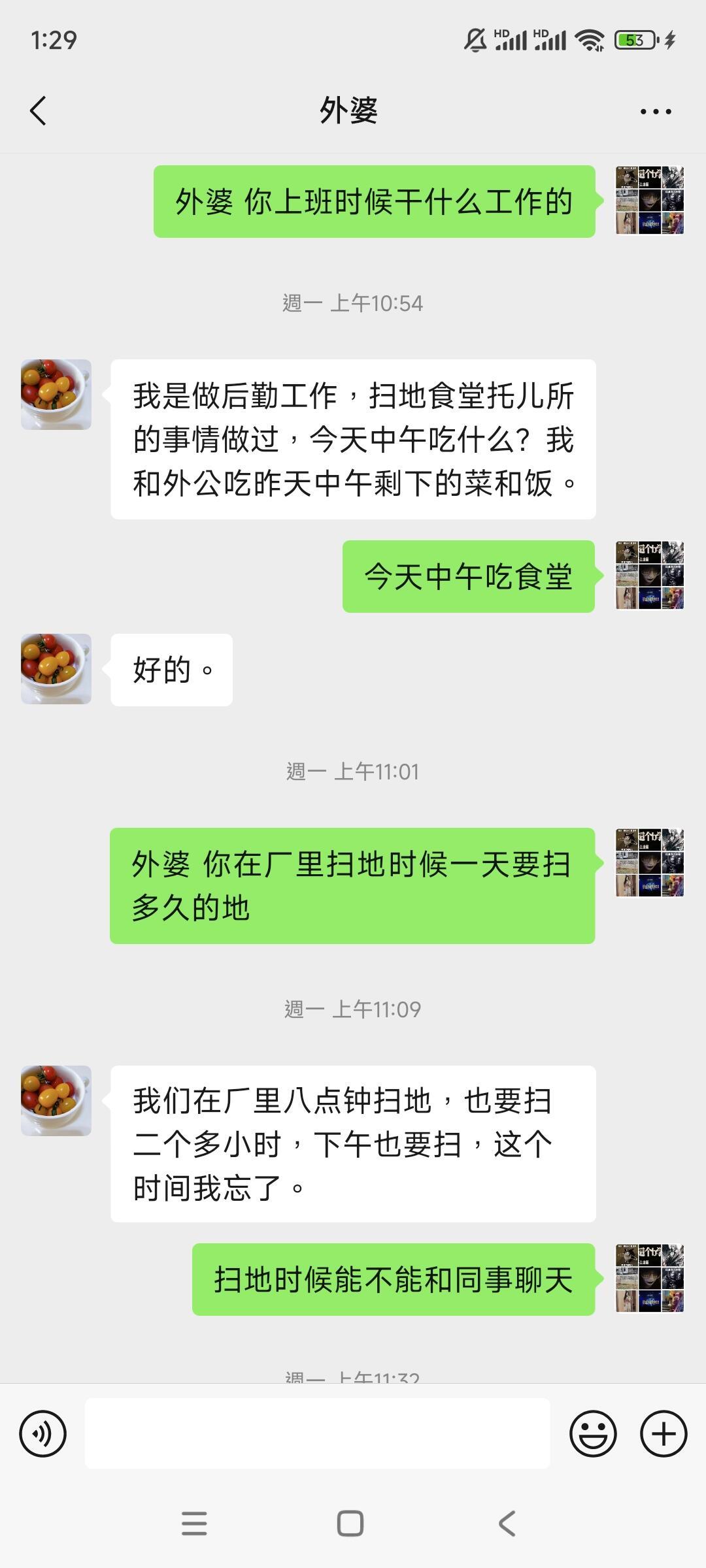



![[笑着哭]太有意思了近日,一广西小伙子被顾客整懵了,他家一大片柚子树,他直播卖柚](http://image.uczzd.cn/2847863593002038578.jpg?id=0)



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