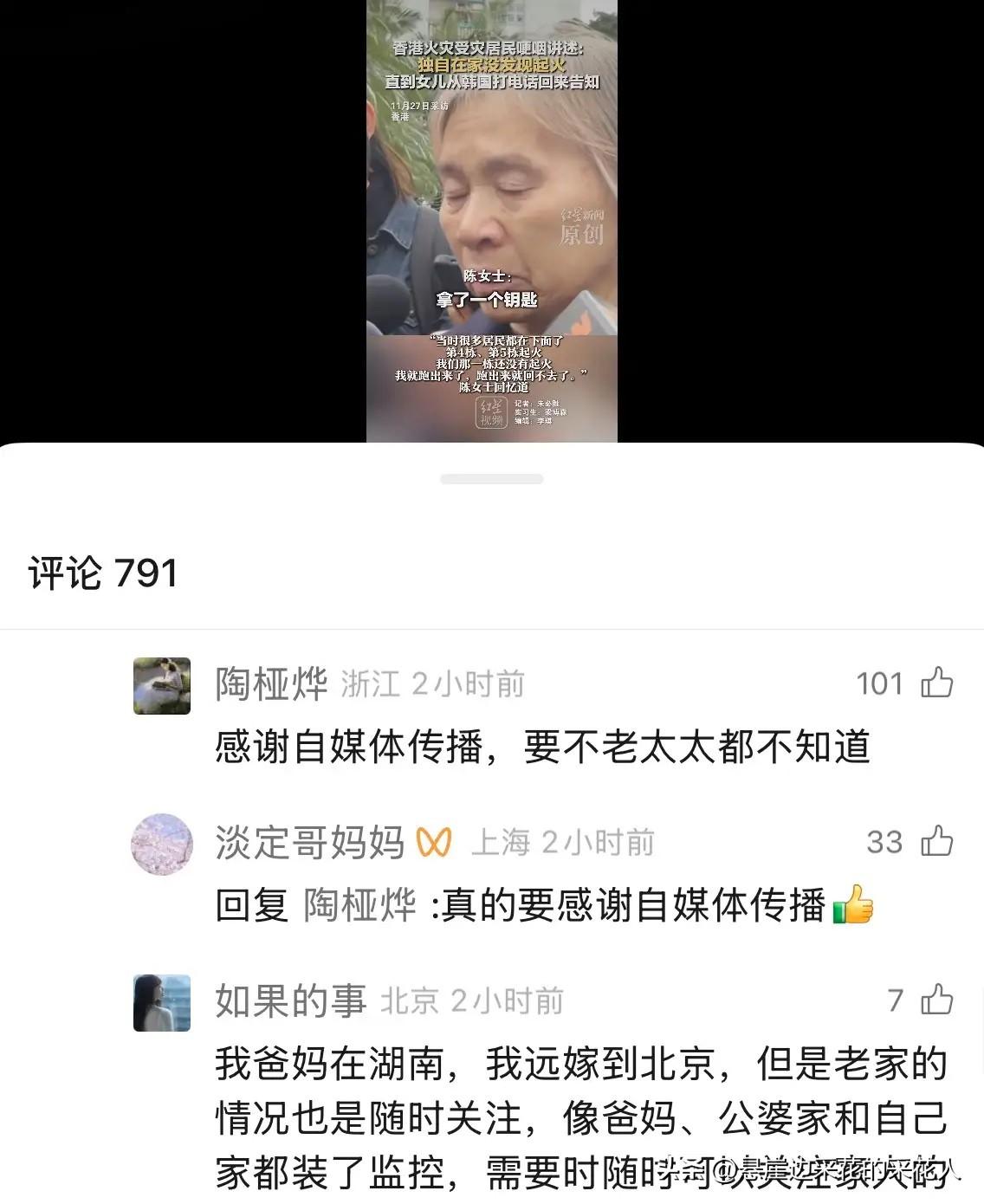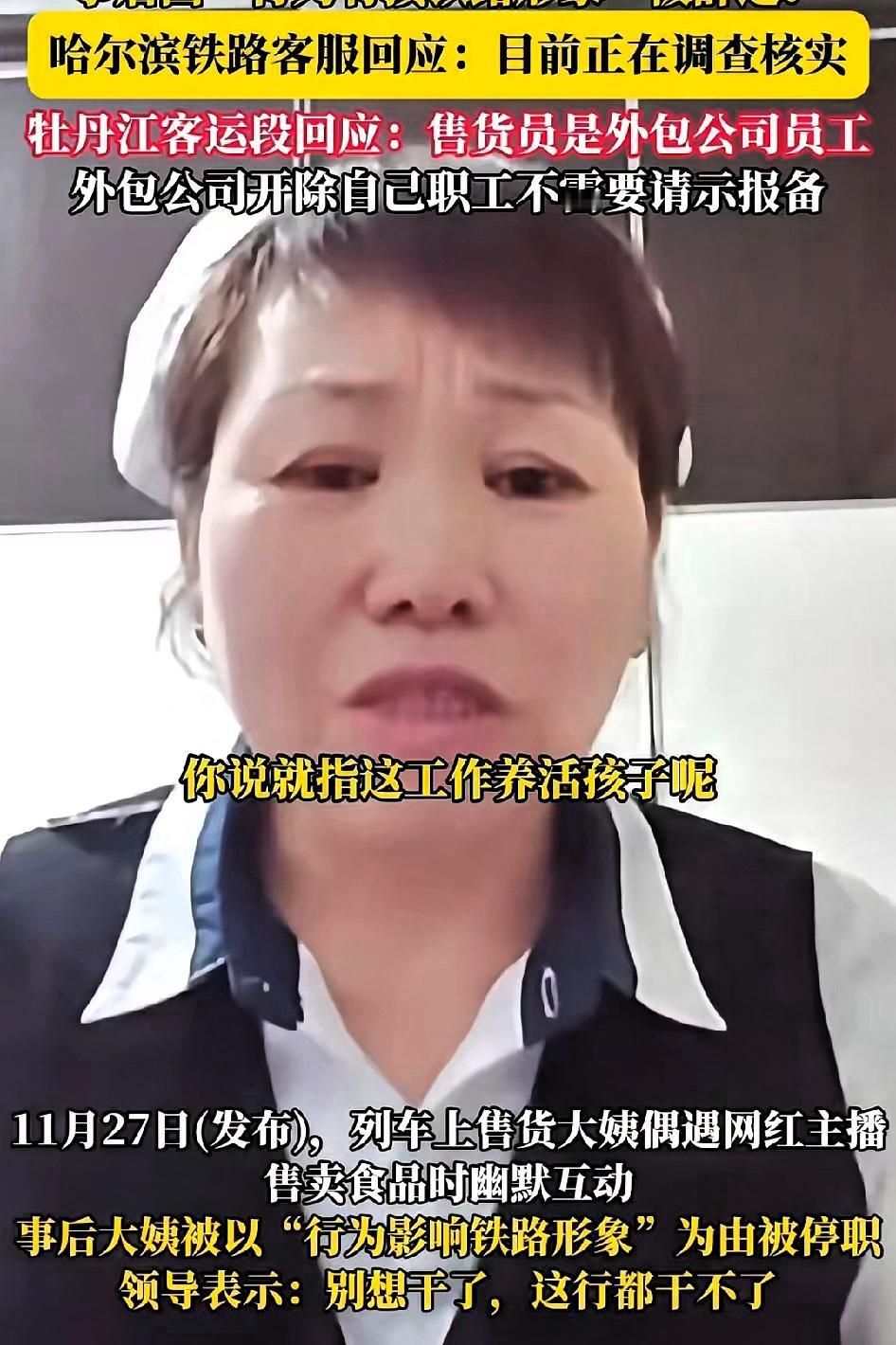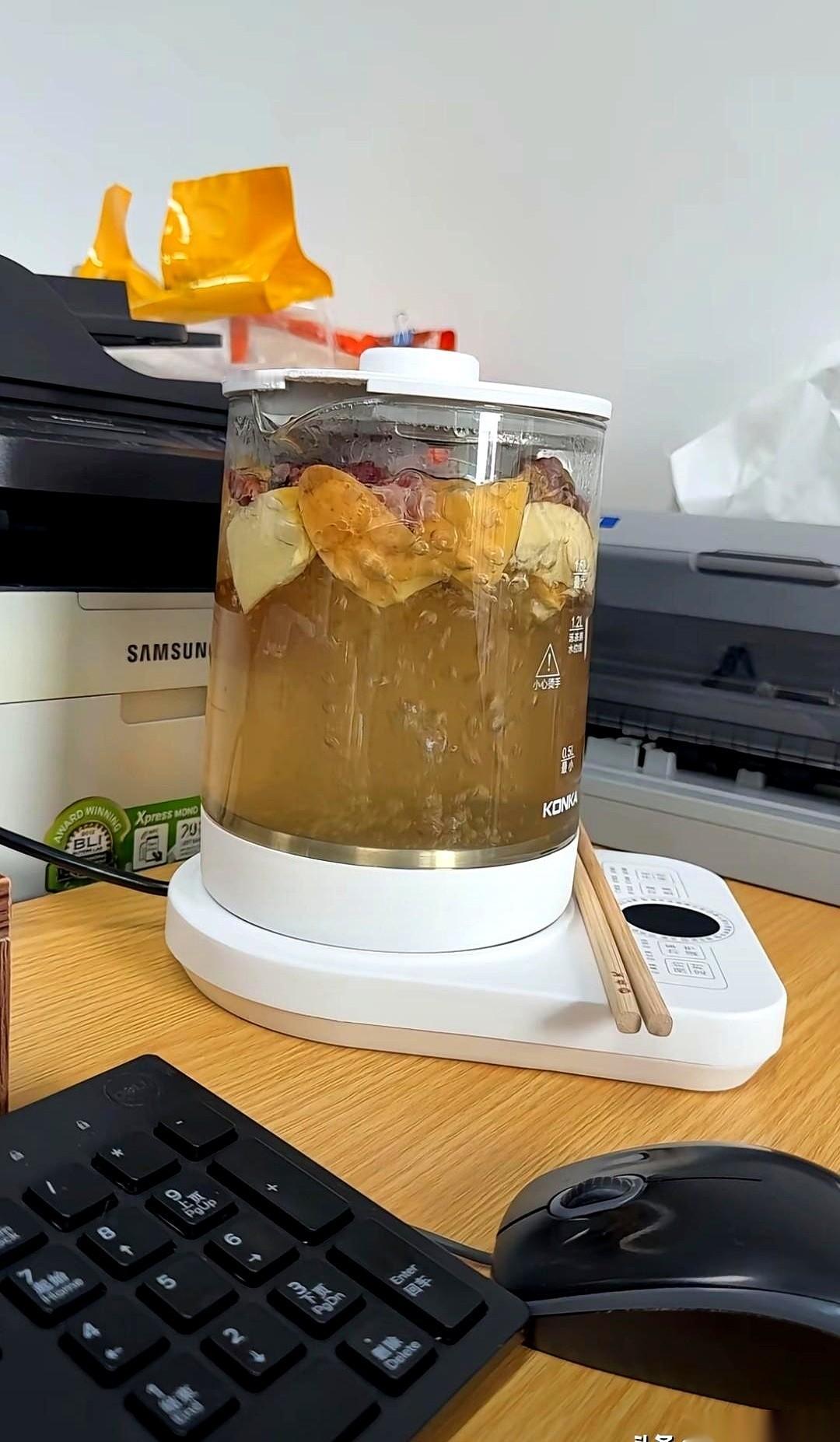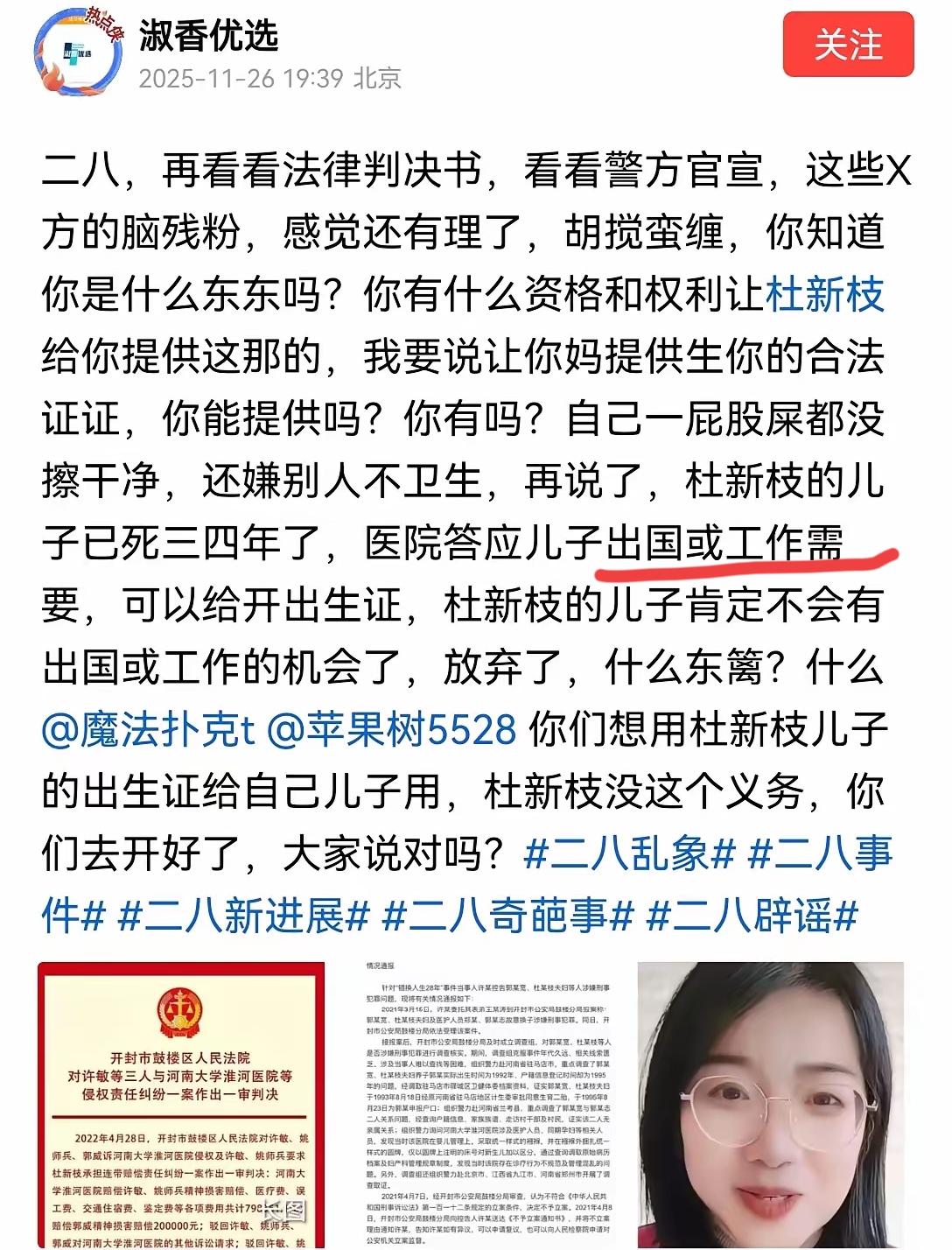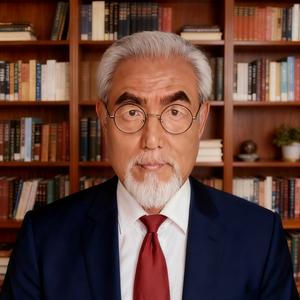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忆苦思甜 小时候上语文课,最难忘的就是那篇讲“粗粮麸子馒头”的课文。老师拿着泛黄的课本,一字一句地念着:“吃一口麸子馒头,就想起过去的苦;咽一口粗茶淡饭,就记着今天的甜。” 那时的我们,捧着白面馒头还嫌不够香甜,直到老师掰开一块黑乎乎、粗糙剌喉的麸子饼,让我们轮流尝了尝——满口的苦涩混杂着麦麸的粗糙,卡在喉咙里难以下咽,才隐约懂了课文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十个字的重量。 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的秋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农机厂的大俱乐部听老农民讲过去的故事。俱乐部里挤满了周边学校的孩子,长条木凳坐得满满当当,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机油味和秋日的桂花香。一位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的老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布包,慢慢走上临时搭起的土台。 他没带稿子,就坐在小马扎上,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把我们拉回了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那时候啊,地里长不出庄稼,老天爷不下雨,收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子。” 老农的声音沙哑却有力,“饿啊,是真饿!大人小孩都瘦得只剩皮包骨头,30多岁的小伙子,本该是能挑能扛的壮劳力,却饿到站都站不起来,扶着墙都走不动道。” 他顿了顿,指了指自己的膝盖:“实在没吃的,就去地里挖那些晒干裂开的泥巴,磨成粉,掺点野菜叶子揉成团,往嘴里塞。那泥巴喇嗓子啊,咽下去刮得食道生疼,可不吃就得饿死。” 他说,村里好多人就是这样,吃了太多泥巴,肚子胀得像鼓,最后就没挺过来。“那时候死个人,就跟掉片叶子似的平常。” 老农的眼睛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哽咽,“你们现在有白面馒头吃,有热饭热菜,有学上,这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啊!” 俱乐部里静悄悄的,只有老农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不少同学都偷偷抹了眼泪,我手里的白面馒头,突然就变得沉甸甸的。 那天听完讲座,我们排着队回学校,一路上没人打闹,每个人都低着头,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后来我才明白,老师和老农不是要我们活在过去的苦难里,而是想让我们知道,如今碗里的每一粒米、身上的每一件暖衣、安稳的每一个日子,都不是凭空来的。是无数人在饥饿与苦难中挣扎、坚守,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温饱与安宁。 如今几十年过去,白面馒头早已成了寻常食物,甚至成了健康饮食里“需要控制”的选项,农机厂的大俱乐部也早已拆了,变成了一栋栋住宅楼。那位老农的模样也渐渐模糊,但他讲的那些故事,那口麸子馒头的苦涩,还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诲,却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从未褪色。 现在每次看到餐桌上的食物,想起小时候的那些经历,都会忍不住心生敬畏。那些粗粮馒头的苦涩,那些干裂泥巴的喇喉,那些老农眼里的泪光,都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幸福从不是理所当然,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安稳,传承那份对生活的敬畏与感恩,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未来最好的期许。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忆苦思甜 小时候上语文课,最难忘的就是那篇讲“粗粮麸子馒头”
山岗间漫步的旅人
2025-11-28 07:21:07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