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年没有收入的陈忠实在家闲坐。突然一通电话打来,接完电话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妻子吓得赶紧过来扶他,哪知,陈忠实却激动地说:“老婆,咱不用养鸡了!” 主要信源:(中国网三农——陈忠实为写《白鹿原》:辞职回村6年,熬4个寒暑,写出一生的血泪巨著) 1993年初春的陕西农村,乍暖还寒。 陈忠实家老屋的木门虚掩着,阳光从门缝斜照进来,在泥土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陈忠实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一封刚收到的信。 信纸很薄,在他长满老茧的手指间微微颤动。 灶台边做饭的妻子抬头时,发现丈夫脸色苍白,赶紧在围裙上擦擦手走过来。 这封来自北京的信让陈忠实百感交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他的小说《白鹿原》。 陈忠实反复读了三遍,抬头对妻子说: "咱们不用养鸡了。" 这句话背后,是六年清贫孤寂的坚守。 六年前,在文化单位工作的陈忠实做出惊人决定:辞职回乡写作。 那时他工作稳定,却执意要写一部"能带进棺材的书"。 妻子虽不理解,还是默默支持,独自扛起养家重担。 陈忠实回到白鹿原下的老宅。 老屋年久失修,窗户漏风,只有一张旧桌子。 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他光着膀子写作,汗水把稿纸浸得发皱。 冬天手指冻得握不住笔,要对着手哈半天热气才能继续写。 最困难时连稿纸都买不起,只能在废纸背面写作。 为写好这部小说,陈忠实花了两年准备。 他走遍关中地区,在县档案馆查资料,一坐就是一天。 晚上找老人聊天,收集民间传说。 动笔前,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已在他心中活了很久。 写作过程充满艰辛。 有时为一段文字反复修改,写到深夜是常事。 煤油灯熏得他满脸黑灰,第二天洗好几遍脸才干净。 妻子每月送来口粮,看见丈夫蓬头垢面的样子直抹眼泪。 陈忠实经常在写作间隙走出老屋,站在黄土高坡上眺望。 远处是绵延的秦岭,近处是层层梯田。 这些熟悉的景象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 有时他会蹲在田埂上,看农民劳作,听他们闲聊,把这些生动的场景都记在心里。 夜深人静时,陈忠实点起煤油灯继续写作。 灯光摇曳,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土墙上。 窗外虫鸣阵阵,屋内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这样的夜晚,他常常写到鸡鸣时分。 1991年寒冬,小说完成最后一稿那天,陈忠实一个人走到村外麦地。 夕阳西下,他望着熟悉的黄土地,六年心血凝结成五十万字手稿,装满了旧木箱。 投稿之路并不顺畅。 多家出版社退稿,有的说题材敏感,有的说不够商业。 直到遇上识货的编辑,小说才得以出版。 谁料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首印一万册很快售罄,半年加印七次。 更让陈忠实意外的是,版税收入高达455万元,这在九十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成功背后是数十年积累。 陈忠实少年家贫,靠助学金读书,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 青年时白天干农活,晚上点灯写作,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文学梦想。 这些经历都成了他创作的财富。 《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时,评委会要求删改部分内容。 陈忠实虽不情愿,还是作了修改,但他始终认为那些描写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艺术追求与现实妥协的无奈,是那个时代作家的共同经历。 如今,《白鹿原》已成为文学经典,列入大学必读书目。 而陈忠实依然朴素如初,用他的话说: "作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 这部用生命写就的史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虔诚坚守。 每个细节都浸透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每个人物都凝聚着他对人性的思考。 这正是《白鹿原》历经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 陈忠实晚年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 他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每天早起写作,保持着数十年的作息规律。 有年轻作家来访求教,他总是耐心指点,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经验。 他说: "文学需要传承,我愿意做铺路石。" 《白鹿原》的成功不仅改变了陈忠实的生活,更影响了一代代读者。 这部作品展现的不仅是历史变迁,更是人性的光辉。 陈忠实用他的一生证明:真正的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又回归生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长安犹见白鹿原,人间不见陈忠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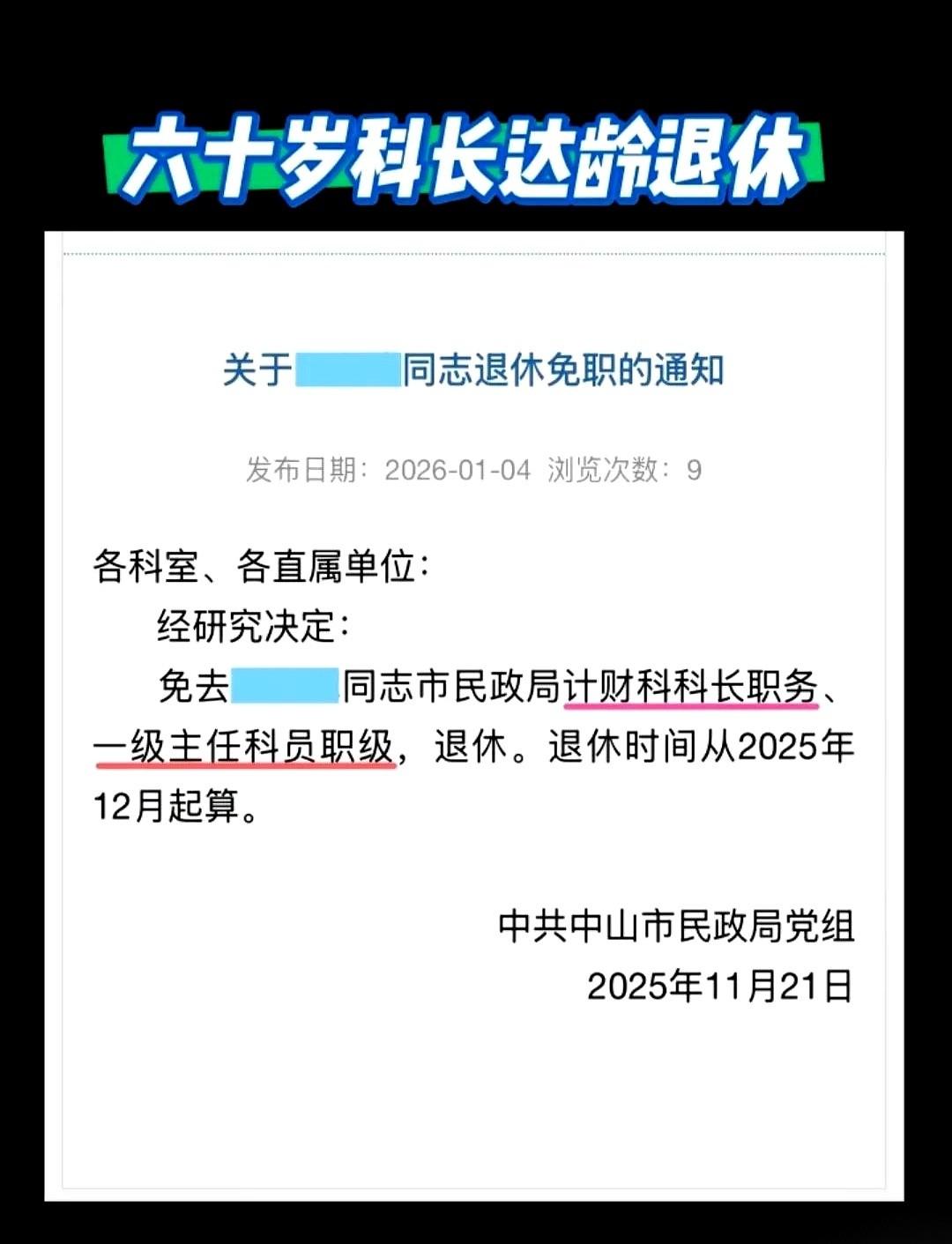





歼35
如果在欧美,陈老爷子肯定是诺奖得主[点赞][点赞][点赞]
用户10xxx25
[赞][赞][赞]
用户12xxx45
没看过,也是刚听说白鹿原
方 言
一介文人,写尽古长安周边自清朝末自建国前历史的,唯有陈忠实老先生!!!
香山仔
陈忠实是以小说家的方式写了一部小说《白鹿原》,以其睿智和洞察力、思想性,蜕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方 言
致敬,有骨气的文人,这里!把长安周边的历史变革如实写进了了作品!!!
天涯明月刀
陈忠实和路遥的作品都看过了,贾平凹的一个也没看过,莫言的也没兴趣看
央迈勇
把老婆甩了吗?
yangjing
[点赞][点赞][点赞][玫瑰][玫瑰][玫瑰]
龙腾盛世
一部很好的著作!最喜欢美丽的田小娥!
用户10xxx39
我有白鹿原,而且看了好几回。
用户10xxx67
那时, 被《白鹿原》深深地吸引了!
用户10xxx55
他的作品没看过,一个变态心理作家。路遥作品每部看完。
望尽天涯路 回复 11-27 22:09
没看过,怎么知道是变态作家的?
用户10xxx28
陈老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厚重的人生阅历铸就了大作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