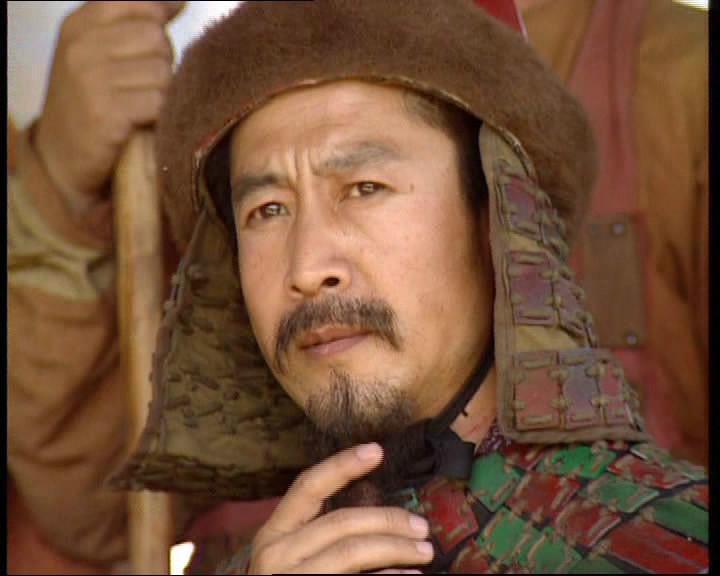诸葛亮最难把控的2位将才,一个让他生不如死,一个让他怀疑人生。 建安十六年的蜀地秋风中,魏延带着部曲投奔刘备时,诸葛亮手中的羽扇微微一顿。 这位在长沙城头斩杀太守韩玄献城的将领,眼神里的锋芒太过锐利,既藏着万夫不当的勇力,也露着恃才傲物的桀骜。 诸葛亮彼时便暗忖:此等将才若能驾驭,可为蜀汉利刃;若失控,则必成祸根。 魏延并未辜负“将才”之名。随刘备入蜀后,他攻雒城、克绵竹,数有战功,从牙门将军一路迁至镇北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破格提拔他为汉中太守,面对群臣惊疑,魏延那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的豪言,更显其胆略超群。 诸葛亮驻汉中后,升他为督前部,可这份重用始终伴着紧绷的制衡,魏延每随亮出,必求兵万人走子午谷,仿韩信故事会师潼关,诸葛亮却总能以“北伐大业不可冒进”为由否决。 这种军事理念的冲突,逐渐演变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魏延常私下慨叹“亮为怯”,恨己才不尽用,其“性矜高”的性格更让他与同僚势同水火,唯独杨仪不肯退让,两人积怨深如渊壑。 诸葛亮夹在中间,既要倚重魏延的战场勇猛。建兴八年阳溪一战,魏延大破郭淮,凭战功封南郑侯,这份战力蜀汉绝难舍弃;又要防备他的刚愎自用,每次北伐都需精心调配兵力,避免其单独行动酿成大祸。 建兴十二年,魏延梦到头生角,占梦者赵直暗语“头上用刀”的凶兆,实则早已埋下的祸根,正随着诸葛亮的病重逐渐显露。 若说魏延是战场上的“不定时炸弹”,李严则是朝堂上的“权力暗礁”。 这位与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的重臣,本是刘备精心设计的制衡棋子——诸葛亮主政成都,李严统军永安,形成文武分治的格局。 李严确有才干,任犍为太守时凿山开路、平定叛乱,还参与制定《蜀科》,可他的野心远比治才更炽烈。 建兴九年的祁山之役,成为两人矛盾的总爆发,诸葛亮出兵前特意叮嘱李严督运粮草,还预设“断后、持久、退兵”三策,可连绵阴雨让粮运受阻时,李严竟派人参传话促退,待诸葛亮撤军又故作惊讶:“军粮充裕,何以退军?” 还上奏刘禅称“伪退诱敌”,试图将责任推给诸葛亮,当诸葛亮拿出他前后矛盾的手迹时,这位托孤重臣的虚伪与狡诈暴露无遗。 此前,李严早已多次试探权力边界:要求划五郡设巴州自任刺史,还劝诸葛亮“受九锡称王”,每一步都在挑战相权底线。 而且诸葛亮对李严的处置,藏着难以言说的痛,他曾力排众议提拔李严,寄望其能共扶汉室,可换来的却是背后捅刀。 将李严贬为庶人时,诸葛亮在奏疏中写道“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这份“厚待”的背后,是对刘备托孤遗愿的坚守,也是对蜀汉内部团结的期盼,最终却落得“自明遭际,悲叹不已”的结局。 而魏延的结局更令人扼腕,诸葛亮临终前安排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可他拒不从命,竟烧绝阁道与杨仪相攻,最终落得被马岱追斩、夷灭三族的下场。 当魏延的首级被杨仪踏在脚下时,诸葛亮若泉下有知,想必会想起当年初见他时的那阵寒意,不是预见了叛乱,而是痛惜这把利刃终究没能为蜀汉所用。 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带走了诸葛亮,也带走了蜀汉最后的制衡。 李严得知诸葛亮病逝后,竟激愤而死,他知道,世间再无一人能让他有复起之机。 这两位让诸葛亮耗尽心力的将才,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魏延的悲剧源于性格与野心的失衡,李严的悲剧则在于权力与忠诚的错位,而诸葛亮在把控他们的日夜里所承受的煎熬,恰是蜀汉政权先天不足的缩影:纵有卧龙鞠躬尽瘁,也难补派系裂痕与人心浮动的深壑。

![刘备真要三造大汉成功了,汉朝很可能变成万世一系了[吃瓜]](http://image.uczzd.cn/1073678762171921458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