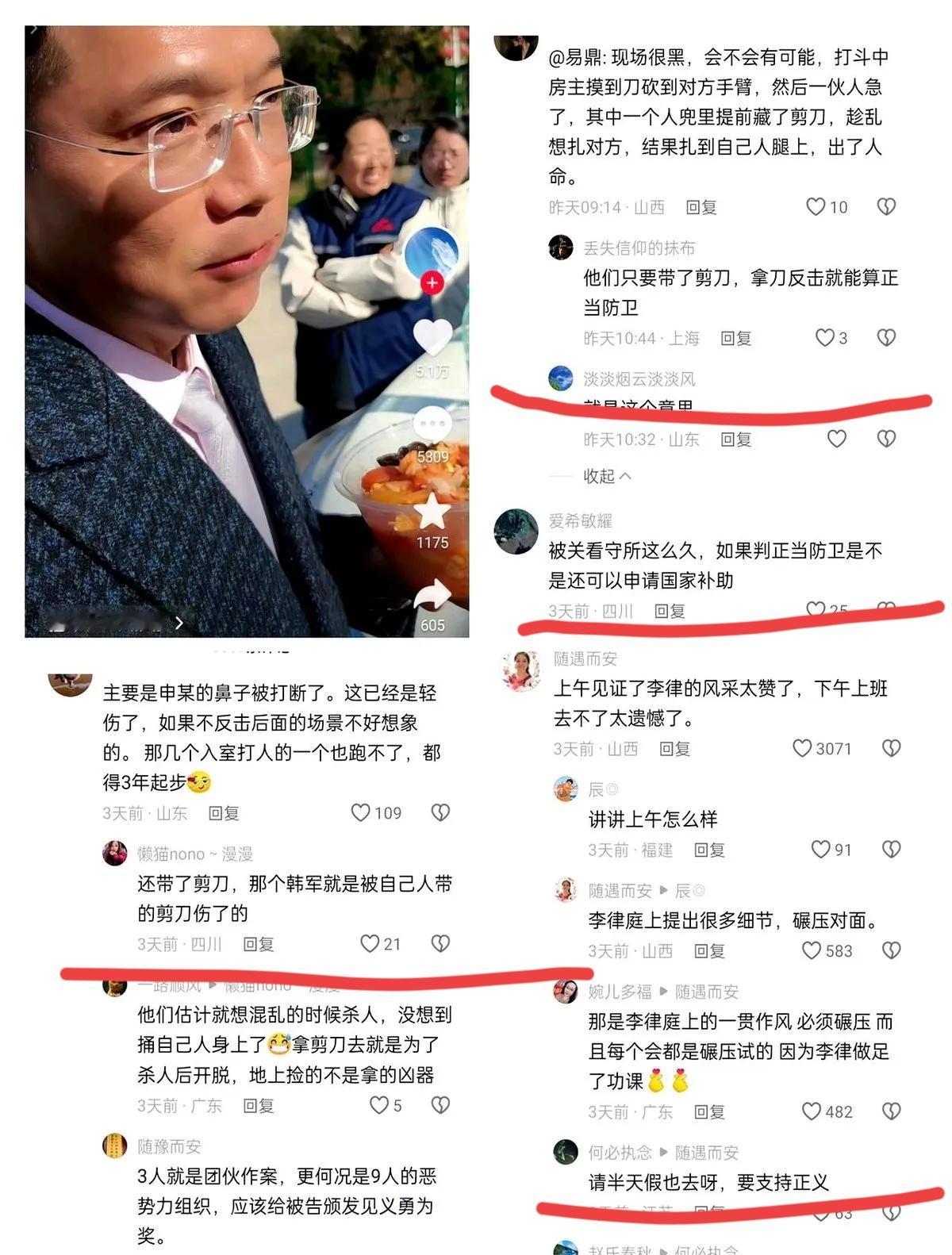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说道“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这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1993年的台北,深秋的凉意透过法庭的高窗渗进来,门口的梧桐叶落了满地,一间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的相机镜头早早就对准了被告席,镜头里的老人裹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别着枚小小的青天白日勋章,那是抗战胜利时颁发的,绶带早已褪成浅灰色,旁听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前排坐着几位同样头发花白的老兵,胸前别着褪色的抗战纪念章,看见薛岳被孙辈搀扶着进来,悄悄挺直了腰板。 法官敲了敲法槌,场子里的窃窃私语立刻停了,问的是关于他居住房屋的产权问题——台湾当局说他占用公家房产,限期搬离的通知发了好几次,谈不拢就把这位抗战元老告上了法庭。 面对法官的问话,薛岳没立刻应声,浑浊的眼睛望着法庭天花板,指节分明的手紧紧攥着拐杖头,沉默像潮水一样漫过整个屋子,“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这句话一出口,连相机的快门声都戛然而止,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地的脆响。 没人敢轻易接话,因为这句话里藏着实打实的战功,容不得半点质疑,1938年的万家岭,他带着部队在德安河谷布下口袋阵,日军第106师团仗着装备精良,气势汹汹地钻进来,却没想到这成了他们的坟墓。 那时候他白天在指挥所盯着地图,红铅笔在等高线上画满圈,晚上带着参谋摸黑查战壕,战士们身上的绑腿磨破了皮肉,却没人叫苦,当地百姓连夜扛着门板来搭建临时工事,连十几岁的孩子都帮着传递消息。 最后总攻时,山炮把日军阵地炸成火海,硝烟弥漫中,冲锋号声穿透云层,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往前冲,光是清理战场就用了三天,日军一个师团几乎被全歼,只有少数残兵侥幸逃脱,这场仗成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最解气的胜利之一。 到了长沙会战,他更是把战术玩到了极致,第一次长沙保卫战,日军仗着坦克大炮开路,一路往南推,扬言要在长沙过中秋,他偏偏不跟敌人硬拼,把部队撤到湘北的水网丘陵里,借着河网稻田跟日军周旋,把敌人的补给线拖得节节断裂。 等敌人推进到捞刀河,早已疲惫不堪,士兵们连饭都吃不上,他突然下令反击,部队从侧翼像尖刀一样包抄过去,打得日军丢盔弃甲往回跑,硬是把“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砸得粉碎。 第三次长沙会战更狠,他琢磨出“天炉战法”,先让部队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把日军引到预设战场,再调动外围三十万兵力形成合围。 寒冬腊月里,战士们趴在雪地里等着冲锋号,冻得发紫的手紧紧握着枪,等日军钻进“炉子”,四面八方的炮火就像铁盖一样盖了下来,浏阳河沿岸的冰面上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这场仗打下来,日军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多具,连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就死了十个,俘虏一百三十九人,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两万八千多人的伤亡代价,鲜血染红了结冰的河面,却没能冻住中国人的骨气。 在场的法官和起诉方代表,心里也跟明镜似的,他们都清楚,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当年在战场上是怎样的意气风发。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带着部队在赣湘鄂三地辗转,军装领口磨出了毛边,军靴底裂了口就用布条缠上,勋章上的绶带褪了色,却从来没退过一步,那些年里,他手下的士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战士牺牲时才十八九岁,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战壕里结冰的水壶、百姓送来的独轮车粮秣,还有战场上永远烧不完的战火,都成了他生命里抹不去的印记。 沉默持续了很久,法官没再继续追问房产的事,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起诉方代表攥着手里的文件,指节都泛了白,却没人敢站出来反驳,连旁听席上原本交头接耳的人,都坐得笔直,眼神里多了些敬畏与动容。 最后法庭没当庭宣判,法槌落下的时候,薛岳慢慢站起身,由人搀扶着往外走,中山装的后襟因为动作有些褶皱,夕阳透过法庭的高窗斜切进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门口的记者想凑上去提问,却被他身边的孙辈轻轻拦住了,这场看似普通的房产纠纷,因为薛岳的一句话,变成了对一段抗日历史的回望,也戳中了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后来有人说,那天走出法庭的时候,薛岳望着台北街头的车水马龙,轻声说了句“当年要是有这劲头打鬼子就好了”,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谁都明白,对于一个把半生都扔在抗日战场上的老兵来说,战功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却是支撑他走完一生的脊梁。 现在有些人忙着翻旧账、搞清算,却忘了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人,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战,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太平,可晚年却连一个安稳的住处都要被争抢,这让在场的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 你说那些为家国拼过命的人,不该被温柔以待吗?评论区聊聊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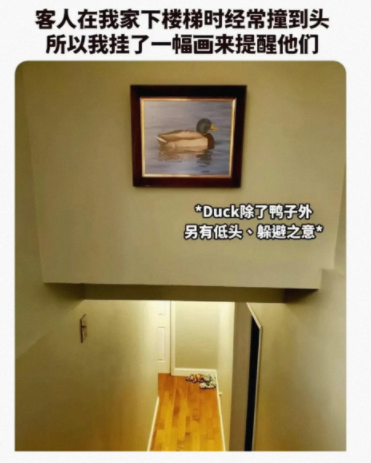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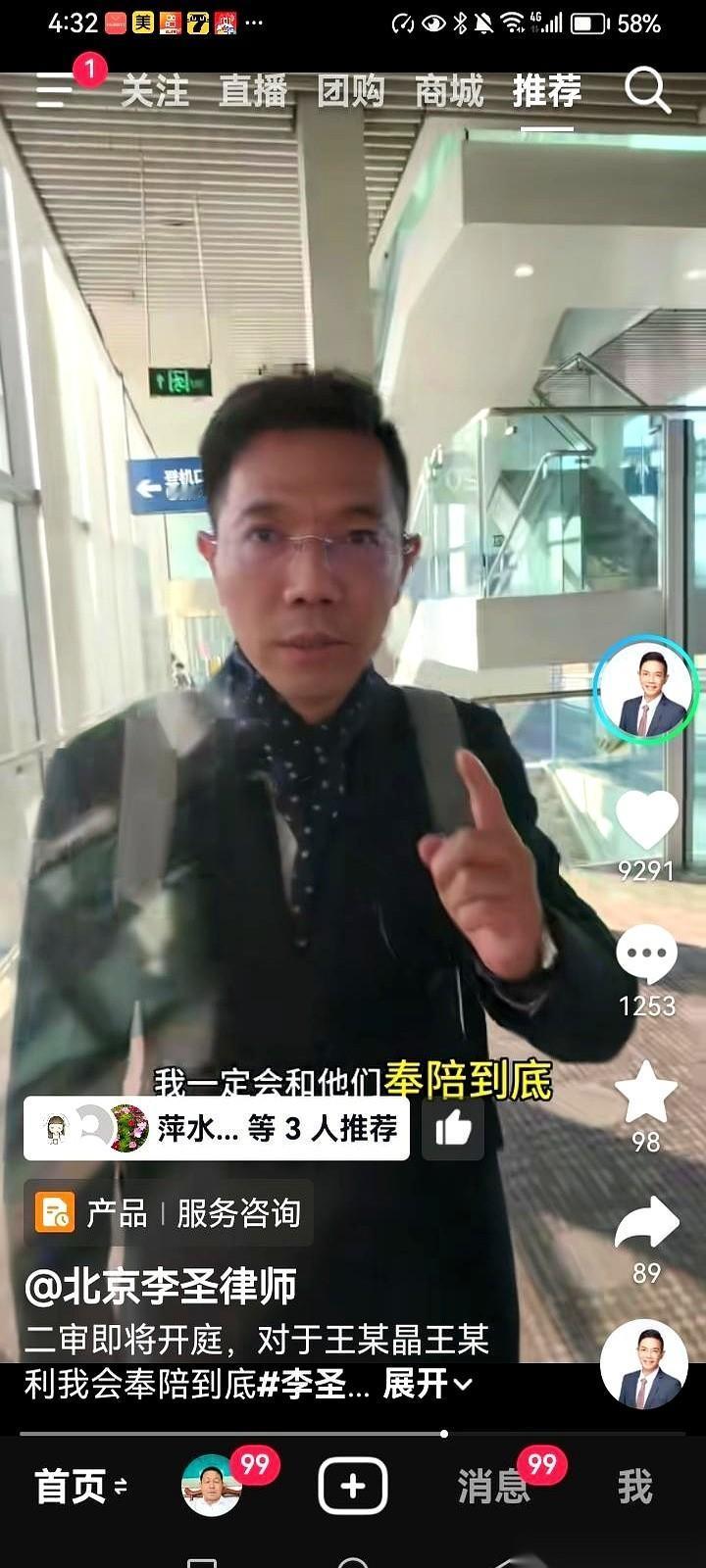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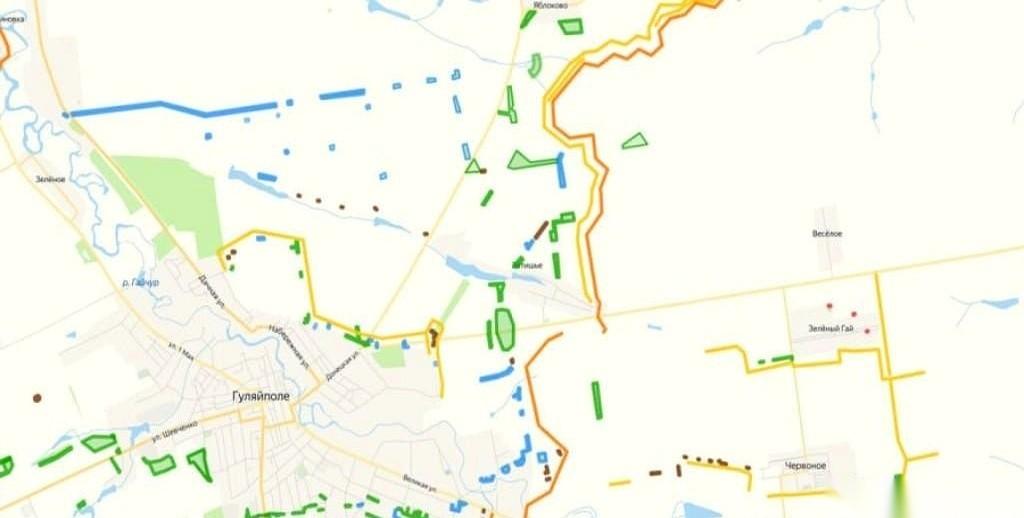
![榜一大哥该哭死在卫生间了吧是一个人吗?网红原来是人贩子[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208380413953750574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