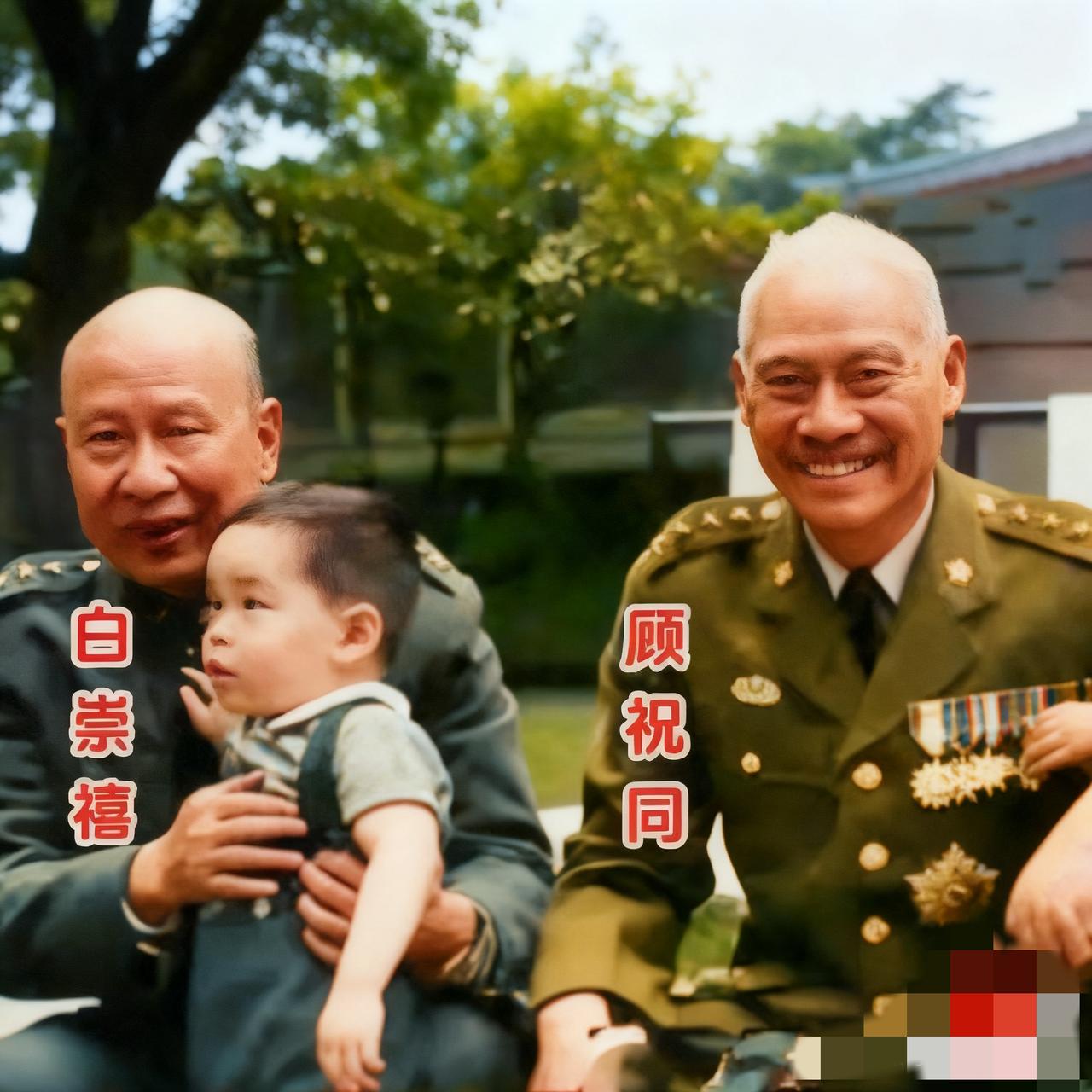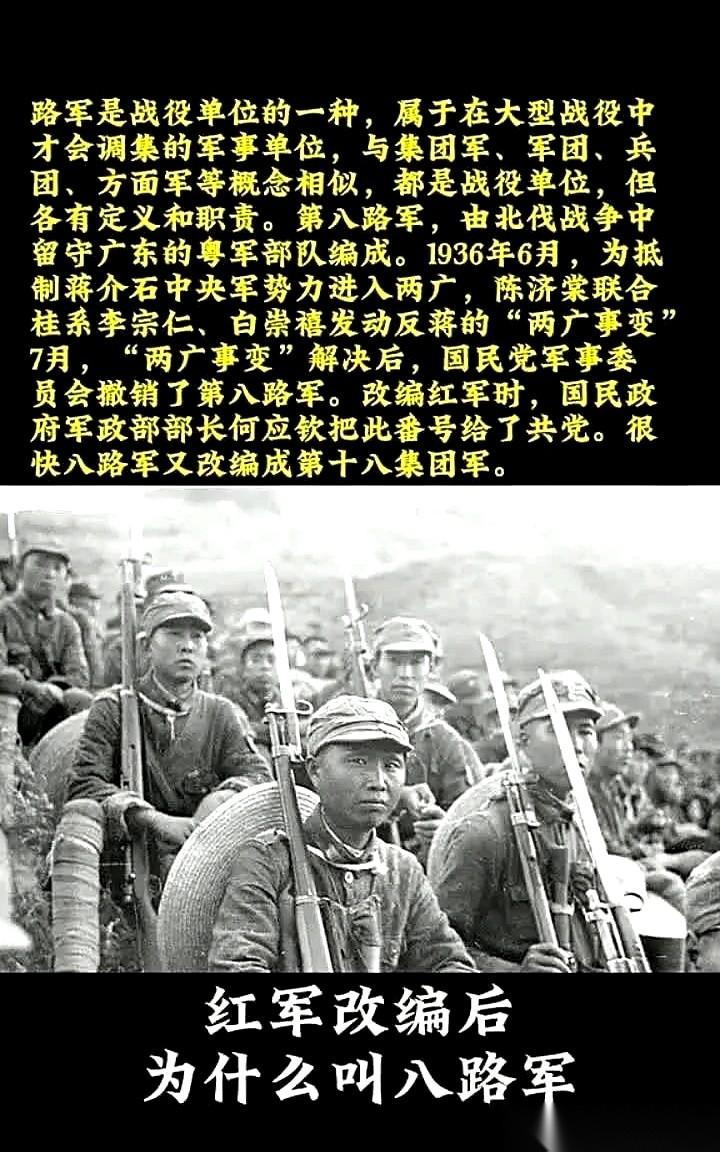1903年,30岁梁启超和王桂荃成婚。同居过后,梁启超却说:“我主张一夫一妻,你只能是丫鬟,就算你生了孩子,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没有资格!” 1903年的上海,初秋的风带着点黄浦江的潮气。梁启超的寓所里,王桂荃攥着刚浆洗好的长衫,指尖在布面上蹭出细小的褶皱——今天是她搬进主卧的第三天,可心里那点忐忑,比刚从广东老家来梁家当丫鬟时还厉害。 她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跟着夫人来梁家五年了。夫人身子弱,去年生二公子时差点没挺过来,拉着她的手说:“桂荃,家里事多,你替我多照看着先生。”那时她只当是句寻常嘱托,没承想,上个月夫人竟亲自张罗着,让她跟先生圆了房。 夜里的煤油灯昏黄,梁启超坐在书桌前写文章,笔尖划过宣纸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王桂荃端着夜宵进去,刚把碗放在桌上,就听见先生头也不抬地说:“桂荃,有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她心里一紧,手不自觉地绞着围裙。 “我在文章里写过,一夫一妻是文明大义,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梁启超放下笔,转过身看着她,眼神里有愧疚,却更多的是不容置疑,“你进了这屋,名分上还得是丫鬟,对外不能说别的。” 王桂荃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就算以后有了孩子,”梁启超的声音低了些,却像冰锥扎在她心上,“他们的母亲,也只能是蕙仙。你……没有资格当母亲。” 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晃,那些曾在报纸上读到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此刻听着格外刺耳。王桂荃猛地想起前阵子先生在演讲台上说“女子也应有独立人格”,台下掌声雷动,可这话到了自己这儿,怎么就变了味? 她没哭,也没闹,只是福了福身,轻声说:“我知道了,先生。”转身退出去时,后背撞到门框,疼得她咬了咬嘴唇——比起身上的疼,心里那股子凉,更让人受不住。 日子还得过。她照旧伺候先生和夫人,只是话更少了。早上给先生研墨,他写文章时,她就在旁边纳鞋底,针脚比以前密了不少。有回李蕙仙看出她不对劲,拉着她的手说:“桂荃,先生就是嘴硬,他心里是认你的。” 王桂荃笑了笑,没接话。她知道夫人是好意,可先生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掉。 转过年来,王桂荃真的怀上了。孕吐厉害,吃啥吐啥,人瘦得脱了形。梁启超看着心疼,让厨房顿顿给她炖鸡汤,却从没提过“名分”二字。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梁启超抱着襁褓里的小家伙,笑得合不拢嘴,可对外只说“夫人又添了个少爷”。 王桂荃抱着孩子喂奶,听着外面先生跟客人介绍“这是蕙仙生的老三”,眼泪悄没声地掉在孩子脸上。小家伙咂着奶头,小手攥着她的衣襟,那点温热,成了她唯一的慰藉。 后来她又生了几个孩子,一个个都被记在李蕙仙名下。孩子们喊李蕙仙“母亲”,喊她“桂荃姨”。有回小儿子刚会说话,抱着她的腿喊“娘”,梁启超听见了,沉下脸说:“叫姨。”孩子吓得哇哇哭,王桂荃赶紧抱起他,拍着后背哄:“乖,叫姨,姨给你糖吃。” 夜里哄睡了孩子,她坐在床边纳鞋底,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像揣着块冰。她想起刚到梁家时,先生给她们这些下人讲“新思想”,说“人人生而平等”。那时候她信了,觉得跟着这样的先生,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可到头来,先生的新思想,唯独没给她留位置。 李蕙仙去世那年,王桂荃已经生了六个孩子。梁启超在葬礼上哭得老泪纵横,转过头却对王桂荃说:“家里不能没个主心骨,以后你多费心。”这话听着像托付,却还是没提“名分”二字。 王桂荃默默点头,给孩子们换孝服,安排葬礼的杂事,忙得脚不沾地。夜里累得倒头就睡,梦里却总回到1903年那个晚上,先生坐在煤油灯前,对她说“你没有资格”。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都知道了真相。三儿子梁启超思成最心疼她,有回跟父亲争执:“爹,您总说平等,为何对桂荃姨这样?”梁启超叹了口气,没说话。 王桂荃拉过儿子,摇摇头说:“别怨你爹,他有他的难处。” 其实她心里明白,先生不是不爱她,只是那点“文明大义”的面子,比她的委屈重要。她这辈子,就像先生文章里没写完的注脚,藏在光鲜的正文背后,没人看见,也没人记得。 晚年时,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孩子们寄来的照片,嘴角会带着笑。有人问她这辈子值不值,她总是说:“孩子们好,就值了。” 只是偶尔风起时,她会摸出藏在枕下的那块布,上面绣着个小小的“荃”字——那是刚到梁家时,她自己绣的,想着总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用这个名字。可到最后,这名字也只藏在她自己心里,像个没说出口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