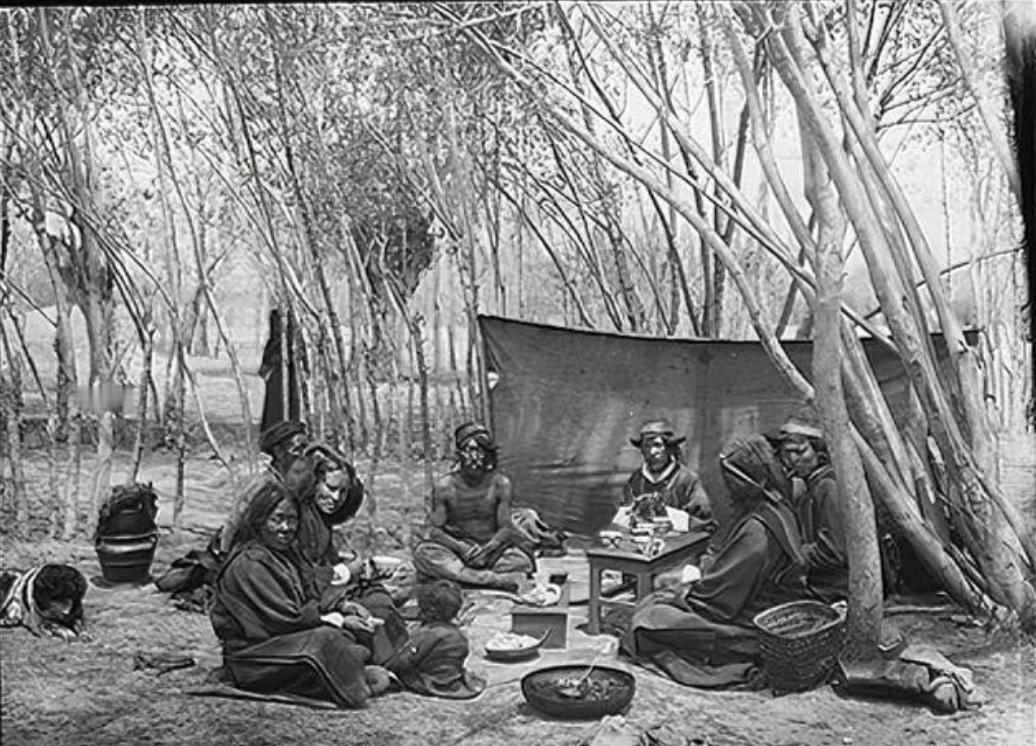青稞是裸口感最差的粮食,没有之一。上世纪70年代,西藏地区曾尝试推广小麦种植,很多牧民第一次吃小麦,结果纷纷嫌弃,味道根本没法和青稞相比,于是,就起了流言:青稞是藏族吃的,小麦是汉族吃的,藏族人吃了就会没力气,就连藏族的牛都要吃青稞杆的。 在西藏,有一种粮食曾被奉为“生命之粮”,又被嫌弃到“难以下咽”。 有一种外来作物,曾被拒之门外,如今却成了餐桌常客。 它便是青稞与小麦! 在西藏种小麦,早不是新鲜事。 《旧唐书》里就有吐蕃种小麦的记载,可直到1971年,西藏才真正大规模推广冬小麦。 不为别的,就为“吃饱”。 那时的西藏,粮食缺口大得很。 1959年民主改革时,全区粮食产量才2.9亿斤,人均口粮不足150公斤。 为了让老百姓吃饱,中央派科考队从内地引了高产小麦品种,试种成功后,1971年正式启动推广。 到1978年,小麦种植面积占到总耕地的近三成,粮食产量翻了近一倍,西藏首次实现口粮自给。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问题”就来了。 小麦不好吃,还不好做。 西藏的小麦,因高海拔、低积温,蛋白质含量低、面筋差,蒸馒头是“死面疙瘩”,煮面条是“散架的面条”。 更要命的是燃料。 西藏缺木柴,农民全靠牛粪烧火,牛粪火力小、温度低,青稞籽粒易熟,小麦却半生不熟。 想做面条、包子,得用柴禾,可那时山上的草根都被挖来当燃料,挖得漫山遍沙。 “那时候吃小麦,跟受罚似的。” 1975年队里全种小麦,青稞只剩坡上一点,“小麦糌粑没青稞的香,煮面条像吃面糊糊,大人小孩都喊‘吃不下’。” 更邪乎的是,流言越传越邪乎:“小麦吃了腰疼”“小麦没力气”。 其实哪是小麦的问题? 是海拔、燃料、配料的限制,把小麦的“缺点”放大了。 连汉族干部都受不了。 “我们吃小麦长大的,可西藏的面粉做不出内地的馒头。” 不少汉人都说:“那时候想吃青稞,得拿鸡蛋跟老乡换,哪有现在方便?” 于是,1977年起,西藏农民开始“抗命”。 明明种了小麦,却偷偷在坡上种青稞。 有的公社甚至把小麦苗拔了,改种青稞。 政策推得越急,抵制得也就越厉害。 1980年,中央考察团赴藏,听到的最多抱怨就是“想吃青稞没青稞”。 胡耀邦当场拍板:“群众愿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干涉!” 随后,西藏调整政策,压缩小麦种植,扩大青稞面积,还把青稞收购价涨到跟小麦持平。 可谁都没想到,1985年土地分到户后,农民又主动种回小麦。 原因很实在,要吃饱,更要吃好。 首先,人口涨得太快。 1980年西藏人口189万,1990年涨到221万,粮食需求翻了倍。 青稞亩产只有小麦的三分之二,种青稞不够吃,种小麦才能填饱肚子。 其次,畜牧业需要小麦。 藏族是“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农区畜牧业靠种植业提供饲料。 青稞秸秆产量低,小麦秸秆多,种小麦能多养牛羊,换肉换酥油。 更关键的是,商品经济活了。 农民不用自己种青稞,能去市场上换。 到1995年,西藏小麦种植面积回到1980年的水平。 农民嘴里的“没力气粮”,成了“能换肉的粮”。 并不是小麦变了,而是生活的需求变了。 如今的西藏,小麦早已嵌入日常饮食。 拉萨的藏面馆飘着骨汤香,日喀则的家庭做着青稞小麦混合的包子,山南的农民用小麦换青稞做糌粑。 小麦是“日常”,青稞是“仪式”。 小麦能“上位”,不是因为青稞不好,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 燃料变了,煤气罐、沼气普及,能煮熟小麦。 配料足了,鸡蛋、油、糖、肉,能把小麦做成多样的美食。 更多的是观念变了,年轻人不觉得“吃小麦不是藏族”,反而觉得“能吃小麦是日子好的象征”。 而青稞,也没“消失”,它成了文化符号和高端食材。 藏历新年,家家户户摆青稞苗祈求丰收。 望果节,人们围着田地转圈,青稞的香味混着祈祷声。 而青稞的营养,也正在逐渐被挖掘。 β葡聚糖含量高,能降血压,做成饼干、爆米花、青稞酒,销往内地。 高原的“纯净”标签,让青稞成了“网红食材”。 虫草、松茸能火,青稞为什么不能? 有人问:“小麦取代青稞,是不是丢了藏族文化?” 答案恰恰相反。 藏族文化没丢,反而活了。 青稞还是那个青稞,只是从“主食”变成了“文化载体”。 小麦还是那个小麦,只是从“外来粮”变成了“日常粮”。 农民的选择,从来不是“抛弃传统”,而是“选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就像庄巧生院士说的:“有机体遇到新环境,会适应,会进化。” 西藏的小麦和青稞,也是这样。 小麦适应了高原的烹饪条件,青稞适应了全球的市场需求,藏族农民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 这就是西藏的故事。 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兼容并蓄的智慧。 主要信源:(观察者网——强舸:小麦怎样走上藏族餐桌——西藏现代化与藏族饮食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