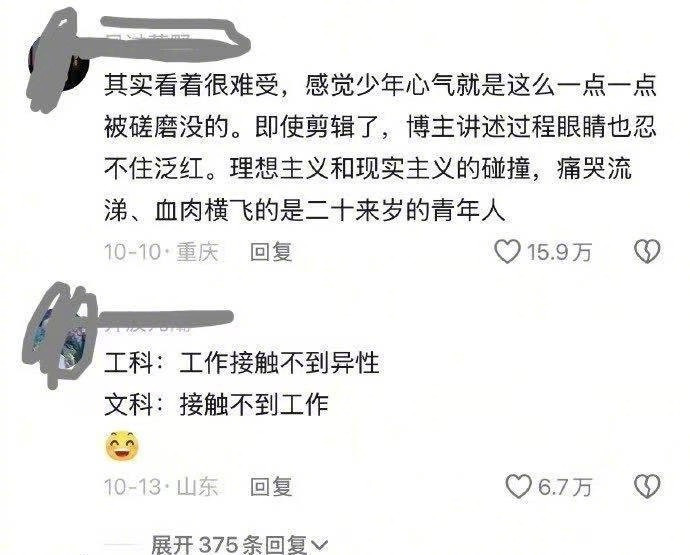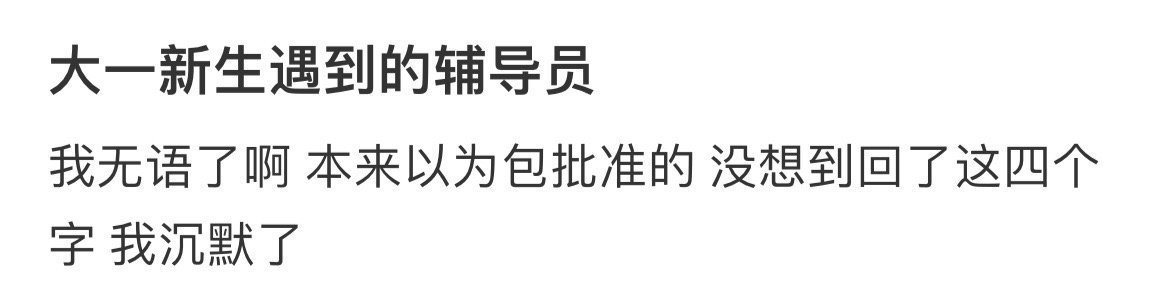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后,没钱租房子,就对房东说:“我把你的孩子辅导到全班前10,你可以免了我的房租吗?”房东高兴地说道:“好!” 2006年,俞敏洪在纽交所敲响了上市钟声,这清脆的声音,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几十年前江苏江阴那个农家少年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沙沙声遥相呼应。 人们常用坚韧与逆袭来描述他的人生,但贯穿其数次绝境逢生的真正线索,是对“知识”这一无形资本四种价值形态的极致挖掘与重塑。 在他的青年时代,知识是他冲破命运枷锁的唯一“通行证”。 1962年,俞敏洪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匮乏的资源几乎注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换钱买书,他捡过废品;为了抓住补习的机会,他曾步行十几里路。 知识是他唯一的武器,在经历两次高考失利后,1980年那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是这张“通行证”的最终兑现。 即便入学后因乡音和薄弱的英语基础备受打击,在班里排名倒数,他依旧凭借苦修完成了身份的跨越。 他坚持每日背诵50个单词,在树林里将口语练至沙哑,最终从一个自卑的农村孩子成长为北大的留校教师。 在这个阶段,知识是他用以对抗出身、实现个人救赎的纯粹工具。 然而,1991年他离开北大体制的庇护,知识的价值形态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象牙塔内的晋升阶梯,而是赖以生存的“硬通货”。辞职后的俞敏洪囊中羞涩,甚至无法支付房租。 面对窘境,他向房东提出了一个交易:用自己的英语辅导能力,换取一处栖身之所。 当房东的孩子成绩从班级中下游一跃成为年级第五时,知识的商品价值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 这份市场认可,也让他反思了此前与“东方大学”合作办学的教训,那次合作让他明白,若无自主权,知识创造的利润终将旁落。 对知识商品属性的领悟,催生了新东方的诞生。 1993年,借助教育政策的东风,俞敏洪在北京中关村一间仅10平米的教室里,开启了知识的第三重形态塑造,将其打造成可复制、可规模化的“商业系统”。 他独创的“激情英语教学法”,将枯燥的语法点融入幽默故事与励志演讲,迅速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学生们甚至下课后也不愿离开,而是抢占下一堂课的座位。 更关键的是,他说服王强、徐小平等好友从海外归来,组建了“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的互补团队,这标志着新东方的知识服务开始流程化与系统化。 从最初的20余名学员,到1995年学员规模达到一万五千人,知识在他手中完成了从个人技艺到商业帝国的蜕变。 2006年,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大陆首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将知识的规模化价值推向了顶峰。 辉煌总伴随着考验,当行业政策的巨变让新东方的核心业务遭遇重创,年过六旬的俞敏洪再次面临绝境。 他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出于“不能让跟着我的兄弟没饭吃”的责任感,开启了知识的第四次形态进化,将其锻造为企业“再生”的媒介。 他带领团队跨入直播带货领域,创建了“东方甄选”,这并非简单的销售,而是将知识重新编码,把商品置于历史、文化与诗意的语境中讲解。 课堂搬进了直播间,知识成为了连接产品与消费者的全新桥梁,最终让新东方在争议中重焕生机。 俞敏洪的人生,是一部关于如何运用核心资产穿越周期的教科书,他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信条,真正的底气或许就来源于此。 无论环境如何变迁,他总能重塑知识的价值形态,使其从个人的通行证,变为交易的硬通货,再到庞大的商业系统,最终化为绝境中自我再生的强大媒介。 他的传奇,归根结底,是知识力量的胜利。 信息来源:海峡新干线 2025-10-24 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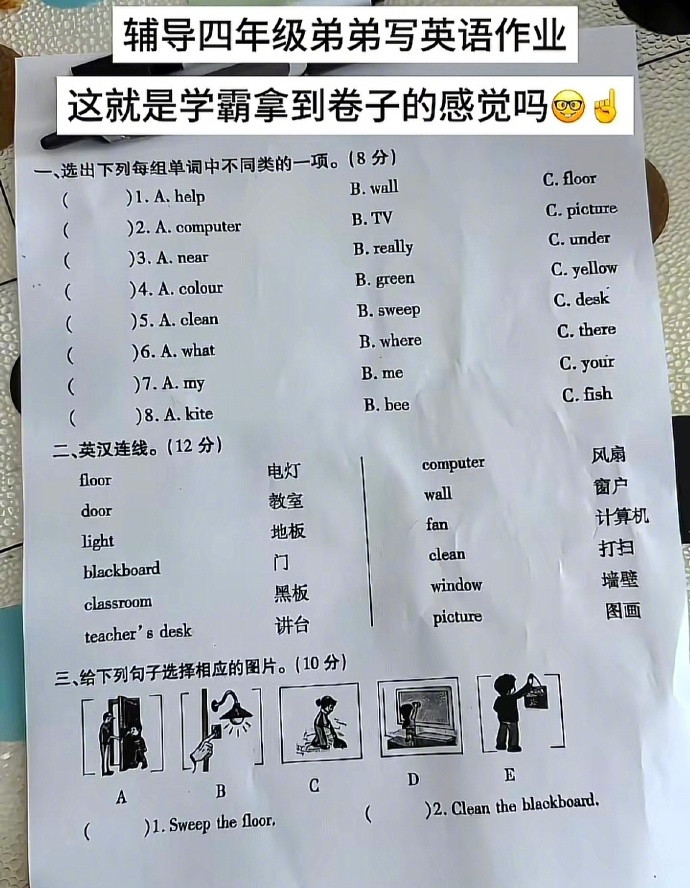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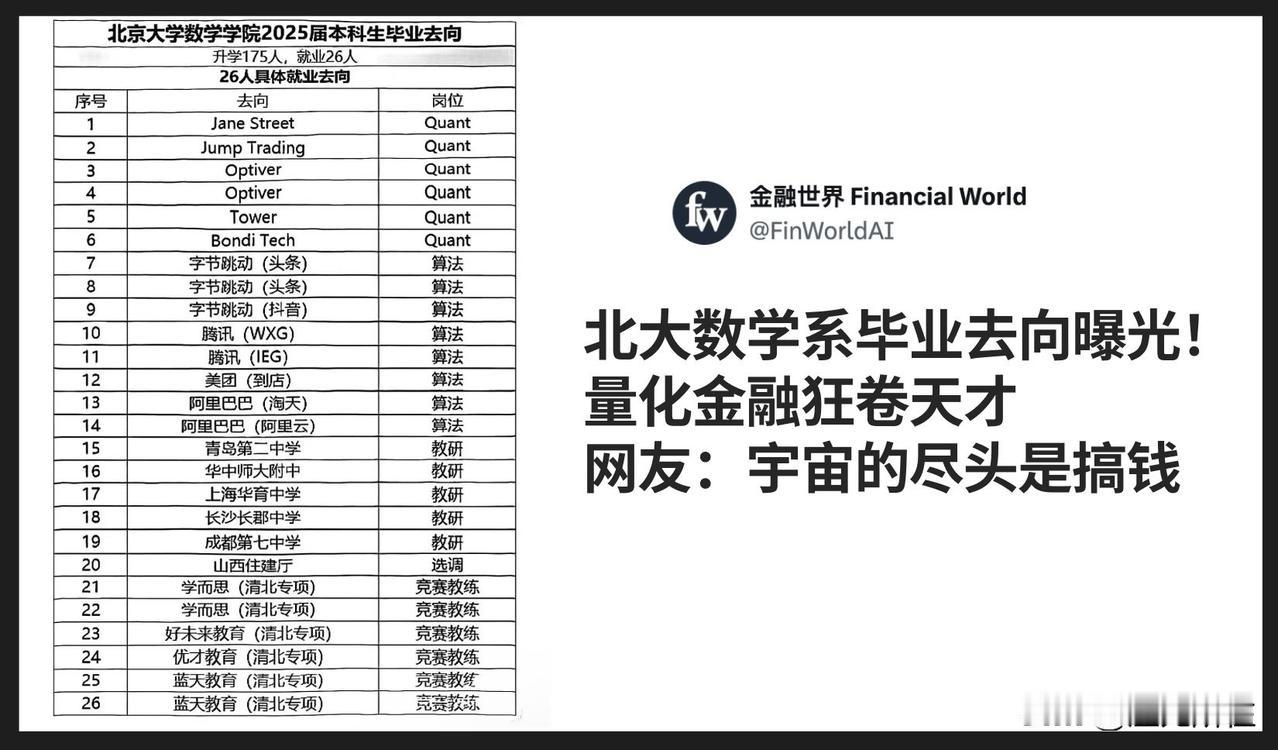
![看来我当年说得还是挺准的。[思考]](http://image.uczzd.cn/762691064286473082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