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土气,但晚上却仍然跟她行“夫妻”之事,张幼仪晚年也曾回忆说:大婚当天,我们就圆房了,在英国时,虽然他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他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 1915年,15岁的张幼仪被家里安排与徐志摩定亲,次年成婚。 她出身于江苏宝山的富商之家,家族背景殷实,但教育程度不高,连小学都没完整念完。 婚前,她只见过徐志摩一次,而那一次,徐志摩就私下在朋友面前说她“像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他嫌她不会讲英文,嫌她穿得老气,甚至嫌她吃饭时的动作不优雅,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羞辱。 婚后,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善,他整日躲在书房看书、写诗,或是外出聚会,与朋友谈理想、谈自由,却几乎不与张幼仪交谈。 张幼仪曾说,他们白天说不上三句话,但到了夜里,他却会照样上床,完事之后翻身背对她睡觉。 她从未敢问为什么,甚至以为这是做妻子的义务,是应该的,她也曾尝试改变自己,努力学英文、学穿衣打扮,但在他眼里,她始终是那个“配不上他”的人。 1920年,徐志摩带张幼仪赴英国留学,名义上是“进步”,实则是进一步的冷暴力。 他在剑桥读书,张幼仪不会讲英语,每天独自待在宿舍,连出门买菜都成问题,她曾炖了一锅汤等他回来,他却甩下一句“我不吃这些东西”,连筷子都没动就走了。 她忍着委屈、孤独,却仍然在夜晚被他当作“妻子”对待。 她曾回忆说:“白天不同我讲一句话,但晚上仍然和我行夫妻之事。”那不是亲密,而是一种剥夺。 1921年,她怀了第二个孩子。 徐志摩明确表示不愿意再要孩子,逼她打胎。张幼仪不愿意,徐志摩干脆搬出住所,留下她一个人。 在德国生下孩子后,他寄来一封信:“必欲离者,虽死不辞。” 这封信后来成为他们离婚的正式文书,送达的是张幼仪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破碎。 1922年,两人正式离婚,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为罕见,特别是女性主动签字同意离婚,更是少见。 而她这样做,不是因为她不爱了,而是她终于明白,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只会让你越来越卑微。 “我那时才知道,女人不能靠男人,得靠自己。” 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不是口号,而是血泪。 离婚后的张幼仪并没有崩溃,她在德国学习幼儿教育,学德语,读书,接触新的教育理念。 1926年,她带着孩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后来还帮哥哥张君劢打理银行事务,并创办了“云裳时装公司”,成为上海滩最早的女企业家之一。 她从那个“土气的妻子”,变成了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而徐志摩呢?他在离婚后不久就和陆小曼相恋,后来结婚,但婚姻并不幸福,陆小曼嗜烟嗜赌,生活不规律,徐志摩既爱她又被她拖累。 1931年,36岁的他在飞往北平的飞机上失事身亡,结束了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 张幼仪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与徐志摩的婚姻,没有怨恨,只有清醒。 “他是个诗人,不适合过日子。” 这句评价,既客观又残酷,徐志摩在诗里写“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但他在婚姻中从未轻轻离开,而是狠狠地伤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和尊严。 很多人把张幼仪和陆小曼、林徽因放在一起比较,说她没有文化、不时髦、不懂浪漫。 但如果把目光从诗意的滤镜下移开,就会看到真正的张幼仪——那个从被嘲笑、被忽视、被抛弃,到最后依靠自己站起来的女人。 她不是“土气”,她只是没有被赋予机会去展示自己,而一旦她掌握了话语权,她就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大树,而不是被风一吹就散的云烟。 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冷淡,而是被当作“工具”对待,徐志摩嘴上说不爱,却仍然“行夫妻之事”,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控制。 他不是不理解自由恋爱,只是他从未真正尊重过一个女性,他爱林徽因,是因为她能与他谈诗谈梦;他爱陆小曼,是因为她能陪他叛逆放纵;而张幼仪——她只是被安排进他人生的一段“过渡”。 但也正是这个“过渡”,成长为了风雨中站立的女性楷模。张幼仪没有诗人的浪漫,却有实干者的清醒;没有豪门太太的光环,却有自我觉醒的勇气。 她后来在上海滩的地位,靠的不是徐家的名头,而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事业。 张幼仪,用一生走出了一条不依附、不讨好、不回头的路,她的晚年,平静、优雅,不再谈爱情,也不再提徐志摩。她不需要诗,她自己就是一首活成的诗。 那种从裂缝中长出来的坚韧,是任何纸上谈兵的浪漫都无法比拟的。 张幼仪的故事,不只是过去的故事,它是提醒,是启示,是力量,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给你选择,而是你有能力拒绝被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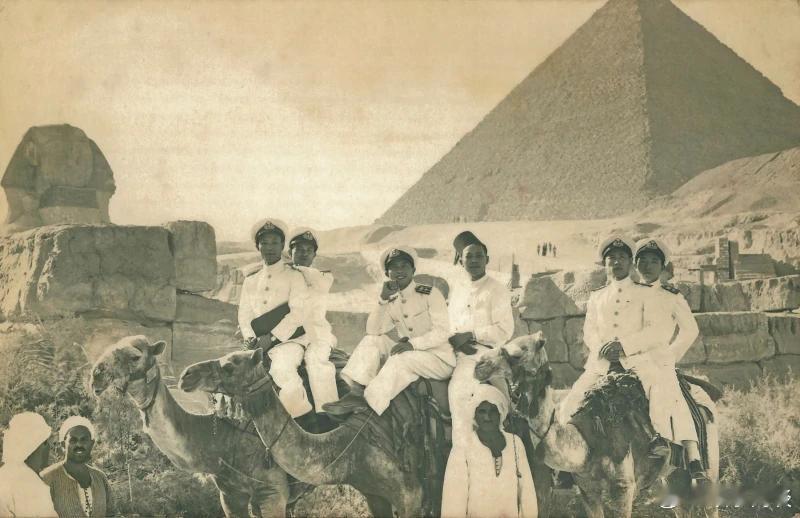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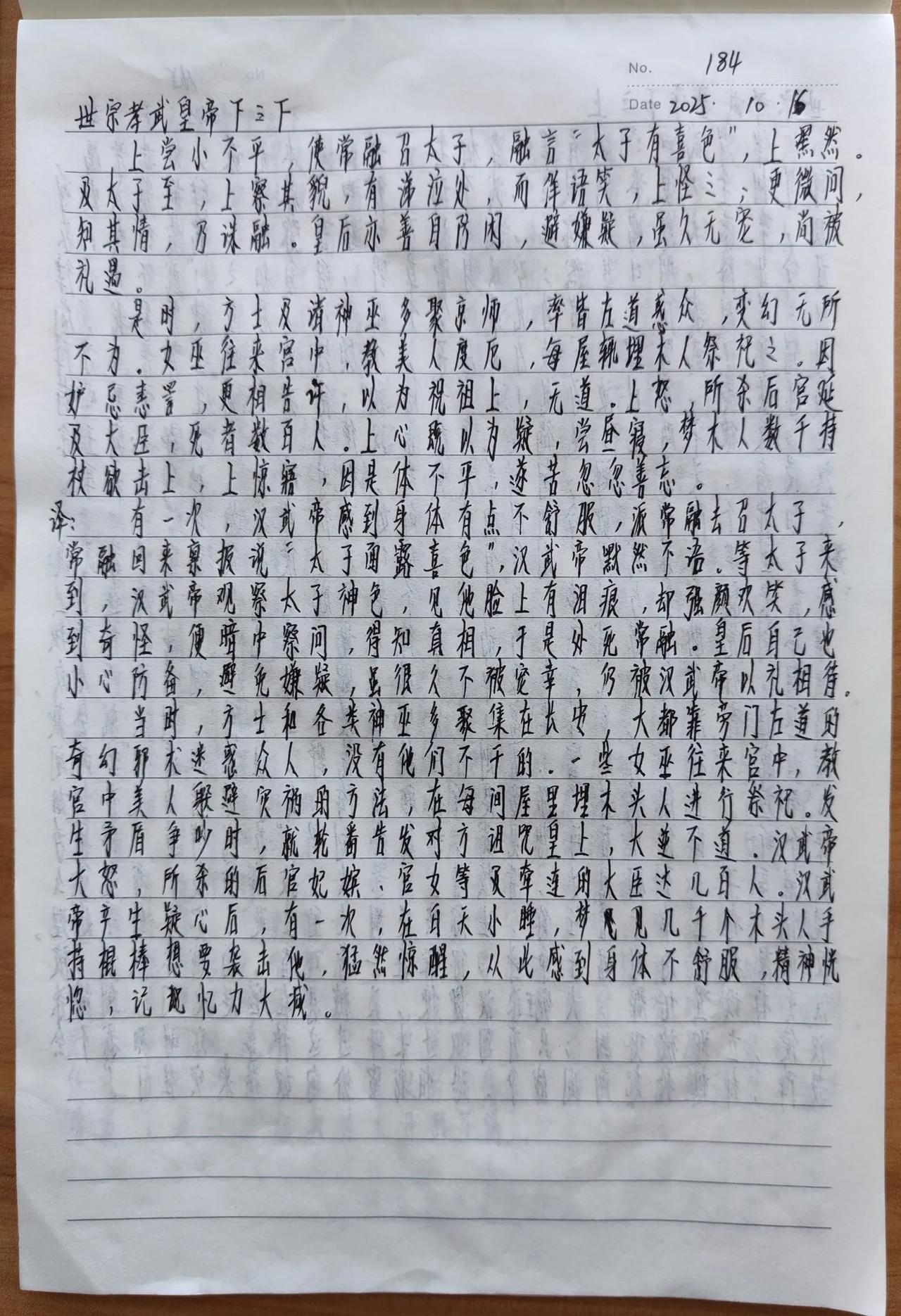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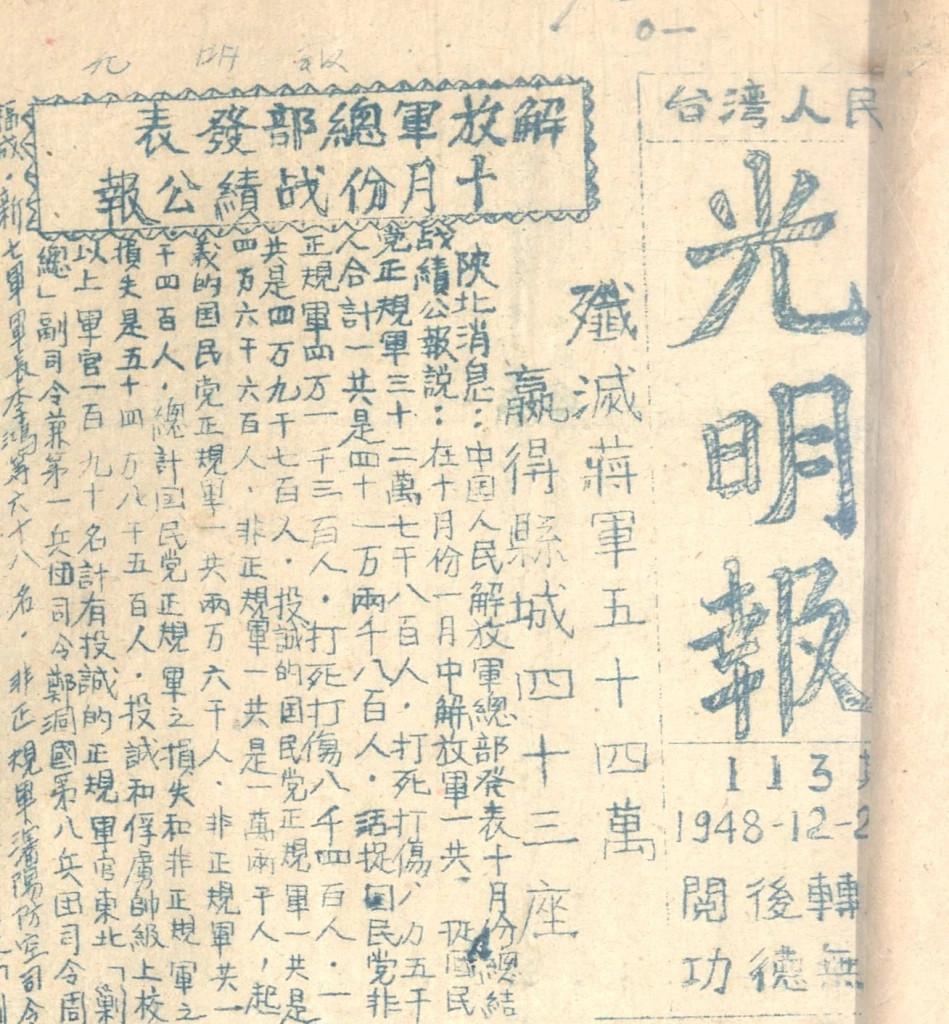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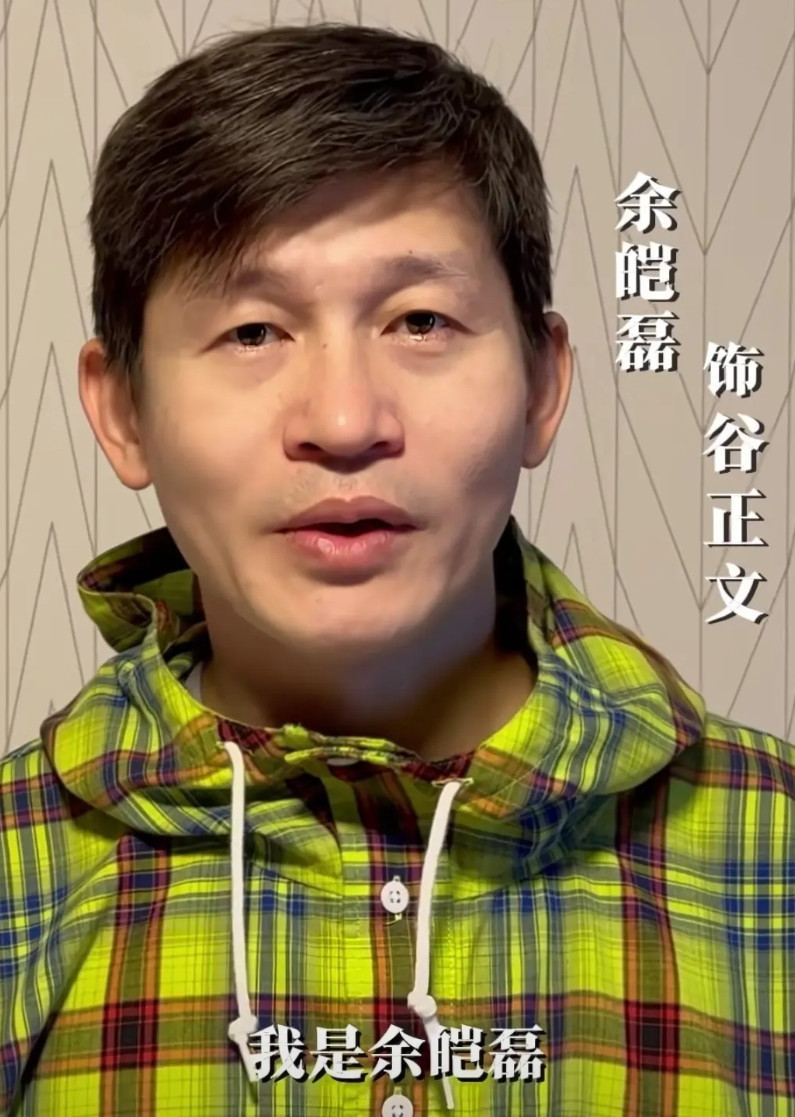

用户72xxx71
渣男鼻祖
用户12xxx17 回复 10-16 17:42
徐真不配张幼仪。梁启超也看不惯这弟子背信弃义。张比陆强得多。陆不愿去北京陪徐,让徐在京沪间飞来飞去,怎不出事,那时的飞机没那么可靠
笨笨
这个照片是黄磊和周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