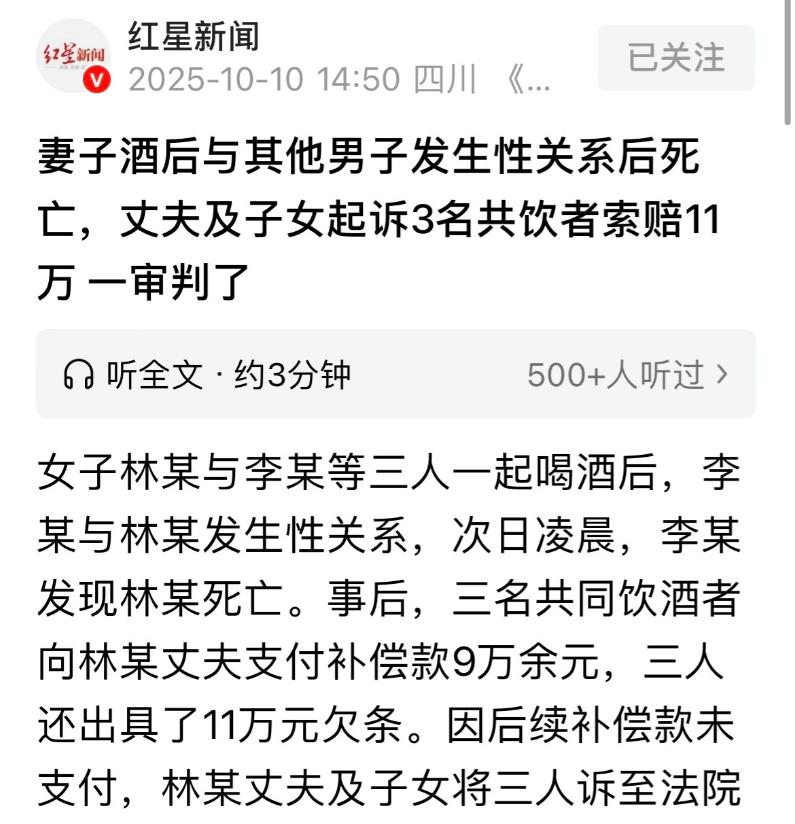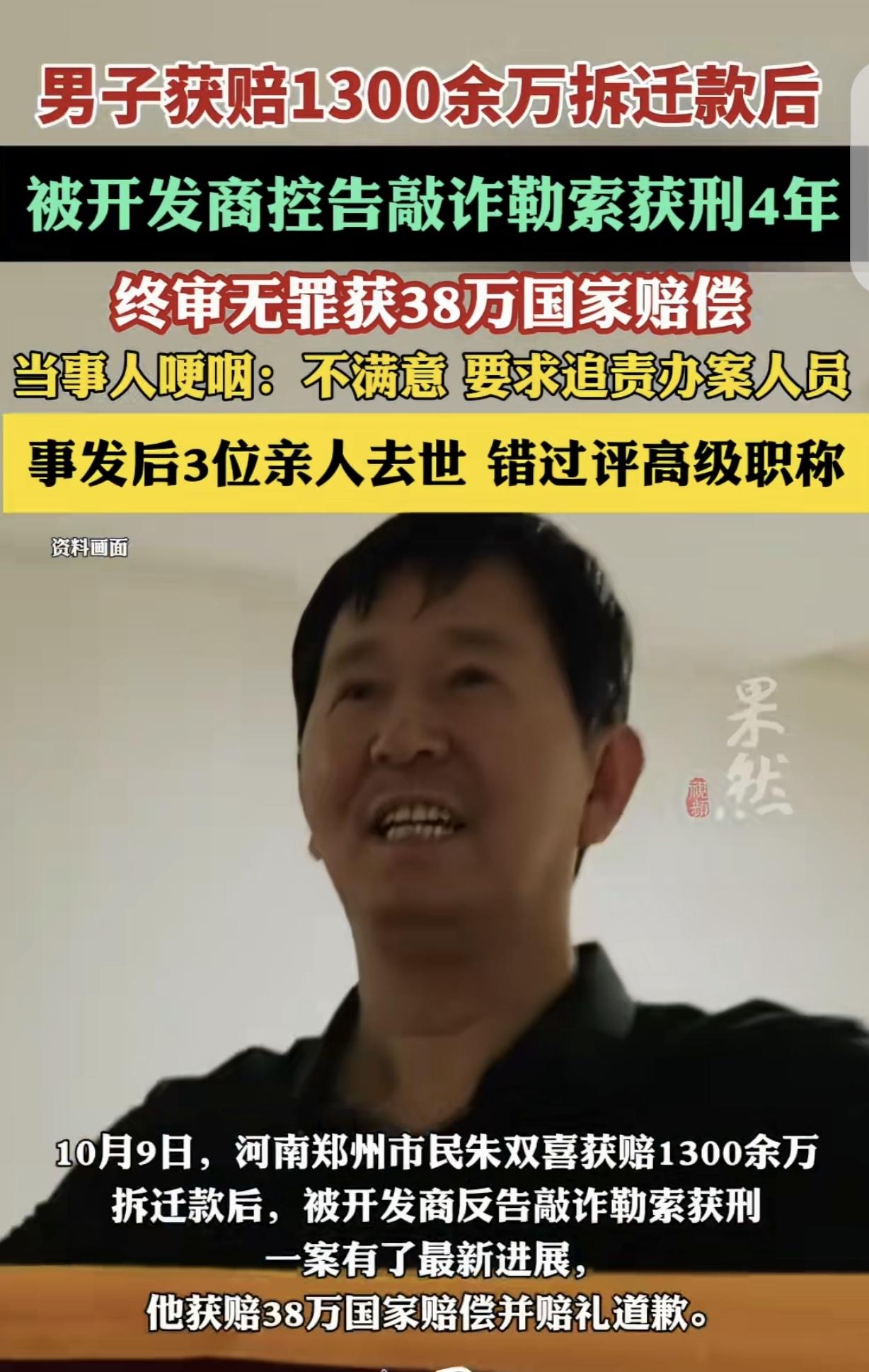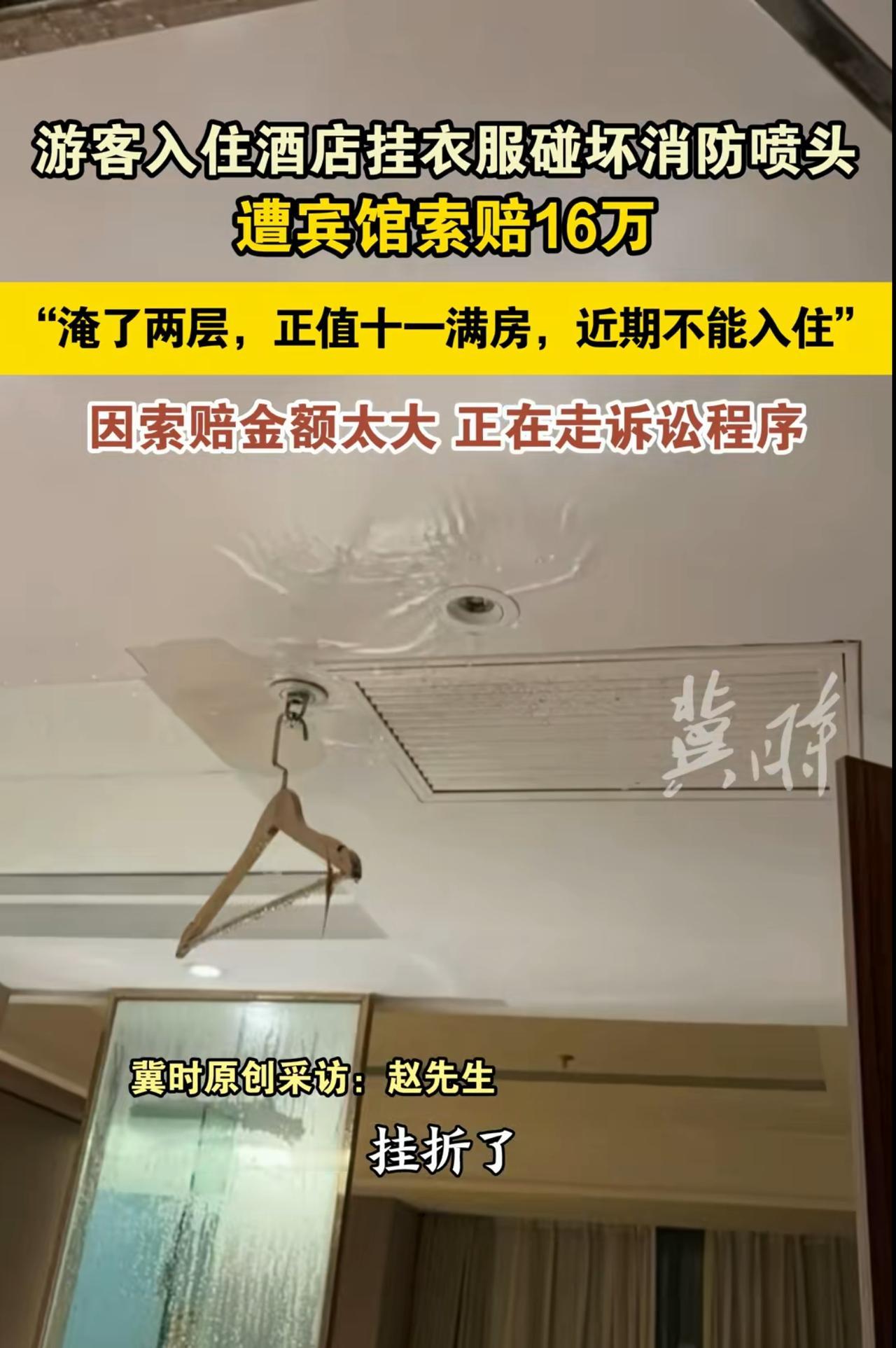青海,一女子与三个男性朋友酒后,与其中一人发生关系,结果猝死。女子丈夫要求3人赔偿,3人理亏,赔偿9万,并签下11万欠条。可一年后,欠款迟迟未付,女子丈夫将三人告上法庭——却没想到,法院的判决完全出乎预料。 2023年12月22日,林某与丈夫赵某因工作分居两地。这天,她与老朋友李某约饭,又拉上两位熟人祁某和张某。席间气氛热烈,四人共饮两斤多白酒。饭后,张某先行离开,剩下三人又一同去了林某的出租屋。 进入屋内,李某与祁某继续饮酒,林某只喝了少量。夜深后,祁某离开,只剩李某和林某二人。酒意上头,两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午夜,李某喝水后在沙发上睡去。 凌晨六点多,李某醒来时,林某已经没了呼吸。 他慌乱地摸了摸她的额头,冰凉无比。他立即用林某的手机联系到她的丈夫赵某。赵某赶到后报了警。 法医鉴定的结论让人唏嘘——林某生前患有脑血管病,那晚饮酒过量,再加上酒后性行为诱发脑出血,最终抢救不及身亡。警方调查后认为,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建议双方协商赔偿。 在派出所调解下,李某承认有疏忽,当场拿出5万元现金并写下5万元欠条。祁某写下3万元欠条并先行支付2万元,张某也出于同情,塞给赵某2万元并签下补偿协议。三人合计赔付9万元,并承诺余下的11万元稍后补齐。 然而,时间一晃过去大半年,赵某始终未收到那11万元,于是携子女将三人告上法院,要求偿还欠款及利息。 但法院的判决,却让赵某无法接受。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虽然有欠条存在,但欠条背后的性质并非单纯的债务关系,而是源自侵权调解协议。法院查明:林某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与饮酒行为共同导致的,李某虽有过错,但祁某和张某未参与劝酒或侵权行为,他们的“赔钱”只是出于同情。 法院最终认定:李某在饮酒及事后未尽到救助义务,对林某死亡负次要责任。林某明知自己患病仍大量饮酒并发生性行为,对死亡结果负主要责任。祁某、张某未存在违法行为,不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仅需再赔偿2万元,其此前支付的5万元视为补偿款;赵某要求的11万元欠款及利息,不予支持。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它同时涉及了侵权责任与民事债务两种法律关系的交叉。许多人看到“签了欠条”,就认为应当偿还,但法律上,“欠条”的性质要结合形成原因来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作为同饮者,酒后与林某发生关系,且事后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没有及时发现并救助林某,其行为构成疏忽过失。但《民法典第1173条》又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或扩大的结果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身体患病仍参与大量饮酒并与人发生性行为,其自身过错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典型的过失相抵原则。 从法院角度看,李某并非完全无辜,但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并不直接。喝酒不是他强迫的,性行为虽存在不当,但缺乏强迫证据。法院在裁量时,更多考虑了注意义务缺失而非故意侵权。因此只判追加2万元赔偿。 反观祁某与张某,他们既未劝酒,也未在事发时在场,对林某死亡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他们支付的钱属于自愿补偿,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债务。《民法典》第566条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换句话说,他们签下的“欠条”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赵某的起诉方向错误,他将一场侵权纠纷误当成了债务诉讼。法院当然不能支持一个缺乏法律依据的还款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还引发了一个社会层面的警示:饮酒聚会不是免责区,朋友关系也不是法律屏障。 首先,从劝酒责任角度来看。若有人明知他人身体不适仍强行劝酒,或未尽照顾义务,导致严重后果的,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类似案例中,已有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95条》判决劝酒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次,针对李某的行为——酒后与醉酒女子发生性关系,若存在违背女子真实意愿或其醉酒无意识状态下发生行为,可能构成刑法第236条的强奸罪。但在本案中,因警方调查未能查出强迫或胁迫证据,未立刑案。 此外,从公共道德角度看,即使不触法,酒后与他人发生关系的风险极高——不仅涉及健康,更可能引发法律与伦理纠纷。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最后,从家庭层面看,林某的丈夫赵某虽失去了妻子,但选择走法律途径维权是理性的。然而法律追求的是事实与责任,而非情感安慰。法院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虽冷,但并非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