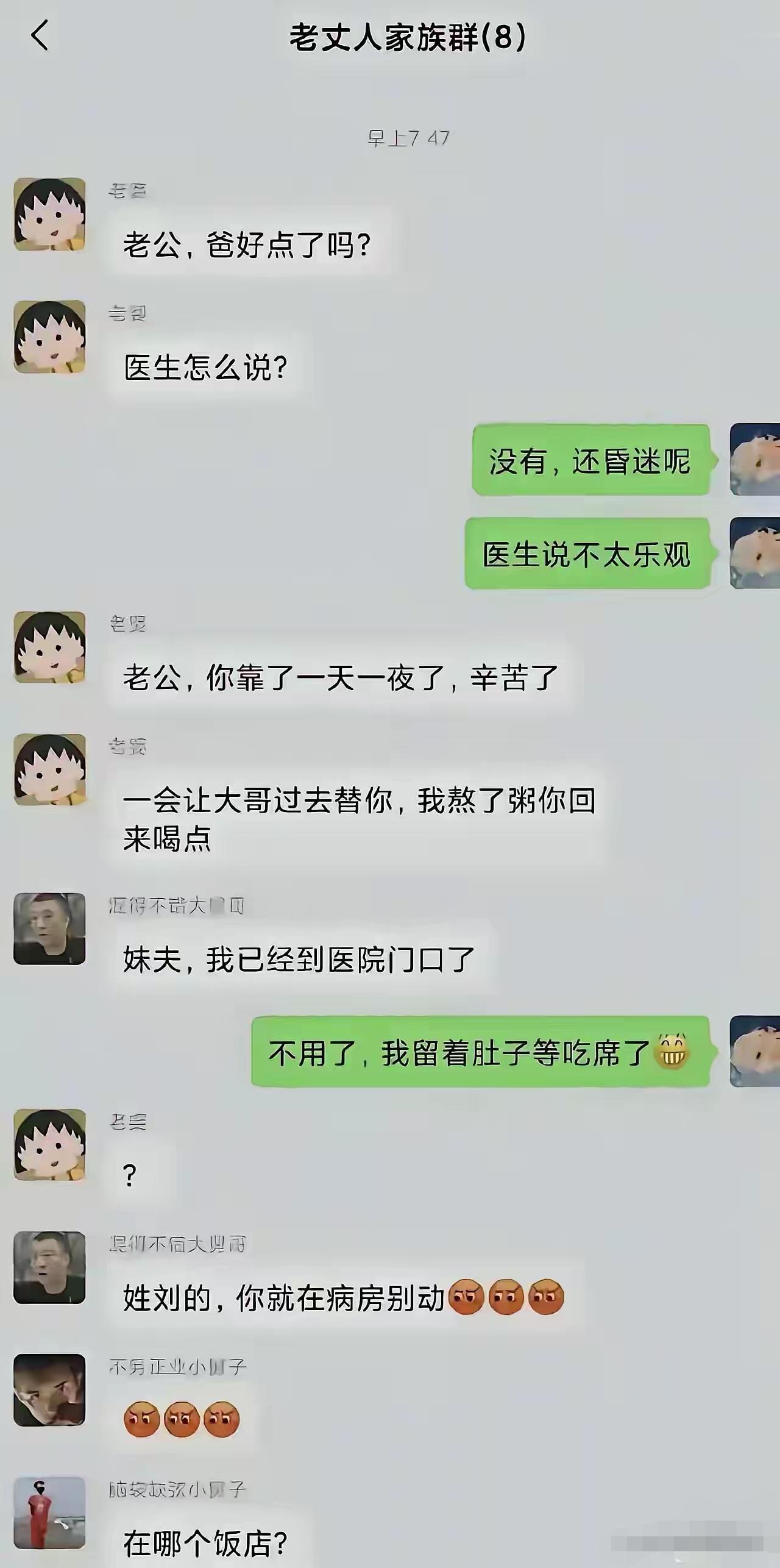1997年,48岁的耿保国不顾妻子反对,借遍亲朋好友又咬牙贷款几十万,终于凑够了120万买下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明清古宅,此后他又把后半辈子的时间,都放在了修缮复原这座老宅上面,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和这座宅子近况如何? 没人知道,耿保国当年揣着那张写满借款人名字的纸条回家时,手心里全是汗。他是河北曲阳人,打小跟着做木工的爷爷在村里老庙打转,爷爷刨木时哼的老调子、卯榫对接时“咔嗒”一声的脆响,早刻进了他骨子里。 20岁那年,村里老庙的戏台梁断了,他跟着爷爷蹲在戏台顶修了三天,看着那些雕着牡丹的木构件重新拼合,心里就埋下个念头:以后要是能守着这么一处老宅子,这辈子就值了。 可1997年那会,他家日子刚有点起色,儿子正准备考大学,妻子靠织棉布补贴家用,120万对他们来说,是把全家架在火上烤的数字。 妻子把刚织好的半匹棉布往炕上一摔,眼圈红了:“娃明年学费还没着落,你借这么多钱买个破院子,是想让我们娘俩喝西北风?” 耿保国没敢反驳,只是把从老宅墙上拆下来的一块雕花木片递过去——那上面刻着两只衔着灵芝的仙鹤,木纹里还留着百年前的包浆。 “你看这手艺,现在没几个人会了,要是拆了盖新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说得轻,却把木片攥得紧,指节都泛了白。 那之后,他没再跟妻子争,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八自行车去老宅,先把院子里的荒草割了,再一点点清理碎砖,晚上回来时,裤腿上全是泥,手上也被荆棘划了不少口子,妻子看在眼里,慢慢没了脾气,后来竟主动把家里的存粮装成布袋,让他带去老宅当午饭。 修缮的难,比耿保国想的还多。老宅的主梁有三根已经蛀了虫,得用百年老松木替换,他揣着干粮往太行山深处跑了十多趟,才在一个老木匠家里找到合适的木料; 窗棂上的雕花断了大半,当地的木匠没见过这种“一榫三卯”的工艺,他又背着铺盖去山西平遥,蹲在古城的老作坊里看老工匠干活,看了半个月才学会; 最急的一次是2003年夏天,连着下了三天暴雨,老宅西厢房的屋顶漏了,雨水顺着梁缝往下渗,他半夜披着雨衣爬上去,用塑料布裹住漏雨的地方,手里的钉子没拿稳,扎进掌心,血顺着指缝滴在瓦片上,他也没顾上拔,直到天亮把漏口堵严实,才坐在房顶上喘粗气——那天他捧着染血的瓦片跟妻子说:“这梁要是糟了,这宅子就真没救了。” 为了凑修缮费,他把家里传了三代的红木衣柜卖了,把儿子攒的学费也先挪了用,儿子起初埋怨他“眼里只有老宅子”,直到有次跟着去老宅,看见父亲蹲在地上,把拆下来的旧钉子一个个敲直了再用,嘴里还念叨“这都是老辈人的心思,不能糟践”,儿子才慢慢懂了。 后来儿子大学毕业,没去大城市找工作,反而回了家,帮着耿保国整理老宅的构件图纸,还学会了用电脑记录修缮过程,父子俩常对着一张老梁的图纸琢磨到半夜。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那座曾经破败的明清古宅,早没了当年的荒败模样。 雕花的窗棂透着光,朱红的大门上挂着“曲阳古建保护点”的牌子,耿保国在宅子里设了个小展厅,摆着他这些年收集的老木匠工具、老宅拆下来的旧构件,每到周末,就有学生来参观,他会指着房梁上的斗拱,给孩子们讲“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一块木头不用钉子,就能架起这么大的房子”。 他头发早白了,背也有点驼,却还每天早上绕着宅子走一圈,摸一摸那些重新拼合的木柱,偶尔还会跟路过的乡亲说:“你看这宅子,现在多精神。” 耿保国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冷冰冰的院子,是藏在木构里的老手艺,是刻在砖瓦上的历史。 他没靠宅子赚过一分钱,却把后半辈子的时光都搭了进去,不是傻,是怕那些老东西没了,后辈就再也见不到老辈人怎么用心过日子。这种守护,比任何财富都金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