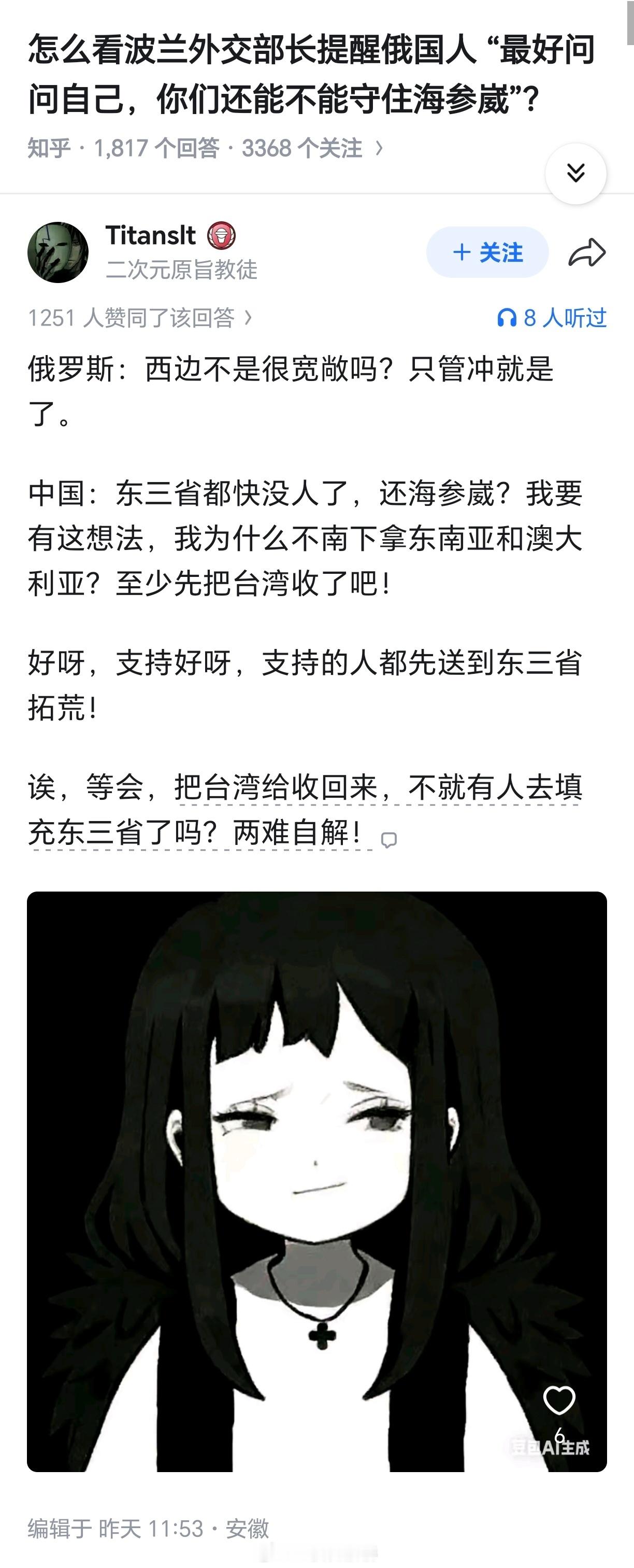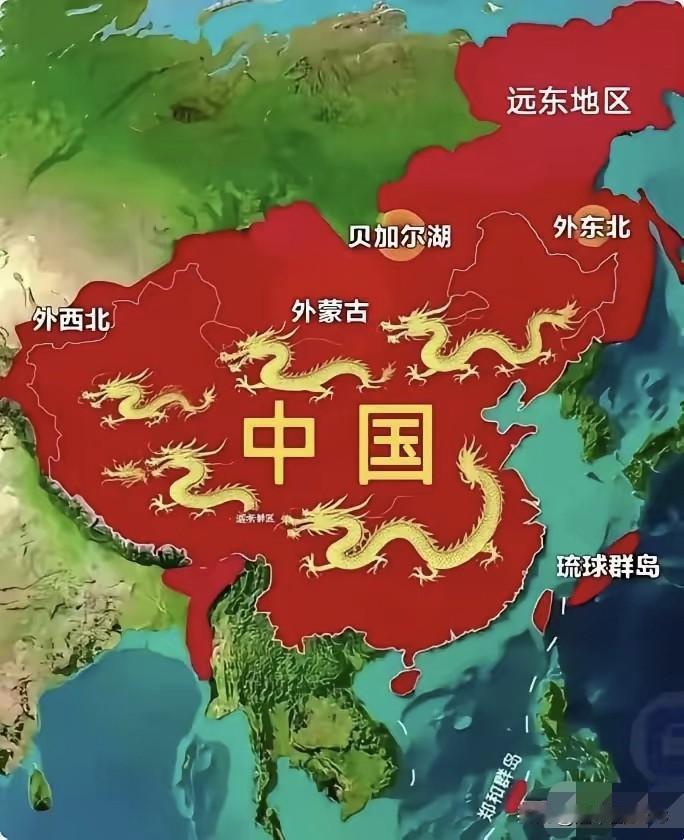1979年,台湾老兵瞒着妻儿寄钱给大陆的原配,没想到妻子居然跟以前的下属“同居”30多年了。 1979年,湖南邵阳黄泥村的空气里,突然多了一丝让人不安的躁动。一封贴着台湾邮票的信,几经辗转,像一块烫手的烙铁被扔进了陈淑珍的家门。 信是易祥寄来的。信封里鼓囊囊的,塞着汇款,还有一张他在台湾的全家福——他身边站着新妻子黄美惠,膝下是四个陌生的儿女。 在那张薄薄的信纸上,易祥用近乎“死刑判决”的口吻写下了一段话:我在那边已经成家了,你也找个好人嫁了吧。陈淑珍的回信,无半分撒泼责骂之语,却道出一个让易祥瞬间崩溃的事实:当年你临行前托付事务的勤务兵庹长发,根本未曾离开。 把时针拨回1949年,那是个混乱到人命不如草芥的年份。易祥接到的撤退命令冷酷得只剩数字:名额仅限两人。一边是身怀六甲的地主千金陈淑珍,她腹中孕育着新的希望;另一边是两个尚处年幼的儿子,他们眼神中满是天真与依赖。 怎么选都是错。陈淑珍做了一个母亲最惨烈的决定:保孩子,自己留下。易祥站在卡车边,眼神落在了跟了自己11年的勤务兵庹长发身上。 彼时,庹长发年仅二十五岁,本是一位忠厚老实之人,却不幸被抓了壮丁,被迫离开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卷入那动荡不安的时代漩涡。当易祥郑重说出:“等我三年,帮我照顾好她们”,那话语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庹长发微微颔首,以这无声动作,应下这份托付。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漫长的出差,却不知道这一下巴点下去,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抵押了出去。 随后的日子,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在空调房里想象出来的。50年代初的农村,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家属是什么成分?那是众矢之的。 村里有人提议要把陈淑珍母子赶走,甚至更激进的想要“斩草除根”。挡在门口的是庹长发。这位即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未曾屈膝的铮铮汉子,此刻,于村长面前,“扑通”一声,毅然决然地跪在了那片泥泞不堪的烂泥地里。他掏出了自己“贫农”的身份证明,用男人的膝盖,给这孤儿寡母换来了一张生存许可证。 为了避嫌,为了不让陈淑珍那大家闺秀的名声在那个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的年代受损,庹长发给自己划了一条死线。 他态度决绝,不肯住进正屋,反倒将自己“塞”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危房。他对陈淑珍的称呼,始终是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太太”,对两个孩子叫“少爷”。无论外面的流言传得多难听,他都没辩解过一句,只是默默地把界限划得像刀刻一样清楚。 如果说伦理上的坚守是精神折磨,那物质上的匮乏就是肉体刑罚。大儿子易浩光要去十几里外的山路上学,脚被石头磨得血肉模糊。庹长发没说话,把自己脚上唯一那双解放鞋脱了下来。 他巧妙地取来稻草与绳子,稍作摆弄改造,便将其妥帖地套在了孩子的脚上,动作娴熟而自然。孩子有鞋穿了,庹长发的脚就只能直接踩在烂泥和碎石上。几年下来,他的脚底板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那几乎成了他的“自带鞋底”,剪刀都戳不穿。 陈淑珍是读过书的小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地里的农活,全压在庹长发一个人身上。为了借邻居家的一头牛耕地,庹长发得去帮对方干三天重活来置换。手掌已然磨出血泡,钻心之痛难以言表。然而,他毅然决然地挑破血泡,稍作忍耐后,便又投身于手头的事务,继续那未竟之业。 到了困难时期,他更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筛子,把能吃的粮食都漏给母子三人,自己去挖野菜、扒树皮。他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宏大叙事,他脑子里只有一根筋:答应了长官,就要做到。 而在海峡那头,易祥的日子过得像个分裂的平行宇宙。50年代,他还死死攥着那张写有儿子名字的“授田证”,那是他反攻回家的唯一念想。 然而,时间堪称最为冷酷无情的腐蚀剂。它悄无声息地侵蚀一切,无论是繁华盛景,还是炽热情感,都难以逃脱其消磨,尽显岁月的残酷本色。到了60年代,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绝望、自杀或者再婚,易祥心里的那盏灯灭了。他把大陆妻儿的照片锁进了一只铁皮箱,那是他的禁地。他迎娶了黄美惠,生儿育女,试图在台北的雨夜里麻醉自己。 直到1979年那封回信,彻底击碎了他的伪装。他以为自己是无奈的受害者,结果对面站着一个圣徒般的庹长发。 易祥开始了漫长的赎罪。他不断向大陆汇款,不想此事被台湾的子女察觉,家庭关系由此陷入冷战僵局。他的这一坚持,虽引发家庭风波,却也凸显其内心的那份执着。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在1987年病重弥留之际立下遗嘱,里面6次提到了庹长发。 他于遗嘱中留下一句分量极重的评语:“此人质朴正直,恪尽职守,真乃吾弟也。若无庹弟,家不存。”这是一个军官对一个勤务兵最高的敬意,也是最深的忏悔。 1949年那个25岁的小伙子点头承诺时,以为是三年。结果这“一点头”,就是整整这一生。在那个人心还没有变得浮躁的年代,庹长发用他那双赤脚和那一身老茧,给“承诺”二字下了一个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定义。 信息来源:《真实记录:人性的光辉感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