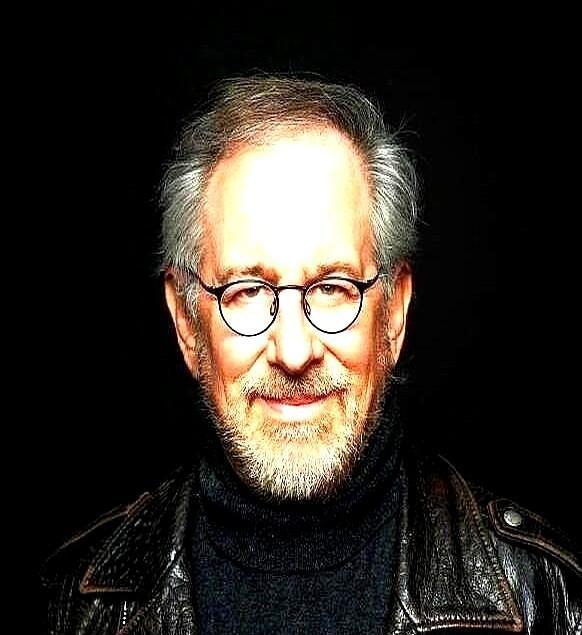其中,史泰龙摄的《第一滴血》反响尤为强烈。 这部电影上映于1982年,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尚处于80年代的冷战阶段。 好莱坞很清楚像《第一滴血》这类影片在某些与前苏联友好的国家上映时是不会卖座的。 当时,电影在中东,以及跟前苏联友好国家的广泛播放的《第一滴血》时,都把故事发生地点从越南改为菲律宾。 事件也现代,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影片中的坏蛋和敌人(越南人和俄国人)也因情节的改动改成了日本人,因为俄国人是许多中东国家的强有力的同盟国。” 在银幕上,美国兵总是受害者,美国政府总是被蒙蔽的一方,真正的坏蛋永远是别人。这种叙事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全世界都学会了用美国电影的视角理解美国。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现实中的超级大国,又是幻想中的理想国。 它输出的不仅是商品与武器,也是故事和梦境。当全世界都在讨论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时,美国电影却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美国人的困惑与反思。 纵观美国电影史,战争题材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叙事场域。一方面,有《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这样歌颂美军英勇的作品; 另一方面,也有《现代启示录》、《猎鹿人》、《野战排》、《全金属外壳》、《细细的红线》这样深刻反思战争创伤的杰作。 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性,恰恰是美国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体现。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媒介,美国社会得以在虚构叙事中完成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对创伤的集体疗愈,对道德的持续追问。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反思往往以"承认错误"的方式进行,从而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 当美国电影承认越战是"错误的战争"时,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叙事上的自我赦免。 承认过去的错误,也许是为了掩盖维护当下的正当性。






![[吃瓜]《阿凡达3️⃣》上映23天,中国内地票房终于过十亿…确实是“费老大劲](http://image.uczzd.cn/1126048546240527769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