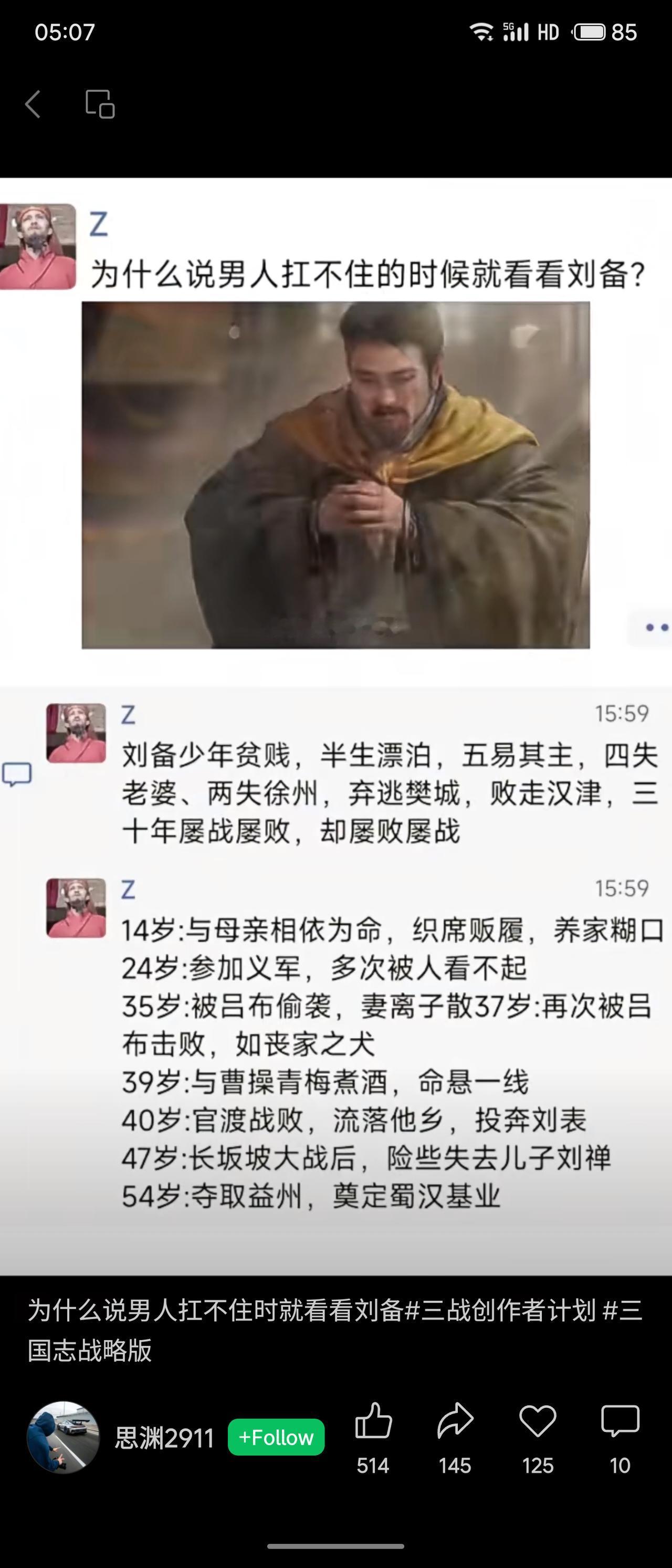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十天不愈,病情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一九七四年冬天,医院手术灯打在毛主席脸上,人已经八十多岁,双眼几乎看不见。 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盯着显微镜,手上捏着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金针,准备给他做“拨障”。这种法子在书上早就写成“失传”。台下警卫、医护都不敢出声。 这台手术背后,其实挂着一条线,线头拴在一九五七年那场青岛重感冒上。 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的海风有气无力,毛主席住在那边,一场感冒死死缠上来。 十天高烧不退,人明显虚了下去,西药吊着用,效果跟白水差不多。 保健医生盯着体温表,手心一直是汗。这时候,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提了个建议,说本地有个老中医刘惠民,用药猛,见效快,可以请来试试。 话刚说完,屋子里气氛立刻变了。 赞成的人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反正西药压不住;反对的人心里只冒一个念头:领袖的身体能不能拿“带毒性”的药材去赌。 刘惠民被请到青岛,先是把脉看舌,又静了一会儿,这才开方。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不是普通病号。 为了放心,他提了几条规矩:处方先给主席原来的医生审一遍,抓药、煎药由舒同的爱人石澜亲自盯着,药端进屋时,大家一起看着主席喝下去,有什么反应当场记录。 舒同点头答应,把话挑明。 刘大夫的药,自己和省委不少同志都吃过,效果确实好,如果真出了什么不测,就由他和爱人担责任。 秘书把争论来龙去脉都跟毛主席说了。 毛主席听完,笑了一下,语气不紧不慢,说舒同既然保了,就照这个办法来,药还是要喝的。那种态度,不像不顾一切冒险,更像把专业、把责任都推到明处。 第一副汤药喝进去,指望中的“立竿见影”没有出现,病情没抬头。 屋子里的眼神开始有变化,有人悄悄对视,有人盯着地板发呆。刘惠民没吭声,又重新审方,把几味关键药的量往上加了一点。 第二副药煎出来,味道更冲,毛主席喝完不久,身上开始出汗,被褥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就从那晚起,体温慢慢往下压,人也有了精神。 第三副药跟上,咳嗽轻了,头也不那么昏,睡觉能一觉到天亮。 毛主席对这几付药起了兴趣,不光关心治好了没有,还琢磨方子里的门道。 他叫来石澜,指着其中一味酸枣仁发问:为什么既要生的,也要炒熟的,还得捣在一起用,这样折腾究竟有什么讲究。石澜早就跟着抓药、煎药,心里有数,说酸枣仁本来就有门路,生的提神,炒熟的安神,一起下锅,对中枢神经是个平衡,既不让人过度兴奋,又能把心安下来。 睡眠稳了,抵抗力顶上去,感冒就好办多了。 毛主席听完,笑得更开,说舒同有个好内当家,讲起中医头头是道,将来还可以去当医生。 玩笑里带着欣赏,对中药这条路的信任也从那时开始扎得更深。后来他外出访问,去莫斯科那次,也让刘惠民跟着,一路照看身体。 时间往后一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又感冒,这回病情没上次那样凶,但咳嗽拖得久。 他躺在床上,忽然问起一个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词:“上火”。刘惠民就用中医里阴阳、火热那一套说了一通,话挺专业,也挺绕。 毛主席听着摇头,笑着说,这些说法太悬,脑子转不过弯。 刘惠民想了想,换了种说法。 他说主席熟悉的是西医的那一整套,如果学过一点中医,再来听这些词,感觉就会不一样。 意思是,两种体系要互相通气,不然就容易鸡同鸭讲。毛主席听到这里,神情亮了一下,说关键在于西医也要学中医,两边都懂一点,说话才对得上茬。 这一句看似闲聊的话,在一九七四年的那台手术上算是落了地。 那时候白内障已经把毛主席的视线遮得差不多了,普通人早就坐不住,他还在跟医生讨论方案。 唐由之带着团队琢磨出来的“金针拨障”,既有现代手术的台子、灯光,也借了中医传统的思路。开刀那天,室内安静得能听到器械轻轻碰撞。 手术结束拆纱布,毛主席抬起右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唐由之笑着说,这次成功,多亏中西医搭起了一座桥。 外界常提到一句话,说中国对世界有几样拿得出手的东西,中医总是被摆在前面。 把青岛那几付汤药、那句“西医也要学中医”、再加上七十年代的那台手术连在一起看,这种评价就不显得突兀。 十天高烧压不下来的焦虑,老年性白内障带来的黑暗,都逼着人去寻找更合适的路子。 对毛主席来说,中医不是摆在架子上的“国粹”,而是要真能顶事、说得清道理、用得起用得住的东西。 青岛屋子里飘着药味的那个夏天,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改变了后面很多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