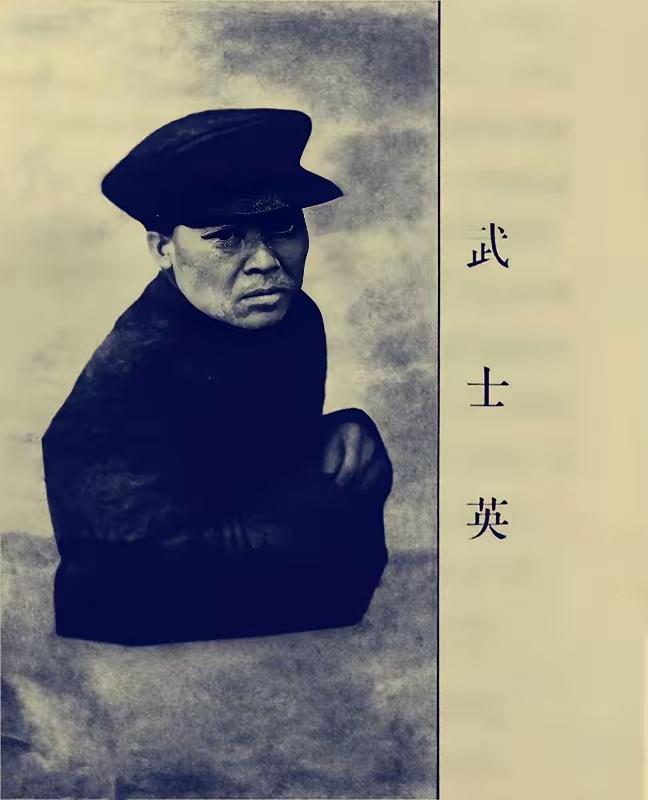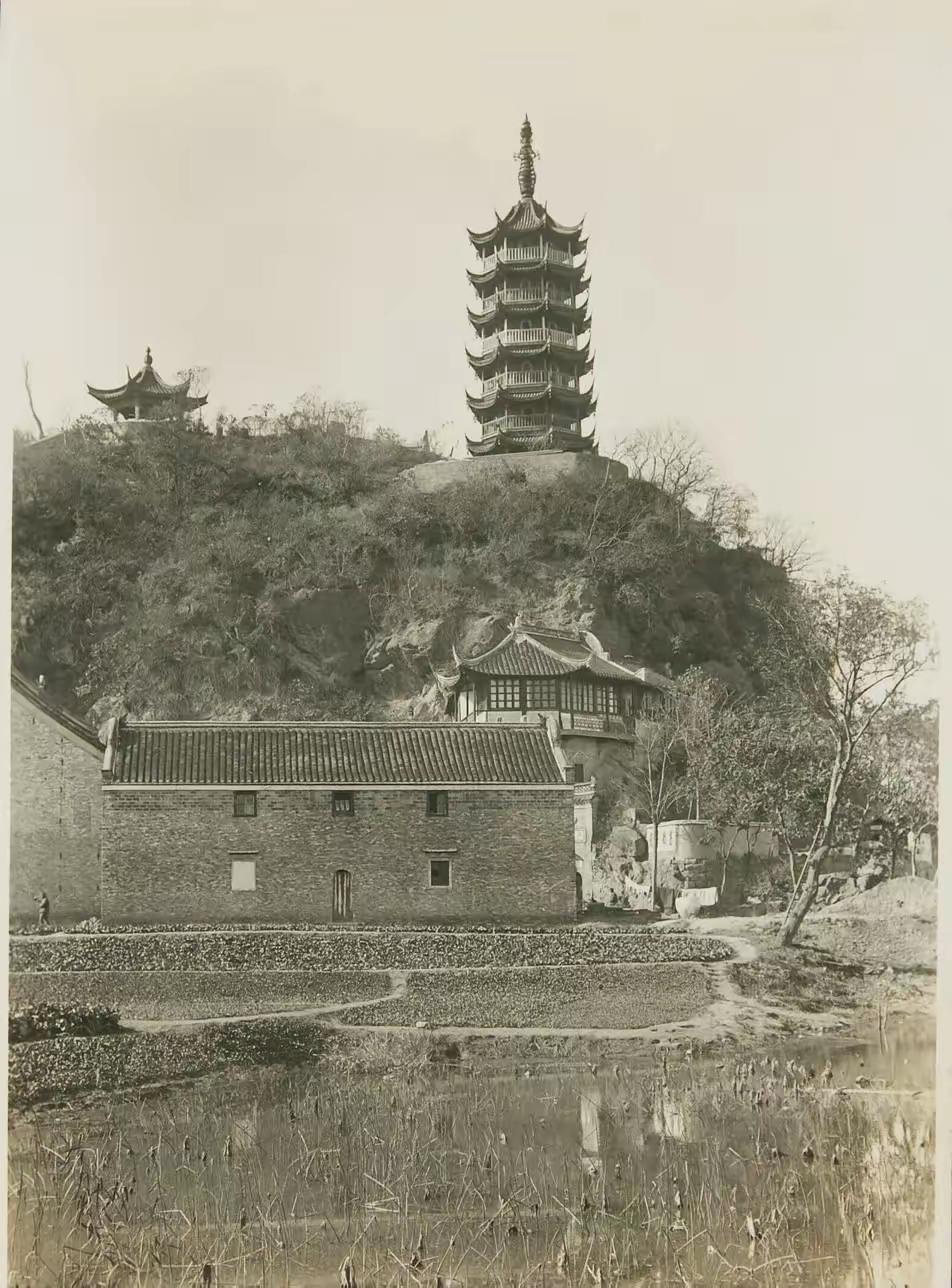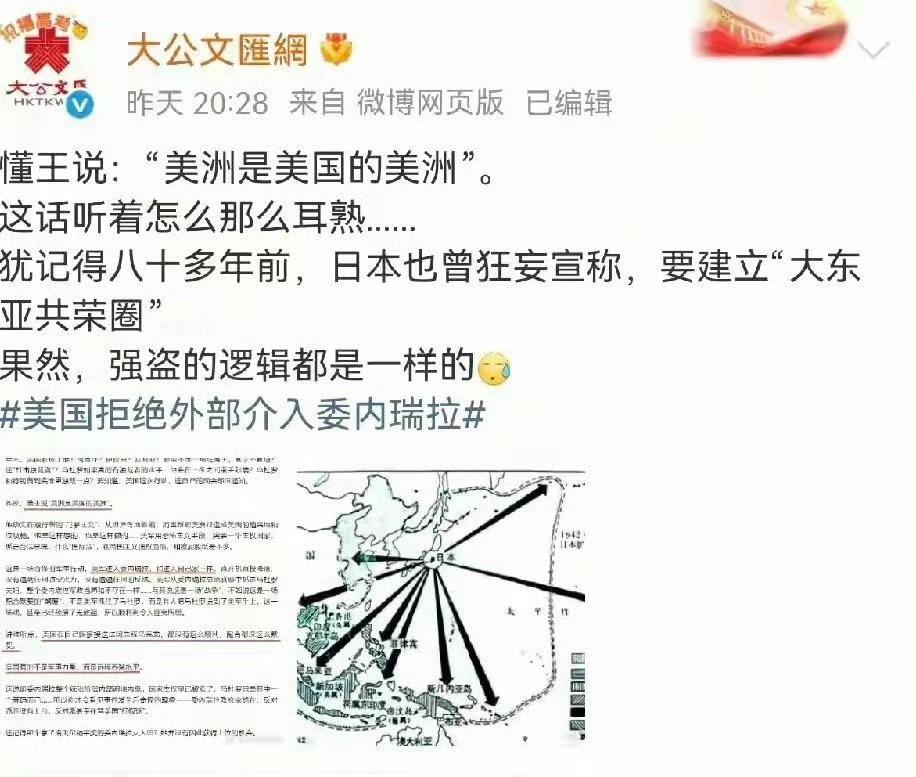1941年秋夜,皖南山区的雾气裹着寒气往骨头缝里钻。 刘奎攥着刚写好的会议纸条,抬头却看见队员王德背对着他,双手在身后攥得死紧,“队长,我头疼得厉害,今晚的会……”话没说完,人已经往住处挪。 山里的夜比墨还浓,王德的脚步声却轻得反常,像踩在棉花上。 刘奎捏着纸条的手指泛白。 王德平时散漫归散漫,扛枪打仗从没含糊过,更别说缺席决定生死的军事会。 他悄无声息跟上去,快到王德住处时,听见“哐当”一声闷响,像是什么铁器砸进了屋后的草丛。 推开门的瞬间,王德正对着墙角的煤油灯发呆,地上的影子被拉得歪歪扭扭,手里还残留着木屑那是把磨得发亮的斧头,刃口还沾着新土。 “叶保长说,解决你给两千大洋。”王德突然转过身,膝盖“咚”地砸在泥地上,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我喝多了就应了,可走到你门口,看见你窗台上晾着的补丁袜子……那是上次突围时我划破的,你连夜给缝的。”刘奎这才注意到,王德怀里揣着个油纸包,露出半块没吃完的麦饼,是队里昨天刚分到的口粮,他自己都没舍得吃。 刘奎弯腰捡起地上的斧头,木柄被攥得温热。 皖南的保甲制度像张密网,五家连坐,一人通共全家遭殃。 叶保长抓着王德老娘的病,用半块大洋和一句“事后就送药”,就把这老实人逼到了墙角。 他把斧头往墙角一靠,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这斧头要是真劈下来,你老娘的药钱,这辈子都还不清。”那晚,两人就着煤油灯坐了整夜,直到窗纸泛白,王德才把叶保长给的那半块大洋掏出来,塞进灶膛烧了。 转过月,刘奎带着王德几个人摸到庙首乡公所。 伪警察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在门口打盹,他们换上从伏击战缴来的国民党军装,大摇大摆往里走。 乡公所里的步枪靠在墙角,机枪挂在墙上,像等着人来拿。 王德第一个冲进去,枪托砸在桌角,把正在数钱的伪乡长吓得瘫在地上。 后来才知道,这种乡公所按规定配5支步枪,可他们愣是缴了12支原来伪乡长偷偷把邻乡的枪也藏这儿了。 王德事件后,刘奎在队里立了条规矩:每周三晚上不开会,改成“说心里话”。 煤油灯把土墙上的斧头影子投在每个人脸上,有人说想家,有人说怕枪子,王德总是最后一个开口,话不多,却字字扎实:“以前觉得打仗是为活着,现在才明白,咱们护着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还有山那边老乡的炊烟。”看着王德说这话时眼里的光,我觉得刘奎当时没劈下那斧头,劈的是队伍里的散沙,聚的是人心。 后来那把斧头被刘奎挂在开会的土墙上,每次“说心里话”前,他都要摸一摸斧刃。 1943年春天,队伍在旌德打伏击,王德抱着机枪往山坡上冲,子弹从他胳膊擦过,血顺着枪管往下滴,他愣是没松手。 战斗结束后,刘奎给他包扎伤口,他指着远处老乡屋顶的炊烟笑:“你看,那烟比上次浓多了。”绝境里的队伍,从来不是靠武器锋利,而是有人愿意把私心磨成刀刃,护着身边的人,护着那些冒着热气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