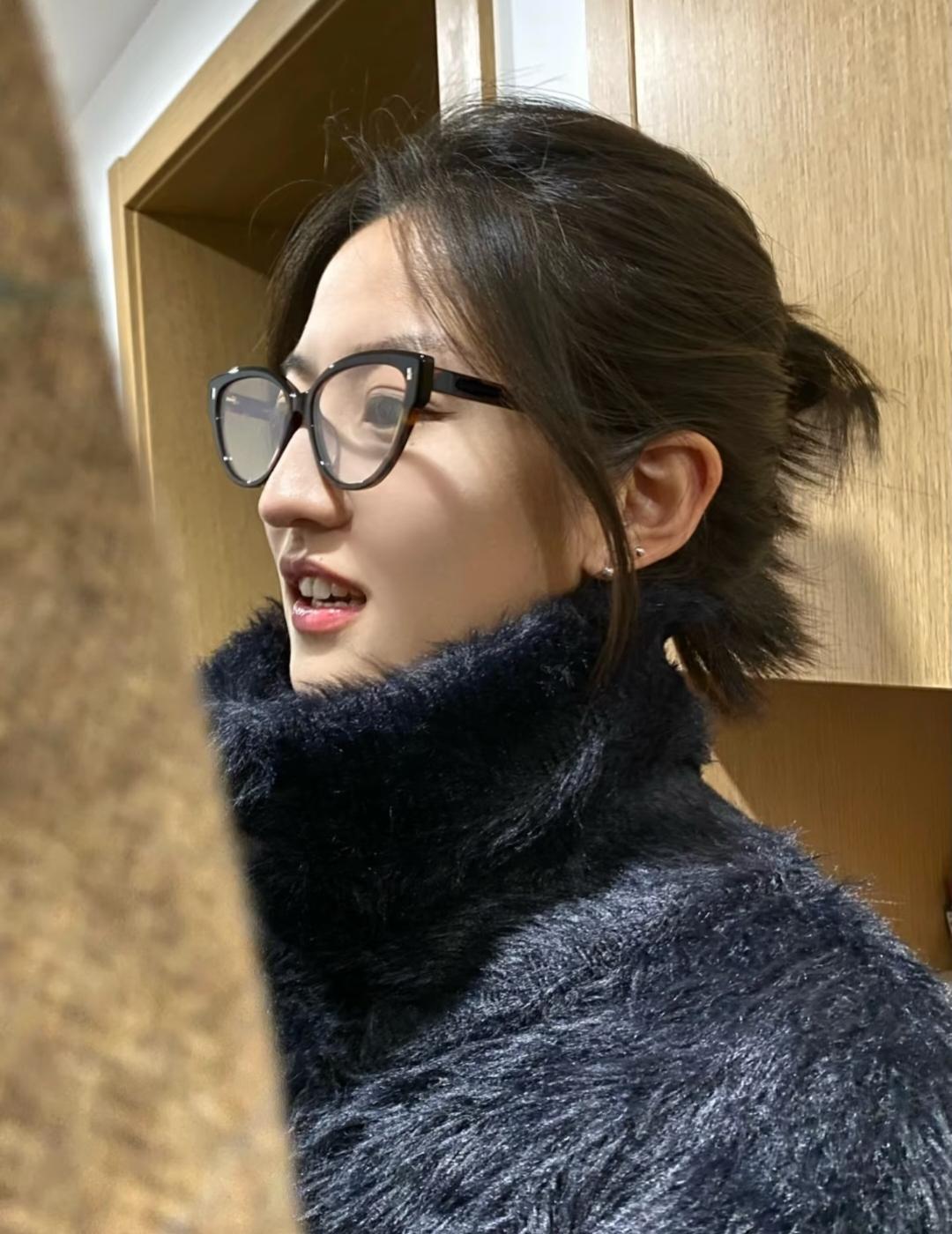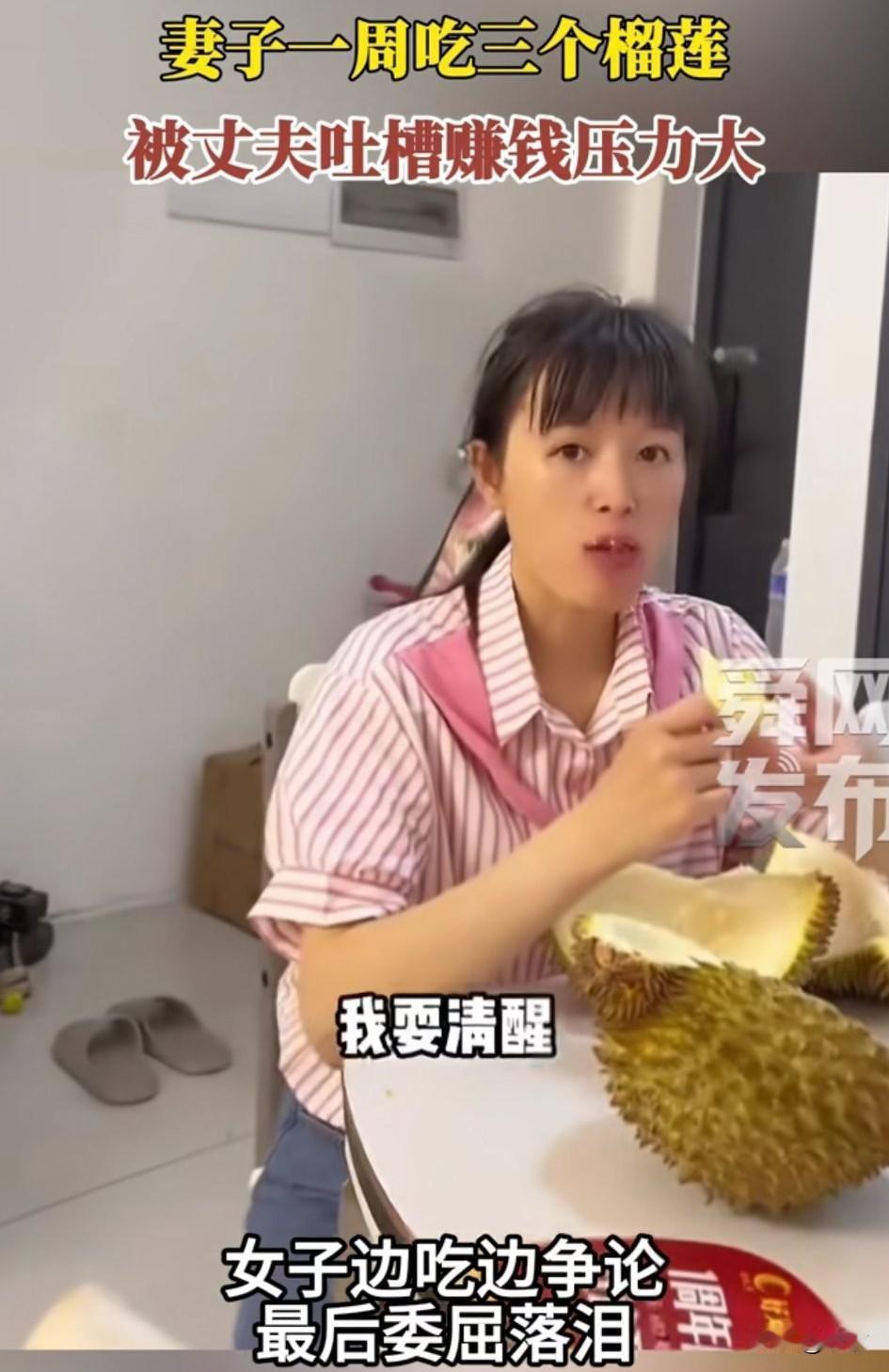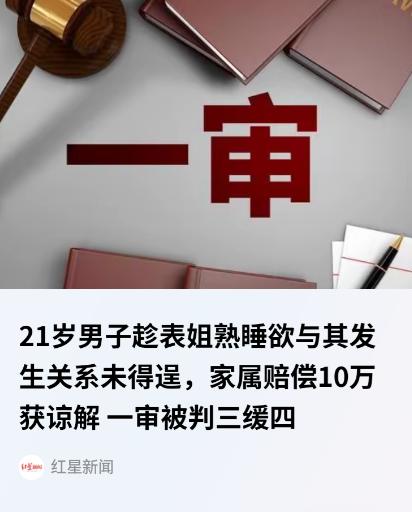我入赘了,娶了市长家智障20年的女儿,新婚夜刚在地上铺床,她突然坐起来说:装傻整整二十年,就是在等你 在这栋贴满喜字的豪宅里,最昂贵的家具不是那张雕花的红木大床,而是镶嵌在吊顶灯边缘、那枚针眼大小的黑色镜头。 陆明跪在地上铺被褥,手心里全是冷汗。十个小时前,他在婚礼聚光灯下还是个为了母亲透析费甘愿入赘的窝囊废,卑微地给据说智力只有三岁的妻子擦口水。此刻,波斯地毯的触感有些扎手,他刚想把枕头摆正,身后那道原本浑浊痴傻的目光,突然变得像数九寒天的冰棱一样锋利。 床上的沈雨晴早已不见了白天抱着毛绒兔子傻笑的模样,她正对着天花板上的那个黑点冷笑,手里抛着一枚有些年头的老旧玉坠。那是一块陆明母亲留下的旧物,也是十年前他在护城河救起落水女孩时给出的信物。 陆明还没来得及开口,沈雨晴就光着脚跳下了床,一把拽过他拖进了卫生间。水龙头被猛然拧到最大,哗啦啦的流水声瞬间充斥了逼仄的空间。借着水声掩护,她贴在他耳边,声音比那玉坠还要凉:“那不是蚊子,是监视器。装傻这二十年,我就是在等你。” 这一刻,所有破碎的线索在他脑海里闭环了。沈家二楼那条曾经发生过“意外”的楼梯,二十年前那颗也是有人故意递给她的糖,还有陆明父亲作为烈士牺牲背后被封存的档案,源头都指向那个看似和蔼的“好叔叔”——副市长王建斌。 这场戏,还得继续演下去,而且得演得比真的还真。 在这个家里,不仅是卧室,连保姆、司机都是王建斌布下的眼线。陆明的策略很直接:示弱,贪财,做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早餐桌上,他故意打翻了牛奶,一边手忙脚乱地擦拭,一边对着满脸鄙夷的保姆赔笑脸。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成功取悦了坐在主位看报纸的王建斌。就在前两天,陆明刚发现母亲在医院的透析液批次出了问题,背后供货商正是王建斌亲戚控制的壳公司。这笔账,他一直记着。 机会来自那个暴雨夜的“试探”。王建斌把他叫到金碧辉煌的会所,几杯酒下肚,开始用所谓“暴利拆迁项目”诱惑他。陆明把酒杯压在掌心,半真半假地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望,顺着桌沿倒掉大半杯酒,只为了换来那几句酒后的真言。 “只要听话,港口那批贴着‘慈善捐赠’标的货,少不了你的好处。”王建斌拍着他的肩膀,眼神里全是看狗的轻蔑。但他不知道,此时陆明的手机正在口袋里静默录音。 拿到外围证据还不够,真正的死穴藏在这个家的心脏。 那个午后,沈雨晴突然“犯病”了。她像头发狂的小兽,尖叫着冲进了严禁任何人踏入的二楼书房。陆明在后面假意追赶,甚至在好几次快抓到她衣角时故意放慢了脚步,嘴里喊着“小心”,脚下却在把周妈和其他佣人往外挡。 书房里传来一声巨响,那是价值连城的端砚砸在地上的声音。 在满地墨汁与碎片中,沈雨晴把视线投向了那幅沈老爷子的巨幅画像。趁着外面乱作一团,陆明跪在岳父面前痛哭流涕地揽下责任,却借着“修补砚台赎罪”的名义把自己留在了书房。当门缝外的脚步声远去,他搬起梯子,颤抖着手指在画像后的暗纹上摸索。 父亲留下的军功章编号,就是打开这道历史伤疤的密码。 机关弹开的瞬间,尘封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个隐秘的夹层里,躺着一本黑色封皮的旧账本和几张泛黄的照片。那是老一辈人在生死线上抢回来的罪证——地下钱庄的洗钱网络,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个节点,以及那些在阴影里握手的名字,都在这几页薄纸上。 最后那个夜晚,风特别大,吹得窗框哐哐作响。 卧室门把手被人悄悄划了几道痕,地毯上多了一枚陌生的鞋印。陆明和沈雨晴对视一眼,他们知道,没有时间了。王建斌的警觉性比预想的还要高,那种被猎食者盯上的寒意已经顺着脊背爬了上来。 陆明将门反锁,沈雨晴利索地掀开床边的地毯,那是她藏了二十年的暗格,里面除了早年收集的磁带和录音笔,还有陆明刚从书房带出来的那个微型U盘备份。 屋里的电闸突然被拉断,四周陷入死一般的黑暗,只有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亮了两人的脸。 他们将所有证据打包,连接了隐蔽的热点,目标是纪检委的加密通道。传输进度条开始缓慢爬升:15%,30%…… 走廊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人在试钥匙,金属摩擦锁芯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如同惊雷。紧接着是沉重的撞击声,门锁开始剧烈晃动,显然外面的人已经不想再装了。 “快点,再快点。”沈雨晴死死盯着屏幕,额角的冷汗顺着脸颊滴落。陆明咬着牙,搬起沉重的欧式沙发顶在门后,用身体死死抵住最后一道防线。 门缝里透进一丝凉风,外面有人低声咒骂,还有器械撬动的声响。进度条跳到了98%,那该死的圆圈还在转动。 窗外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车灯,楼下原本沉寂的街道上传来了不同寻常的嘈杂脚步声,那是早已埋伏好的另一股力量到了。 就在这一刻,屏幕上的数字终于定格在了100%。光芒瞬间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