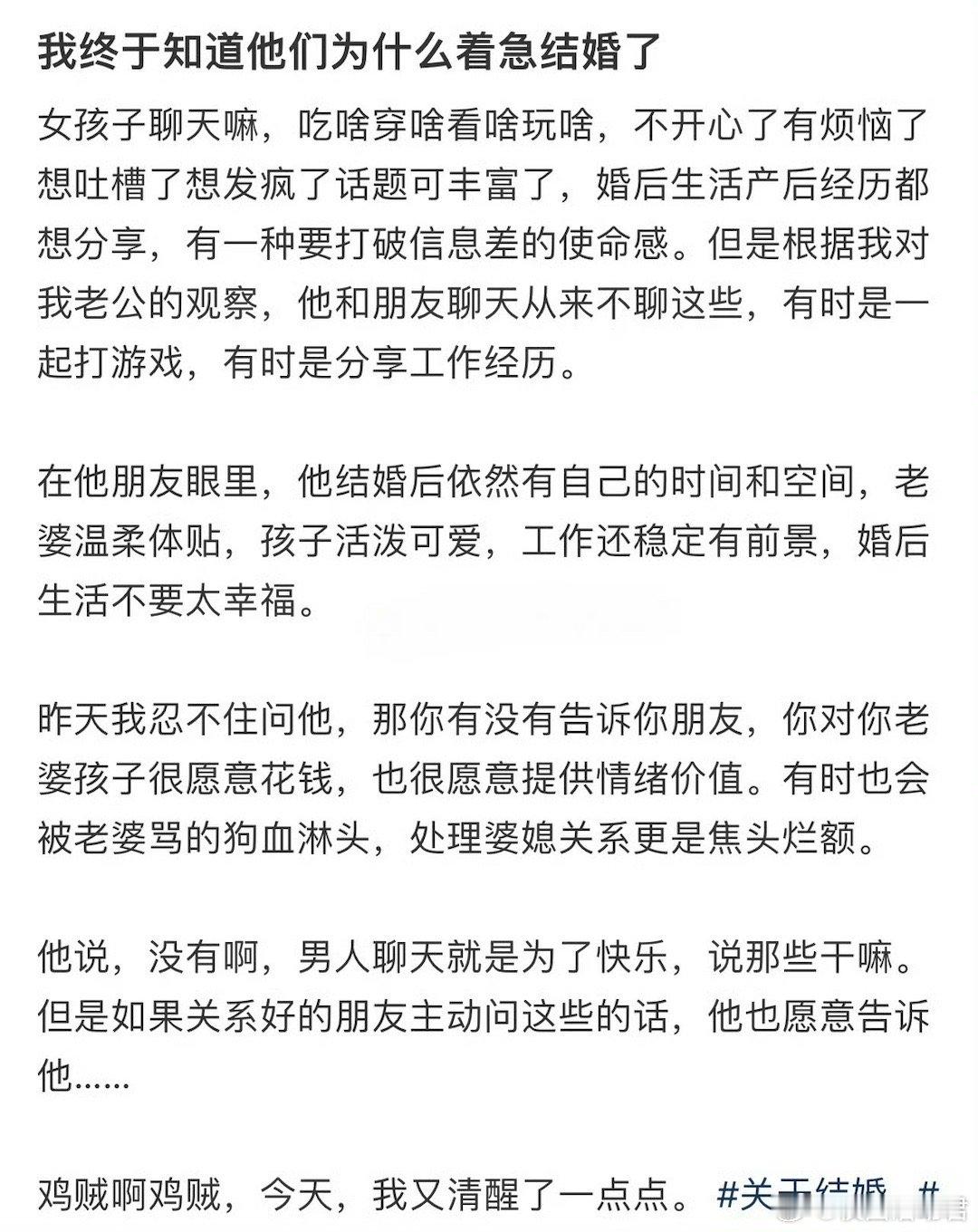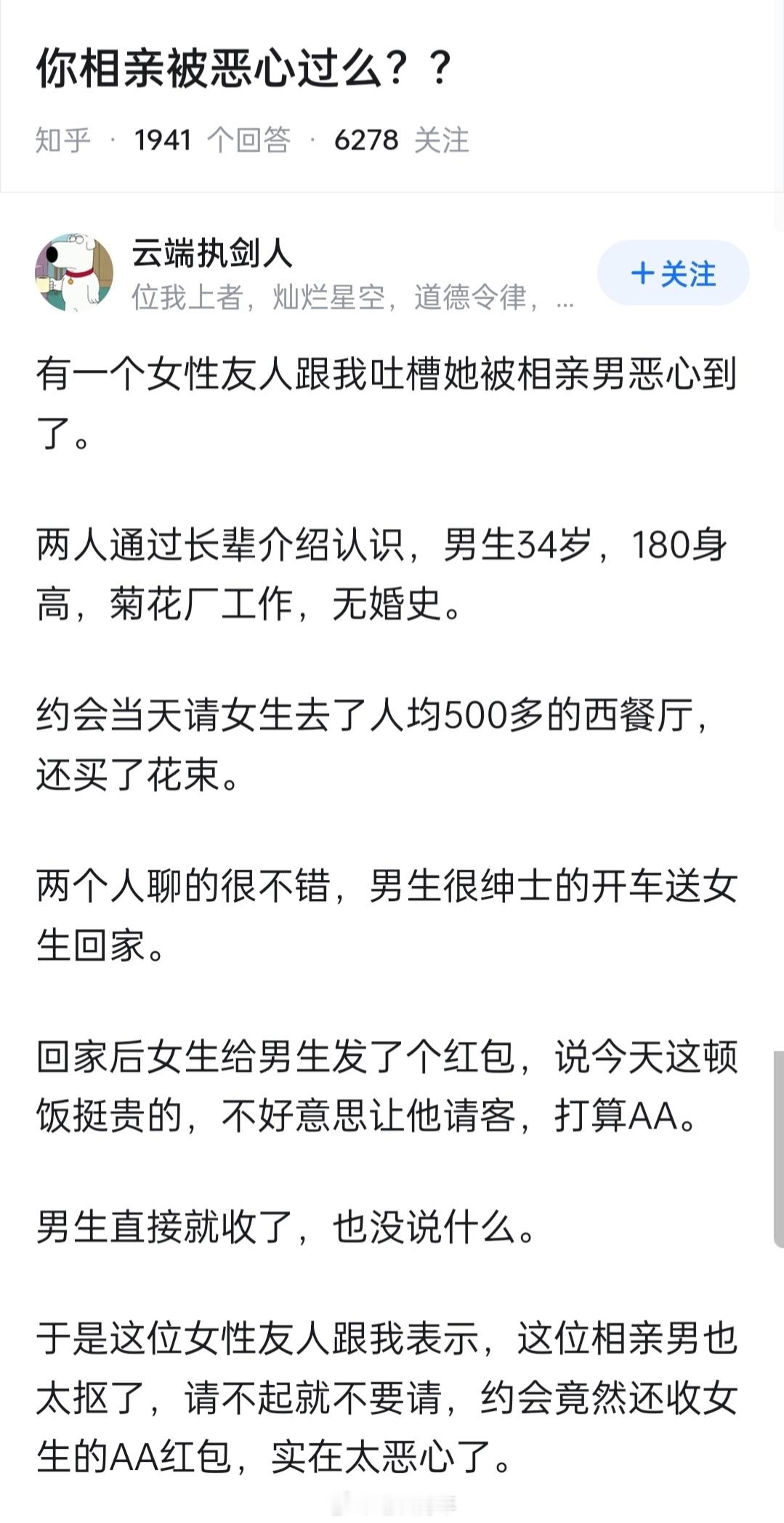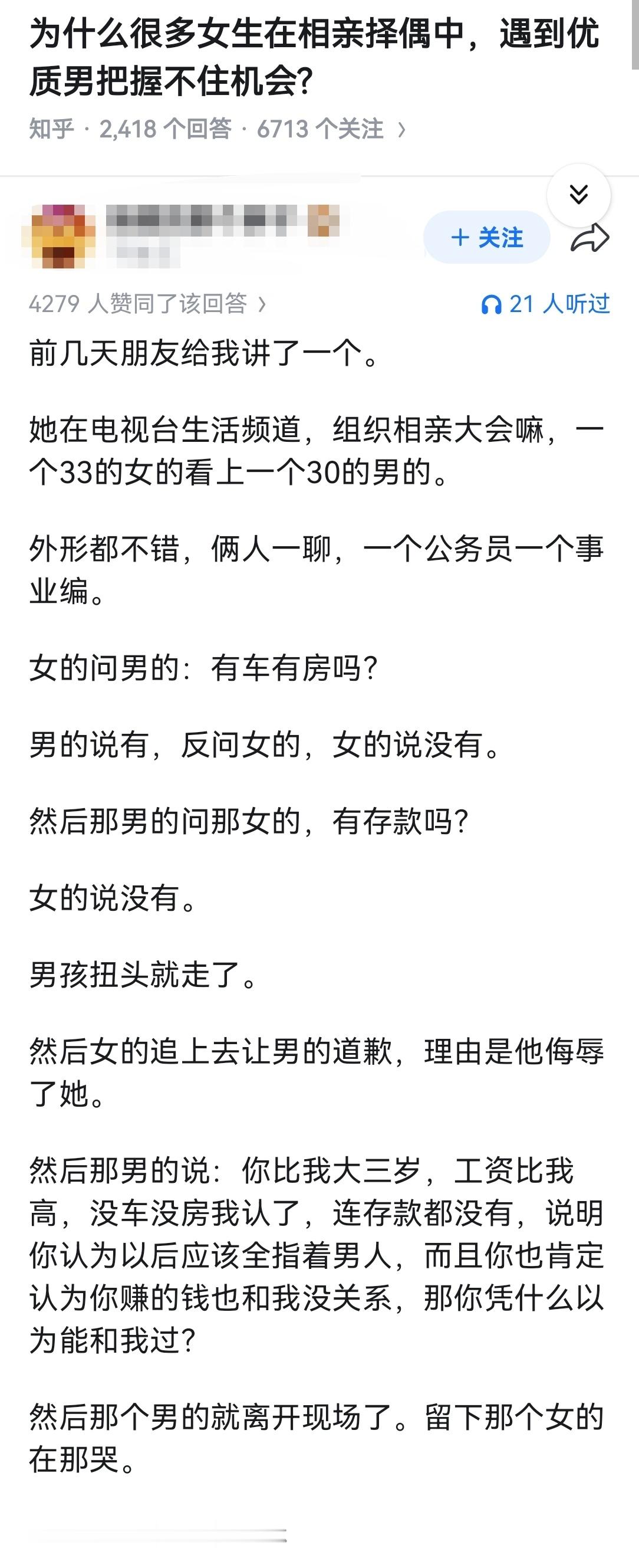我跟我老婆是相亲认识的,刚结婚的时候,我不喜欢我老婆,甚至嫌她烦。实话实说,一开始我们都有点排斥对方,但架不住两方家里人催,然后我们硬着头皮结婚了。 婚后头半年,我们过得像合租室友。她住主卧带阳台,我占着次卧书桌,客厅沙发中间永远隔着一个抱枕的距离。她每天下班就窝在阳台摆弄那台老掉牙的胶片相机,镜头擦得锃亮,洗出来的照片全是些犄角旮旯——窗台的裂缝里长出的三叶草,楼下流浪猫打哈欠的侧脸,还有我扔在垃圾桶旁边、没喝完的半瓶矿泉水瓶底。我呢,周末就把自己关在次卧拼乐高,从城堡到飞船,零件散落一地,她路过时总会绕着走,眉头皱成小疙瘩,却从没说过一句“乱”。 第一次觉得她不那么“碍眼”,是在结婚第七个月。那天她蹲在阳台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兽。我端着水杯路过,瞥了眼她手里的相机,快门键卡在一半,胶卷仓盖松松垮垮。“卡住了?”我没话找话,她抬头瞪我,眼睛肿得像桃子:“要你管!”我没走,把水杯放茶几上,蹲下来摆弄那相机——其实上周我就见她对着说明书唉声叹气,偷偷在网上查了同款机型的维修教程。拆开镜头盖,用镊子夹出卡在齿轮里的一根头发丝,再把松掉的螺丝拧紧,“咔嗒”一声,快门动了。她盯着相机看了半晌,突然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塞我手里,橘子味的,糖纸皱巴巴的,“谢…谢了。” 你说这世上的感情怪不怪?明明一开始谁都没打算对谁好,怎么就在递糖、修相机、找零件的这些小事里,把心给焐热了呢?从那以后,沙发中间的抱枕不知何时消失了。她会把洗好的照片摊在茶几上,指着那张我拼乐高时皱眉的侧脸说:“你认真的时候,眉毛像个倒过来的V。”我会把拼好的小机器人放在她相机旁边,看她拍照时机器人的影子会不会跑进镜头里。有次我拼一个绝版的星舰模型,说明书缺了最后两页,急得抓耳挠腮,她一声不吭出门,跑了三家旧货市场,拎回一本泛黄的杂志,里面夹着个读者投稿的模型攻略,边角还沾着咖啡渍。 去年冬天我妈住院,我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回家时推开门,看见她把我妈常坐的藤椅搬到阳台,垫上厚厚的棉垫,藤椅旁边摆着我妈爱吃的蜜饯,玻璃罐擦得能照见人影。她蹲在地上擦藤椅腿,听见动静抬头,脸上沾着点灰尘,像只刚偷吃完米的小仓鼠:“妈出院了就能坐这儿晒太阳,她不是最爱看楼下的鸽子嘛。”那一刻我鼻子发酸,走过去蹲在她旁边,跟她一起擦那冰凉的藤椅腿,心里却暖烘烘的。 现在结婚六年,前几天整理衣柜,翻出她当年的红嫁衣,缎面上的金线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不像刚结婚时觉得俗气,倒像是把星星都缝在了上面。昨晚她趴在沙发上修相机,我凑过去看,她突然把相机转过来对着我,“咔嚓”一声,闪光灯晃得我眯起眼。照片洗出来,我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嘴角却咧着,背景里是她没来得及收拾的相机零件,还有我随手放在茶几上、给她泡的蜂蜜水,水温刚好不烫嘴。原来日子就是这样,你修你的相机,我拼我的乐高,偶尔递颗糖,偶尔找个零件,不知不觉就把两个人的影子,叠成了一个。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着急结婚了
【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