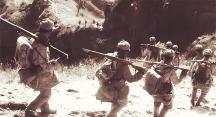1941年的一天,八路军刘锡坤在地主儿媳新房过夜,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只细手在他身上乱摸,立马抬起一脚踹了过去。 冬夜的月光透过窗棂,把院子里的老槐树影投在土墙上,像张牙舞爪的鬼影。 刘锡坤攥着枪的手心全是汗,这已经是他在冀中根据地边缘借宿的第三个村子了。 地主家的西厢房透着诡异。 按理说借宿的八路军战士都该住牲口棚旁的杂屋,可这家非要把他往儿媳新房让。 那会儿他只当是老乡客气,现在想想后背直发凉。 踹出去的脚像是踢中了棉花包,一声闷哼后,黑影裹着棉袄滚到了炕下。 第二天搜院子时,灶房柴堆里发现了半截军用火柴。 这种印着“兴亚院”字样的火柴,只有日军特务才会用。 刘锡坤心里咯噔一下,想起地主夫妇这几天总说去邻村赶集,一去就是整宿。 本来以为是普通借宿,没想到夜里出了这档子事。 村里的老支书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明明灭灭。 他说地主家儿媳是上个月刚娶的,娘家在县城开杂货铺,隔三差五就有人来送“货”。 刘锡坤顺着这话一查,那些送货的驴车每次都在村东头老槐树下停片刻,车把式总要用脚碾几下地面。 后来在那棵老槐树下,挖出了三个装着密信的瓦罐。 信上的字要用醋泡过才能显形,写的全是八路军的动向。 原来地主儿子早就投靠了伪军,儿媳是专门安插的眼线,那晚摸黑进房,是想偷他贴身带着的部队布防图。 那会儿敌后的情报战就是这么回事。 日军特务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混在赶集人群里,村妇纳鞋底的针脚都可能藏着密码。 刘锡坤带着人端了县城的特务点后,把缴获的密写药水倒进了滹沱河。 河水带着那些蓝色的液体往下游流,像一条不会说话的情报。 现在冀中军区纪念馆里,还摆着个掉了瓷的粗瓷碗,碗底有圈不起眼的裂痕。 那是当年刘锡坤用来检测密写药水的家伙,用草木灰和水一调,就能显出字迹。 讲解员说,那碗沿的缺口,是他发现特务时攥太紧捏出来的。 老槐树还站在村口,树干上当年拴驴的铁环早锈成了疙瘩。 去年村里修族谱,有人翻出记载,说那天夜里地主儿媳滚到炕下时,怀里掉出的不是刀,是块绣着鸳鸯的红肚兜。 刘锡坤常跟人说,要不是那只冰凉的手摸上来,他可能永远想不到,最柔软的布料里,能藏着最锋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