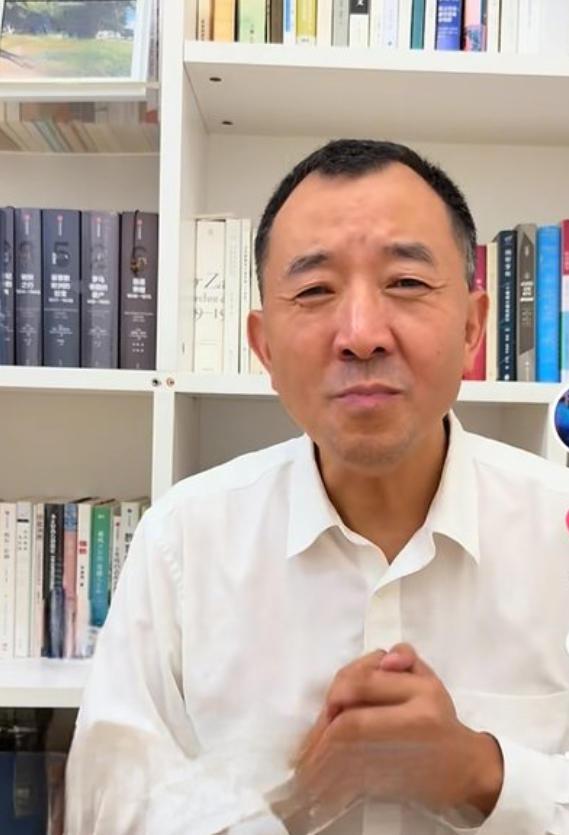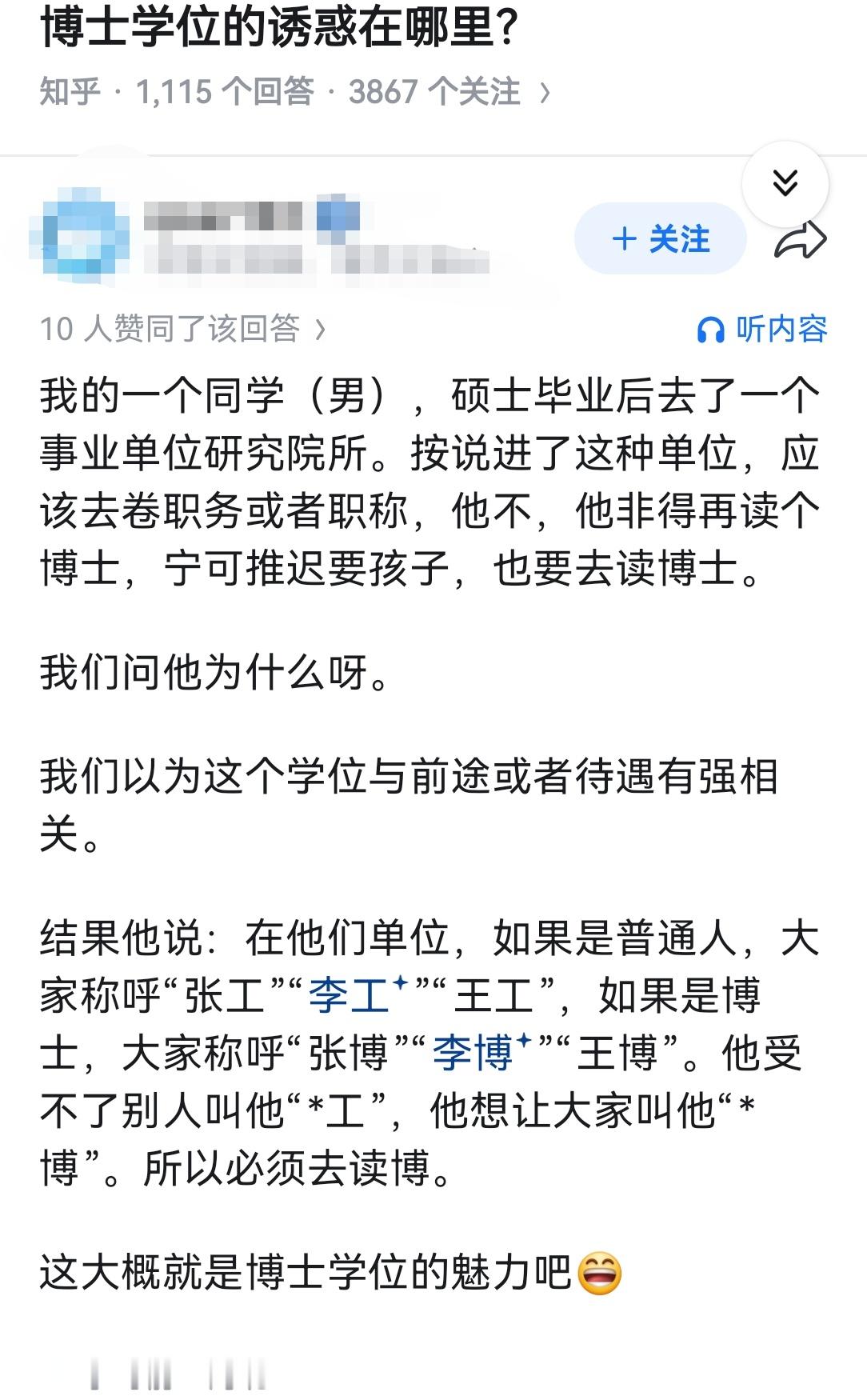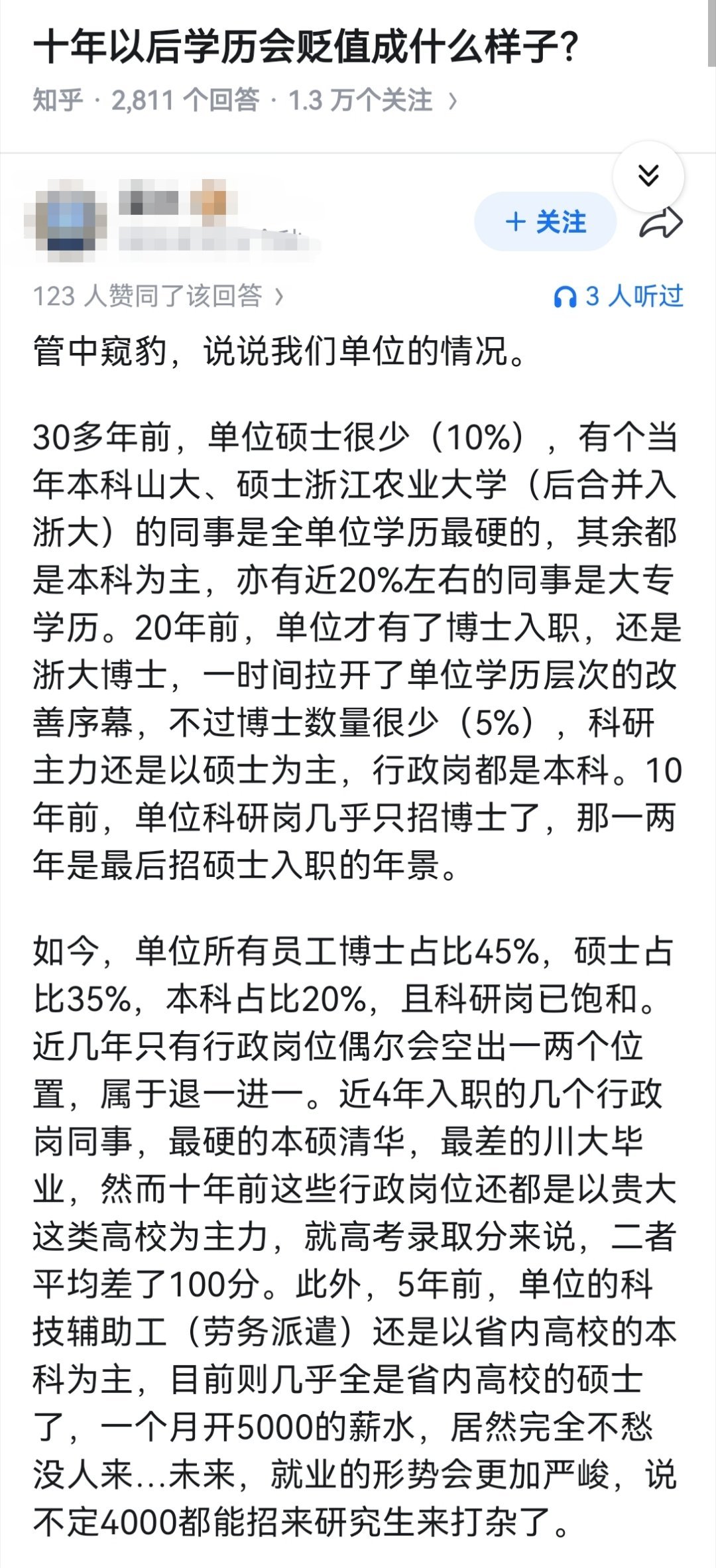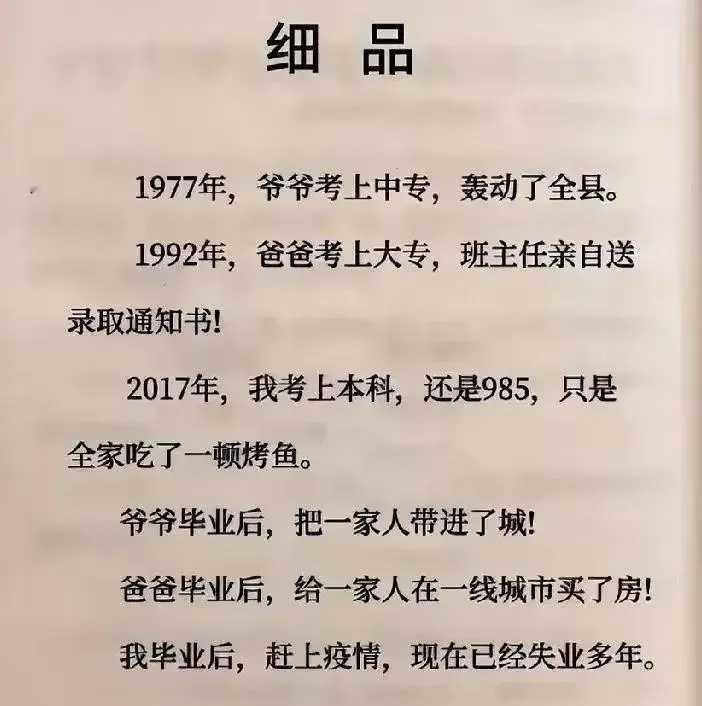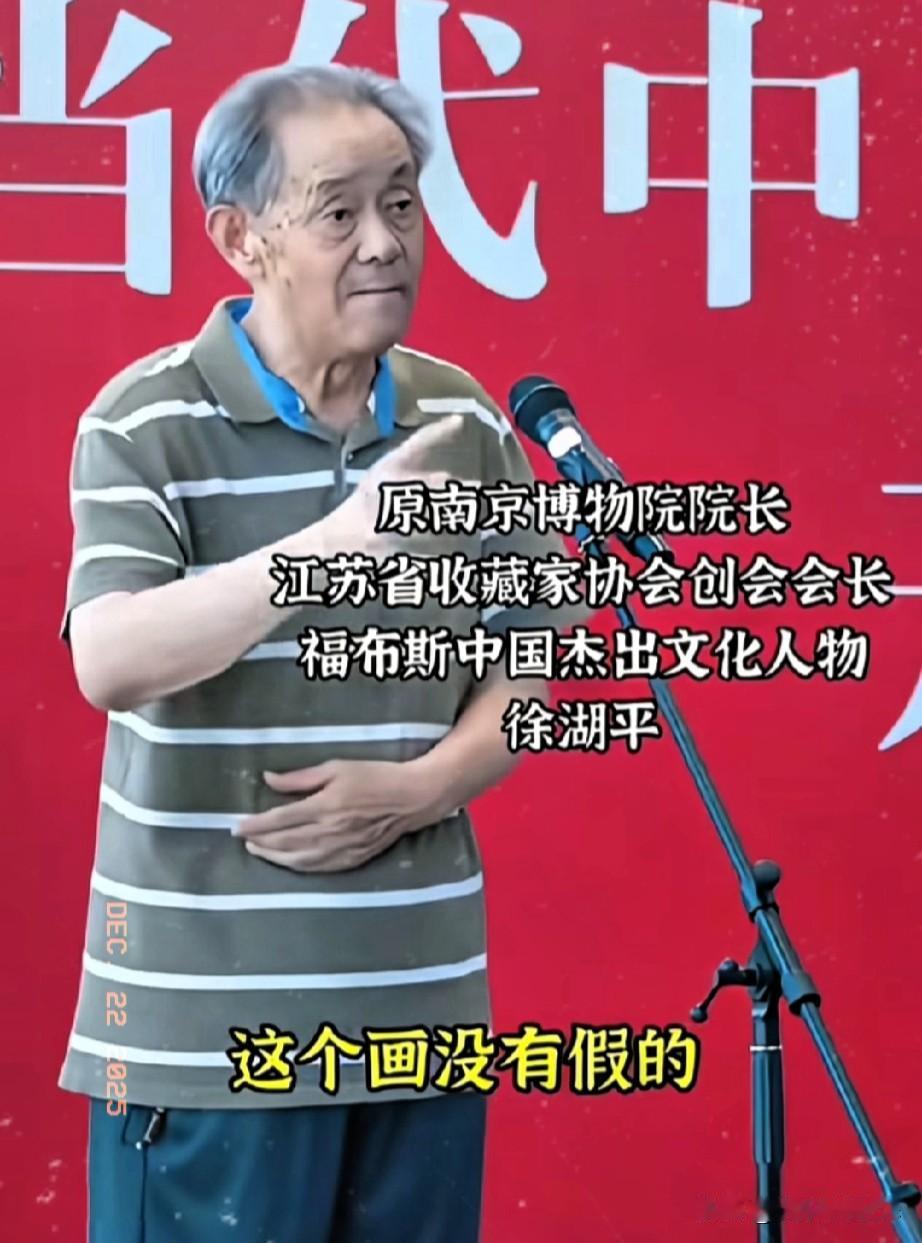手握清华硕士的学历文凭,顶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金字招牌,放在哪里都是官场上妥妥的潜力股。可就在2015年刚拿了荣誉,转过年来的2016年,陈行甲直接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裸辞。 这时候的他,手里分明握着一手世俗眼里的“王炸”。可他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不仅扔了“乌纱帽”,还抛出了一段堪称“凡尔赛”的宣言,把那些贪官遮遮掩掩的遮羞布扯得粉碎。 他说,那些贪官费尽心机捞钱,无非就两个指望:一个是给儿子铺路,一个是买几套大房子。接着话锋一转,语气里全是傲气:“我不贪,是因为我真的啥也不缺。” 这话乍一听挺“狂”,可细琢磨,这里面藏着一种高级的通透。他给大伙算了一笔账:儿子争气得很,在那著名的燕园北大读书,是妥妥的学霸,压根不需要老子拿脏钱去“养”;至于房子,国家对于高学历干部有人才房保障,住了大半辈子公家房,也没见谁流落街头。 既然最烧钱的两个“刚需”都解决了,剩下的身外之物,多拿一分都烫手。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一个人内心的底气不需要靠存折上的零来支撑时,诱惑对他来说,就成了笑话。这恰好印证了他那发人深省的家训逻辑:“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此问振聋发聩,引人思索财富与子孙成长之关联。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 有了这份不求人的底气,陈行甲到了湖北巴东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简直就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当时的巴东,那是一滩浑水。50万人的县城,贫困人口占了三成多,可就是这么个穷窝窝,竟然有人趴在财政上吸血。一项预算仅300万的小型工程,尚在筹备阶段,一铲未动,120多万资金便被挪用。分管副书记与镇委书记更是胆大包天,直接将百万“打点费”纳入囊中,令人咋舌。新修之路未几便塌陷,此等情形令人痛心。百姓对此自是怨声载道,背后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足见其对工程质量之不满。 面对这种局面,换个圆滑点的官,可能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混过去了,甚至还得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但陈行甲偏不,他选择了一头撞上去。 有人提着20万现金和金条上门试探,连门都没进去;有人送来价值十几万的江诗丹顿名表,以为能买个“方便”,结果被他当场严词顶了回去。他在巴东那几年,那是真刀真枪地干,硬是把85名官员送进了号子,这名单里头,不仅有下面干事的9个局长,甚至还有当时和他搭班子的县长刘冰,以及另外几名县级领导。与此同时,那些妄图围猎官员、扰乱政商秩序的47名老板亦未能逃脱法网,被一举查办,彰显了打击违法违纪、维护清朗环境的坚定决心。 这么干,能不招恨吗?威胁的短信直接发到了手机上,明明白白报出了他家的家庭住址,甚至连老婆孩子都收到了暗示,让他“做人留一线”。那些日子,县委大院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敢跟他这个“独夫”走得太近。 他在官场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种“不通世故”的性格基因,其实早早就种下了。1971年出生的陈行甲,是在苦日子里泡大的。母亲目不识丁,她的识字启蒙源于教儿子拆字。她指着“苦”字,缓缓道:“草字头下一个十字架,再下面是个口。人这一辈子,脸便是承载苦难之所。” 当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却还是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盐,借给了那个根本还不起的邻居。小陈行甲不懂,母亲只说了一句:“他们要是能借到,就不来我们家了。” 就是这份在苦难里长出来的干净和善良,成了陈行甲骨头里最硬的钙质。他于巴东掀起的这场风暴,虽令他深感茕茕孑立之苦,却也换来了最为真切的回应。这份孤独与回响交织,恰如生命中独特的旋律。离任那天,没有官员迎来送别,倒是县委大院外头,老百姓自发排成长队,举着横幅送别他们的“甲哥”。 脱了官袍的陈行甲,转身也没有闲着,而是一头扎进了公益圈。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他不贪财真不是装出来的。 他在深圳搞了个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专门盯着儿童白血病救助,硬是推动着要把几千块一盒的进口特效药纳进医保。为了这个事,他像当年抓贪官一样四处奔走,每年帮这些病患家庭省下的钱高达百亿。 甚至在发放救灾物资的时候,遇到有办事员习惯性地伸手要回扣,这都已经不是官场了,他那个暴脾气还是压不住,像当年一样分毫不让,一点情面不留。别人嘲笑他“当官没捞着钱,现在还得靠写书卖惨”,他转手就把书稿收益全捐了出去。连中兴的侯为贵都被他的这股子纯粹打动,主动联系支持他的公益项目。 不贪,是因为真的不缺;不缺,所以无畏。这世上,最大的财富不是留给子孙多少房产,而是留给他们一个清清白白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