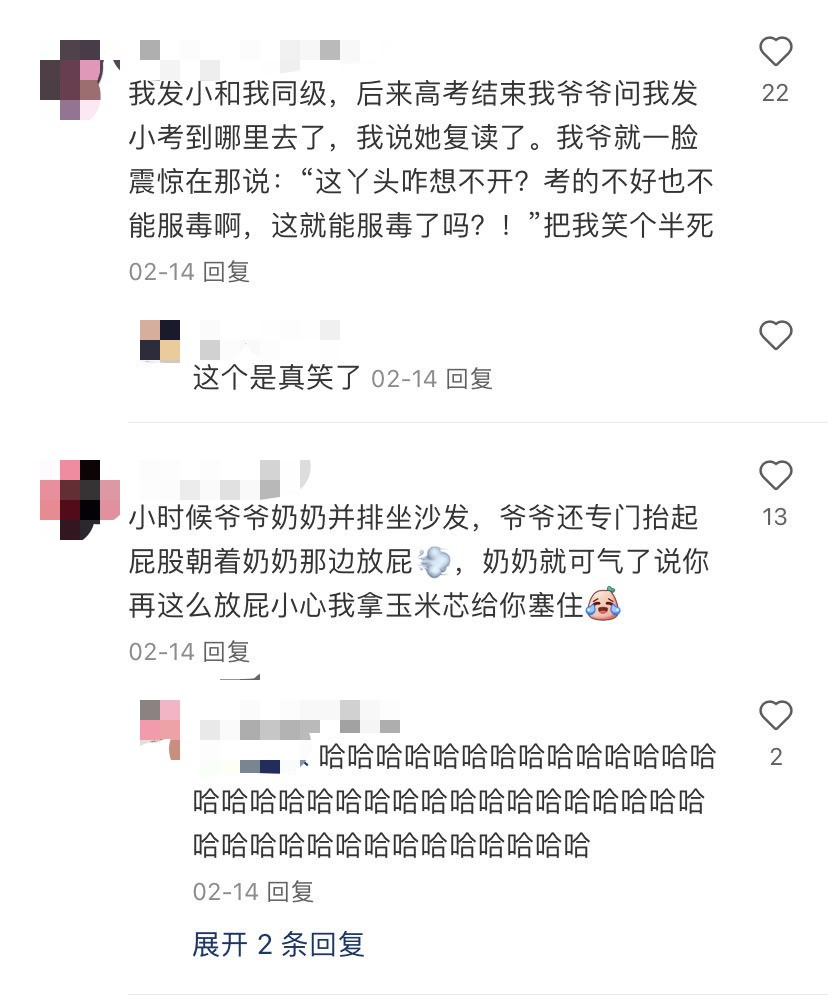1970年,年轻时的莫言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姑娘不屑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莫言没有放弃,请媒人去提亲,姑娘让媒人给莫言带了一句话,直接影响了他一生! 那年的莫言还不叫莫言,叫管谟业,十九岁,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出了名的穷小子。家里成分不好,爷爷是地主,父亲在村里抬不起头,他自己只读了五年小学,就回家跟着大人刨地、割麦、喂牛。脊背被太阳晒得脱了皮,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子,可他怀里总揣着一本皱巴巴的《三国演义》,干完活就蹲在田埂上看,看得入了迷,连饭都忘了吃。 邻村的姑娘叫春燕,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俊丫头,两条麻花辫甩在身后,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管谟业见她第一眼就挪不开眼,收工的时候总绕远路,就为了看她一眼,看她在河边洗衣服,看她挎着篮子割猪草。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春燕,可喜欢这东西藏不住。那天收工,他攥着攒了半个月的津贴买的一块水果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堵住了春燕。糖纸被攥得发皱,他的手心全是汗,磕磕绊绊说,春燕,我想跟你处对象。 春燕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他,看他补丁摞补丁的褂子,看他满是泥点的裤腿,突然笑出了声,笑完就丢下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扭头跑了。那笑声像针,扎得管谟业半天抬不起头。周围干活的乡亲看过来,有人低低地笑,有人叹了口气。他站在老槐树下,攥着那块没送出去的糖,糖都被手心的汗泡化了,黏糊糊的,像他当时的心情。 他不死心。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燕的脸,想起那句扎人的话,心里又酸又涩。第二天一早,他揣着家里仅有的两斤白面,去求村里最会说媒的王大娘。王大娘叹了口气,说谟业啊,你这孩子,明知道不行还犟。话是这么说,还是提着白面去了春燕家。 傍晚的时候,王大娘回来了,脸上带着为难的神色。她说,春燕那丫头,嘴硬得很,说你要是能写出一本书,让全村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让外村的人也知道高密有个管谟业,她就考虑跟你处对象。 这话传到管谟业耳朵里,村里人都炸开了锅。有人说春燕这是故意刁难,写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人说管谟业这下该死心了,一个泥腿子,还想写书。管谟业没说话,只是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他想起小时候,奶奶坐在炕头上给他讲狐仙的故事,讲村里的奇人异事,那些故事像种子,早就埋在了他的心里。他想起自己揣在怀里的《三国演义》,想起书里那些鲜活的人物,突然觉得,写书好像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从那天起,管谟业像变了个人。白天在地里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家,就点起煤油灯,趴在炕桌上写。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老长。 他买不起稿纸,就用捡来的烟盒纸,一张张拆开,用铅笔在上面写。写村里的人,写地里的事,写奶奶讲的狐仙,写自己的欢喜和委屈。 烟盒纸写满了一摞又一摞,他的手指被铅笔磨出了厚厚的茧子,鼻孔被煤油灯熏得发黑。母亲看他熬夜,心疼得直掉泪,说儿啊,别熬坏了身子,咱不挣那个虚名。他只是摇摇头,继续写。 村里人看他这样,都觉得他魔怔了。有人说他是被春燕刺激傻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早晚得饿肚子。他不在乎,那些嘲讽的话,那些不解的眼神,都成了他写字的动力。他想起春燕的那句话,想起自己在老槐树下的窘迫,就觉得手里的铅笔重了几分。他知道,自己写的不是书,是自己的一口气,是一个穷小子不甘于命运的较劲。 后来,管谟业去参了军。临走的时候,他把写满字的烟盒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塞进了包袱里。部队里的生活苦,训练累,可他还是挤时间写。在营房的灯下写,在训练的间隙写,把自己的思念,把自己的经历,都融进了文字里。他的稿子一篇篇寄出去,又一篇篇被退回来,退稿信攒了厚厚一沓。他没放弃,退回来的稿子,他就改了又改,改了再寄。 日子一天天过,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再后来,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莫言。他的小说一篇篇发表,《红高粱》《檀香刑》《蛙》,一部部作品横空出世,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甚至传遍了世界。他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高密东北乡那个穷小子管谟业,真的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成名后的莫言,回了一趟老家。他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想起十九岁那年的自己,想起那块没送出去的水果糖,想起春燕的那句话。 他打听过春燕的消息,听说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木匠,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安稳。有人问他,恨不恨春燕当年的那句话。莫言笑了,说不恨,要是没有那句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刨地的农民,不会拿起笔,不会写出那些故事。 一句嘲讽的话,成了一个人一生的转折点。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不是困难,是自己的认命。而那些看似伤人的话,恰恰能戳醒沉睡的斗志。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做,敢坚持,癞蛤蟆也能跳出自己的一片天。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