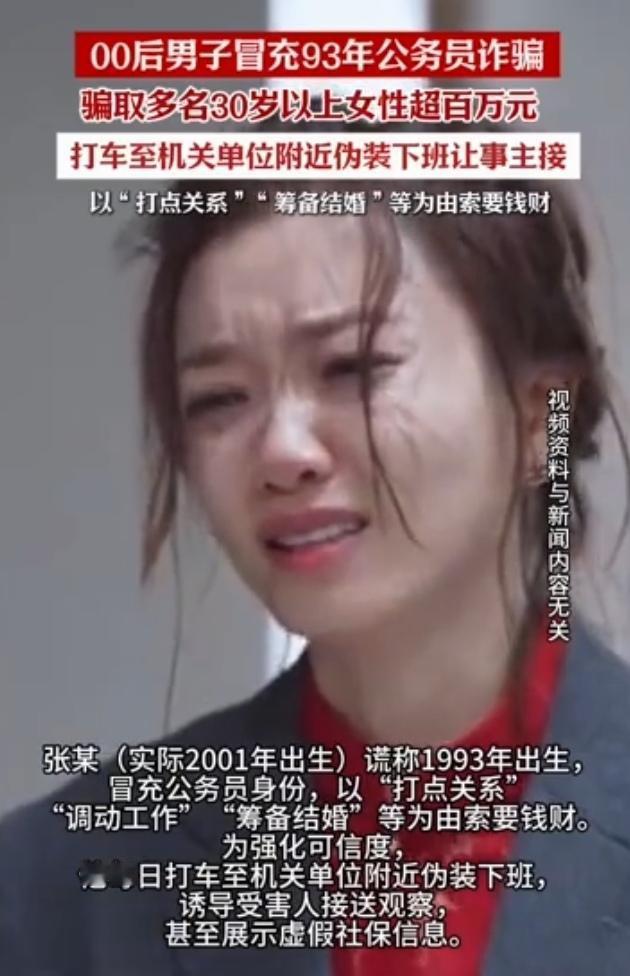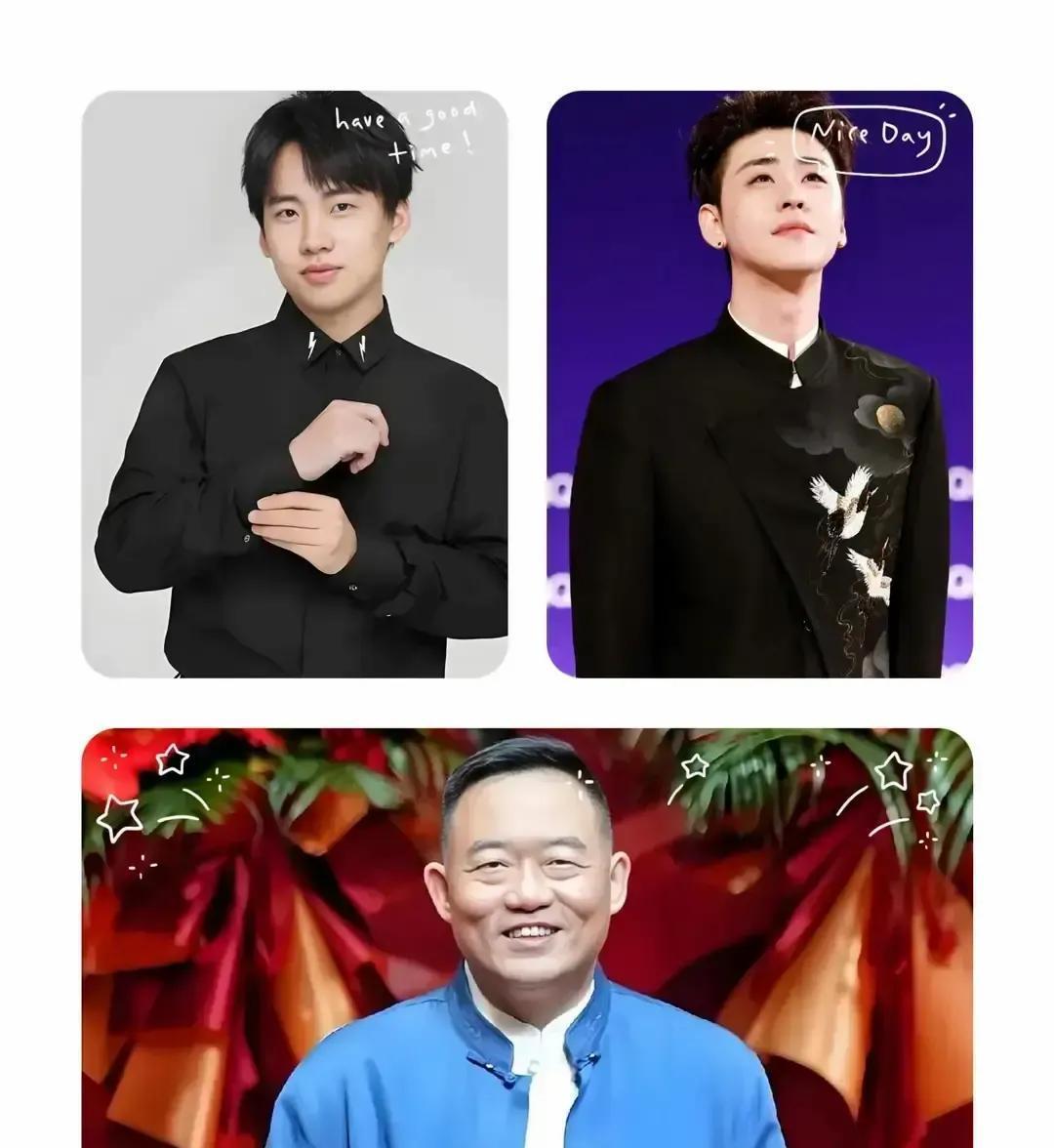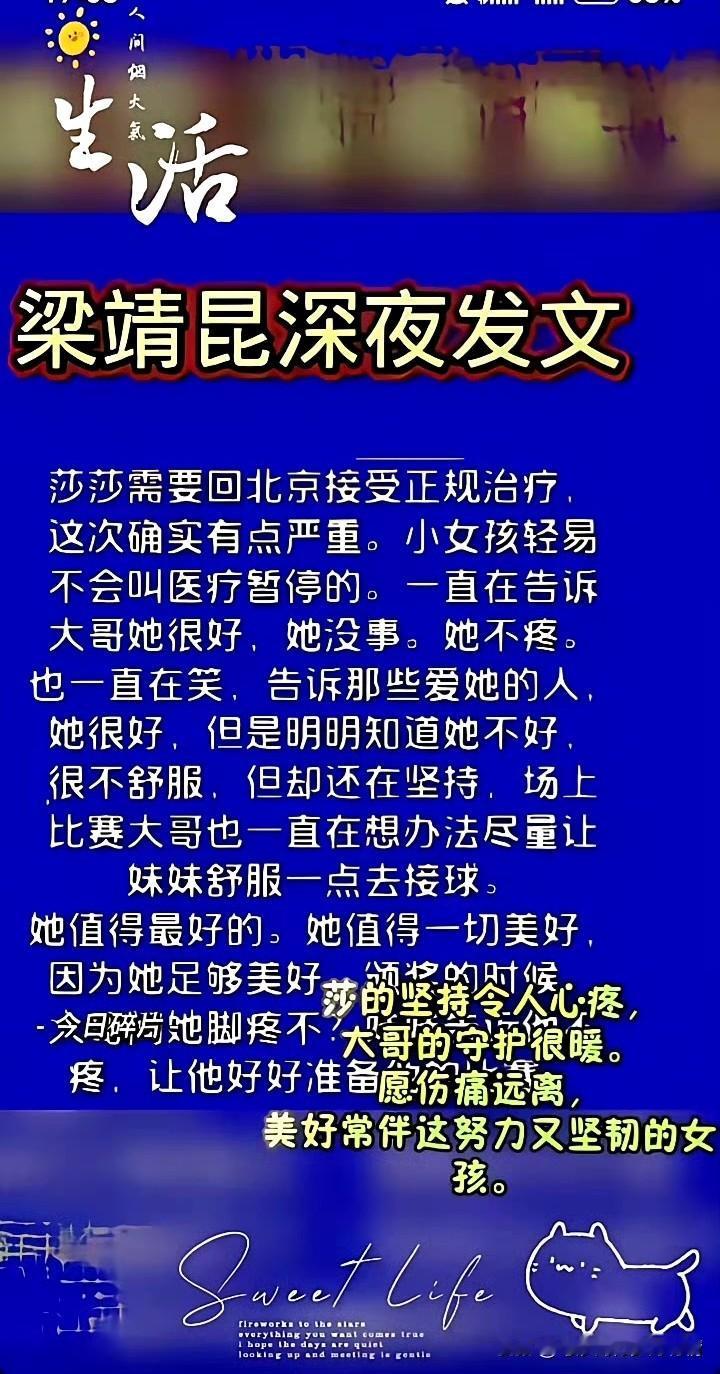2009年11月,钱学森告别仪式上,孙儿钱磊手捧祖父的骨灰盒,走在队伍前面,满脸沉痛,当时前来吊唁的民众络绎不绝,哀悼与送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 那天的北京,天空是一种淡淡的灰白色。殡仪馆外头,队伍排得老长,一眼望不到头。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一步步挪着;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手里攥着自制的白色纸花;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安静地站在寒风里。没人喧哗,只有低低的啜泣声,和鞋子摩擦地面的沙沙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沉重的肃穆,压得人心里发紧。钱磊捧着那个沉甸甸的盒子,头垂得很低,步子迈得又稳又慢。那个盒子里装的,何止是一个人的骨灰,那是一个时代的重量,一段峥嵘岁月的全部结晶。 说起钱学森,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大概是“两弹一星”。课本上写得明明白白,功勋册里记得清清楚楚。可有时候,这些金光闪闪的大词,反倒把一个人捂得严严实实,让我们忘了他也曾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爱听古典音乐,尤其喜欢巴赫。在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教书的时候,周末常泡在音乐厅里。回国时,行李精简再精简,一套音响设备却死活要带上。后来在西北荒漠,耳边是呼啸的风沙,心里或许还能响起那些严谨而恢弘的旋律。科学和艺术,在他身上从来不是割裂的,那都是他对秩序与美感的极致追求。 他也有过憋屈到极点的日子。在美国被软禁那五年,行动受限,电话被监听,书房里说不定就藏着窃听器。从一个备受尊敬的顶尖科学家,瞬间变成被怀疑、被监视的“危险分子”,这种落差,普通人想想都要崩溃。可他干了什么?他把自己关进书房,埋头写了一本《工程控制论》。硬生生在精神的铜墙铁壁上,凿出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这口气,这股劲儿,不是仅仅用“爱国主义”就能完全解释的。这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倔强:你们可以困住我的身体,但囚禁不了我指向宇宙星空的思想。 钱学森回国,几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决心挺直脊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触碰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高度。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现成的资料,就一遍遍推导、验算。他带着一群同样满怀热血的年轻人,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愣是把事情干成了。那时候的人,心里似乎都憋着一团火,一团叫做“争气”的火。这团火,烧出了罗布泊上震惊世界的巨响,也烧出了中国人在世界科技舞台上不容忽视的尊严。 可是,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如此隆重地缅怀钱学森,究竟是在缅怀什么?是缅怀那段万众一心、勒紧裤腰带干大事的激情岁月?还是缅怀他个人天才的头脑和传奇的经历?或许都是。但更深一层,我们是不是在缅怀一种如今略显稀缺的东西,那种纯粹到极致的信仰,那种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毫无保留融合在一起的赤子情怀?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里。选择多了,诱惑多了,声音也嘈杂了。我们推崇科学家,但我们的孩子,最想成为的可能是网红、是明星、是金融巨子。我们赞美奉献精神,但衡量成功的尺度,往往又简单直接地指向财富与地位。这不是谁的错,这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但在这个背景下,回望钱学森,就像回望一座远方的灯塔。光芒或许有些遥远,但它确凿地标示着一个方向:人这一辈子,除了“得到”,还可以“创造”;除了“拥有”,还可以“奉献”。 钱老晚年,思考的问题早已超越具体的火箭导弹。他关心教育,提出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思考系统科学,思维驰骋在整个宇宙文明的尺度。他的心,从未离开过这个民族最深远的未来。他捧出的,何止是几件大国重器,更是一整套关于如何让一个民族真正强大起来的思考。 送别的那天,人潮缓缓移动,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一个时代告别。钱磊手中的骨灰盒,最终会安葬在苍松翠柏之间。但有些东西,是不会被埋葬的。它散落在每一枚划破天际的火箭尾焰里,镌刻在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眼眸中。我们记住钱学森,不仅仅是记住一段历史、一位伟人,更是要记住一种精神的可能性,当一个人把生命的热忱,全部注入到比自身宏大得多的事业中去时,所能迸发出的惊人光芒。 那个为中国航天点燃第一把火的人,走了。但他点亮的星辰,正在由后来者,一片片接续成灿烂的银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