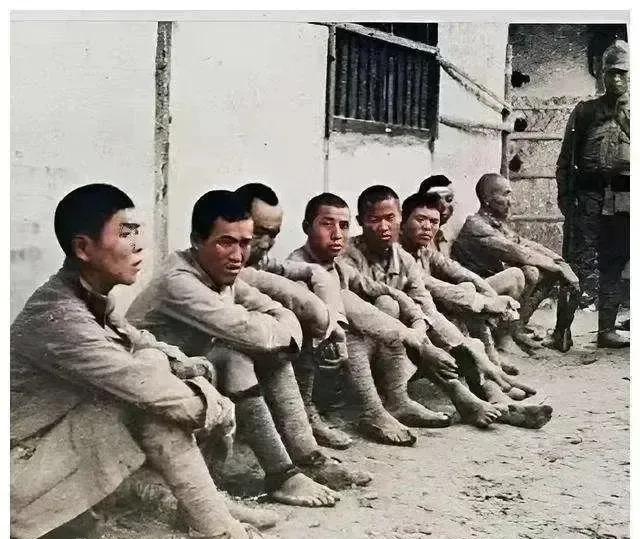1943年,一个女乞丐正要出城,日军怀疑她是地下党,竟让她当众脱下衣服,这时,女乞丐从包裹中取出一东西,竟吓得日本鬼子连连后退。 那女乞丐叫朱文起,山东定陶的庄稼人,头发打结如枯草,怀里揣着磨破的粗布包——里面除了三个孩子的破棉袄,还有丈夫游兰馨留下的半截弹壳。三年前宪兵在村口打死游兰馨时,她当场昏倒,醒来后奶着最小的娃,大的两个拽着她的裤腿要爹,她抹把泪,带着孩子走上了讨饭路。 亲戚劝她改嫁,她指着村口那棵被日军战马啃秃的老槐树:“仇没报,家没建,改嫁了,兰馨在土里都闭不上眼。” 没人知道这个天天端着破碗挨家要饭的妇人,是冀鲁豫第六支队最“合格”的地下交通员。从1941年起,她的破袄里藏过暗语,孩子的麻袋里裹过路线图,连讨饭用的豁口碗,都曾被她用来给伤员盛过米糠——那是她把两名伤员藏在草车里,用牲畜粪盖住车身,从定陶送到菏泽时用的“药碗”。 1943年那次任务,她要送的是县委刚拟好的电文,目标郓城南的接头点。日军最近在城北出口加了岗,宪兵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咔嗒响,每个过路人都得张开胳膊,让刺刀挑开衣襟。 朱文起把电文缝在贴身的衣襟线下,又把那截弹壳——游兰馨战前塞给她“留个念想”的东西——裹进破布里,塞进布包最底层。她想过,要是被搜出来,这弹壳就是她最后的“武器”。 “这个女的不对。”一个宪兵盯着她怀里的孩子,那孩子被麻袋裹着,只露出双黑亮的眼睛。另一个宪兵直接吼:“脱衣服!” 她不动,手悄悄摸向布包。宪兵上来扯她的衣领,针脚缝的地方被拽得发紧。就在这时,她猛地掏出那截缠着破布的弹壳,举到脸前,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敢碰?这就炸了你们!” 日军愣住了。生锈的弹壳在夕阳下泛着冷光,她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怀里的孩子突然哭起来,哭声刺破了岗哨的死寂。 他们未必真信这弹壳能爆炸,但他们怕——怕这疯妇真敢抱着孩子同归于尽,怕围上来的百姓里藏着更多“疯子”,更怕岗哨的骚动引来暗处的冷枪。 “滚!”宪兵挥挥手,朱文起趁机抱着孩子瘫坐在地,拍着大腿嚎:“我要去找人埋我男人的骨头啊……” 她没回头,拖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四十里。傍晚到接头点时,赵干事看着她磨出血的脚后跟,拆开衣襟里的电文,铅笔在地图上重重画了个圈——日军在郓城的调兵换岗时间,被清清楚楚记在上面。 这份情报,让六支队的清剿计划提前了三天。 后来她又送过三次情报,一次躲在拉粪的牛车底,一次装成发丧的家属,每次都带着孩子,用“母子讨饭”的模样,从日军眼皮底下钻过去。 1986年,原六支队的赵树全整理口述资料,才写下这个叫朱文起的“乞丐交通员”。抗战胜利后,县里送来的奖状被她压在箱底,继续在定陶的老院里纳鞋底。 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总听母亲说:“你爹留下的那截弹壳,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告诉咱,活着,就得给这世道留点响儿。” 她确实留了——不是惊天动地的响,是一个普通妇人,在最暗的夜里,举着微光,给一个民族的不屈,当了回“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