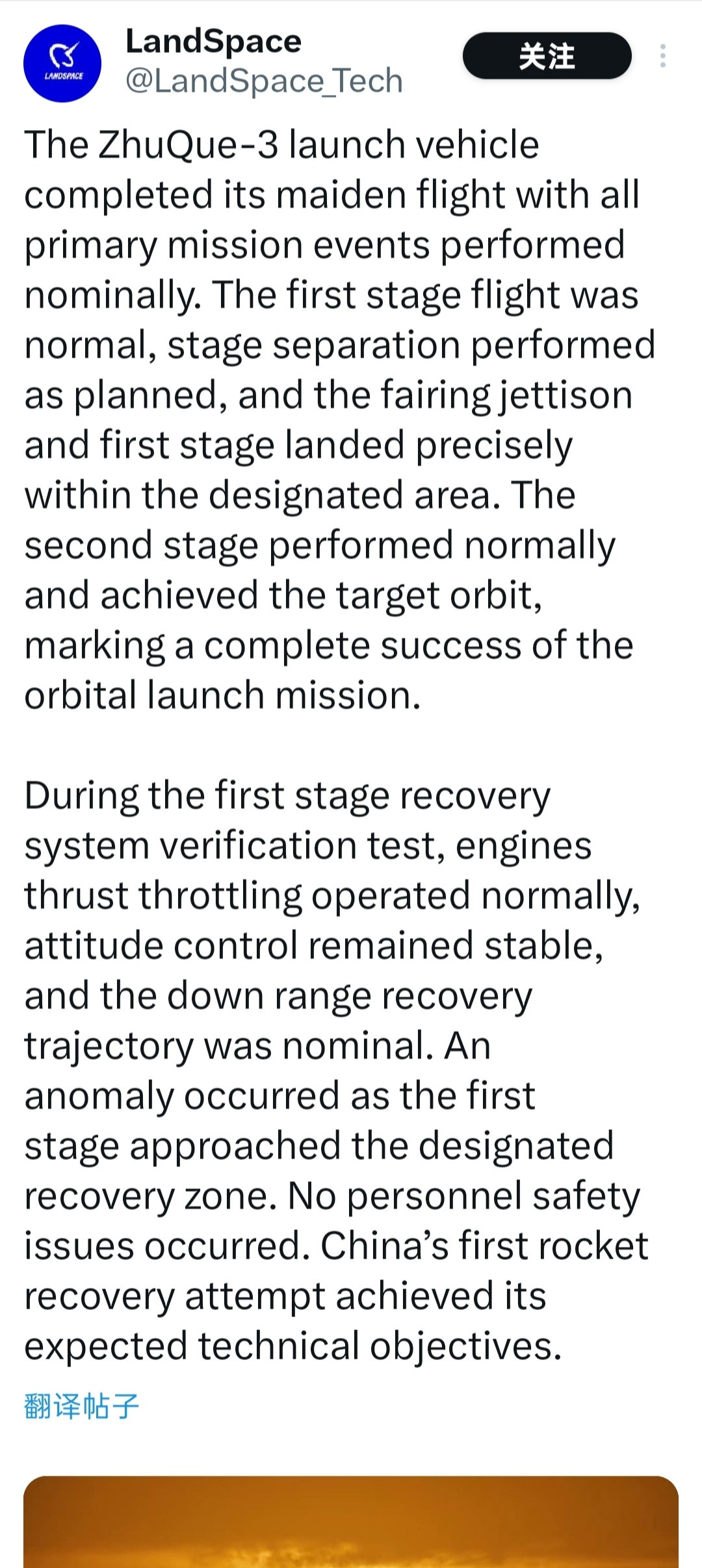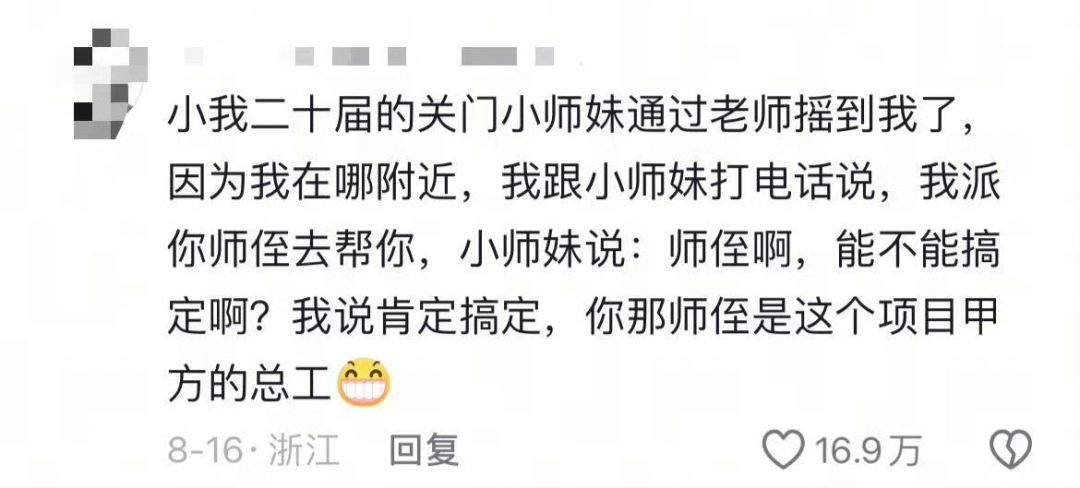他是中国两弹元勋,“中国光学之父”,研制出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为“两弹一星”提供核心光学装备,照亮中国科技崛起之路的民族脊梁——王大珩! 1915年,王大珩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江苏苏州,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年后赴英攻读应用光学,1948年揣着报国心回到祖国。 归国轮船驶入黄浦江时,他攥着英国导师临别赠言的纸条——“光学是工业的眼睛,中国需要自己的眼睛”;码头上迎接他的,只有一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磨镜片工具和三封邀请他去研究所的电报。 那时候的中国,光学事业几乎是空白,连像样的光学仪器都造不出来,只有几家能摆弄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实验室窗台上,生锈的坩埚里还残留着进口玻璃渣,像极了当时科技界的窘迫处境。 1951年冬,他在长春一栋废弃兵营里支起黑板,粉笔灰簌簌落在军大衣肩头——黑板上画的不是光学公式,而是“材料-仪器-人才”的三角草图,这是他为中国光学搭的第一根架子。 有人说“光学太超前,不如先搞无线电”,他却带着学生在零下二十度的车间里烧炉子;第一炉玻璃出炉时呈墨绿色,像块半透明的石头,他拿砂纸磨了三天,透过玻璃看报纸的字迹竟比进口镜片还清晰。 这炉玻璃没来得及庆祝,朝鲜战场的加急电报就到了——前线急需测距仪,他带着团队把实验室改成临时车间,用木架当机床,三个月造出200台军用光学仪器;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搞砸”,他只指着墙上“向科学进军”的标语:“国家需要的时候,哪有时间想怕不怕?”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图纸,长春光机所的保险柜里,只剩下他带着团队手绘的137张光学元件图纸。 最关键的激光晶体生长技术被卡了脖子,他让人从中药铺买来坩埚,在实验室支起土法加热装置;某天深夜,助手发现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块刚长出晶核的石英,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座弯腰拉车的雕塑。 有人说“没有进口设备根本做不出来”,他却在笔记本上写:“规律藏在失败里”;八个月后,中国第一台激光器诞生,波长精度比苏联原版还高出0.3纳米——这不是偶然,他早带着学生把《物理光学》啃得滚瓜烂熟,连书边角都写满批注。 1986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应引进外国高技术”的讨论,当晚就约了陈芳允去办公室。 两位老人在台灯下算了笔账:如果只靠引进,十年后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将落后两代;凌晨三点,他在建议书上写下“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高技术研究计划”,钢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这份建议书递上去时,有人担心“国家没钱搞这么大项目”,他却坚持附上一张表格——列出了半导体、航天等七个必须抢占的制高点;邓小平三天后批示“宜速作决断”,“863”计划就此启动,后来有人说这是“用战略眼光抢跑”,他却摆手:“不是抢跑,是不能掉队。” 他很少提自己的研究,却总把学生的名字写在成果报告最前面。 某次评审会上,有人称他“光学之父”,他当场纠正:“我只是个铺路的,前面有严济慈先生他们,后面有年轻人,这路得一代代接着铺。” 晚年整理资料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张泛黄的船票——1948年从利物浦回上海的船票,背面用铅笔写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后来刻在了长春光机所的纪念碑上,碑座下埋着他生前最爱的那块石英晶体。 他走后,有人统计过,经他培养的院士有26位,光学领域的国家科技奖获得者里,三分之一是他的徒子徒孙。 现在长春光机所的实验室里,还留着他当年用过的那台手摇计算机,键盘都磨出了包浆;年轻研究员说,遇到难题时摸一摸这台机器,就想起他说的“把冷板凳坐热”——不是熬时间,是把心沉下去,在寂寞里种出花来。 他的贡献从来不是某一项技术,而是搭起了中国光学的“四梁八柱”:从光学玻璃到仪器制造,从人才培养到战略规划,每个环节都透着“系统思维”。 就像他常说的:“科研不是孤岛,要长在国家的土壤里”;这种把个人事业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智慧,或许正是今天我们讲“科技自立自强”时,最该传承的密码。 如今,中国光学专利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激光测距精度达到0.1米级,从探月卫星的相机到航母的雷达,处处可见他当年播下的种子。 而他拒绝的“之父”称号,早已化作一种精神——当年轻人在实验室里为一个数据熬通宵时,当科研团队为突破“卡脖子”技术集体攻关时,那种“把国家需要扛在肩上”的担当,不正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他一生都在追逐光,最后自己成了光源——这光不耀眼,却足够照亮后来者的路;就像他当年亲手熔制的第一块光学玻璃,朴素,却让中国科技看见了更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