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仿佛一场精心陈列的哥特美学展览,却难掩内核的疲软与叙事的涣散。 陀螺以惯有的视觉野心构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阴郁舞台,从北极冰原的苍茫到实验室的猩红光影,每一帧都如古典油画般工整,然而这种过度雕琢的华丽反而成为情感的桎梏,让哲学诘问沦为场景切换间的浮光掠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直接被简化为癫狂与懦弱的符号,科学执念背后的伦理困境在夸张的肢体表演中逐渐消解。科学怪物虽然具备忧郁的诗意,却没有深挖认知觉醒的复杂性,最终停留在“悲惨巨人”的浅表层面。电影的矛盾在于类型定位的暧昧:既渴望延续《水形物语》的温柔寓言,又试图包裹B级片的生猛趣味,结果在两者间摇摆失据。结尾怪物与创造者在雪原对峙,那些关于存在与责任的终极叩问,最后被淹没在冗长的篇幅里。陀螺的怪物情结依旧真挚,但这回工匠的巧手也没能唤醒故事的灵魂。




![300一套,配置能行吗[滑稽笑]](http://image.uczzd.cn/6024423467350089387.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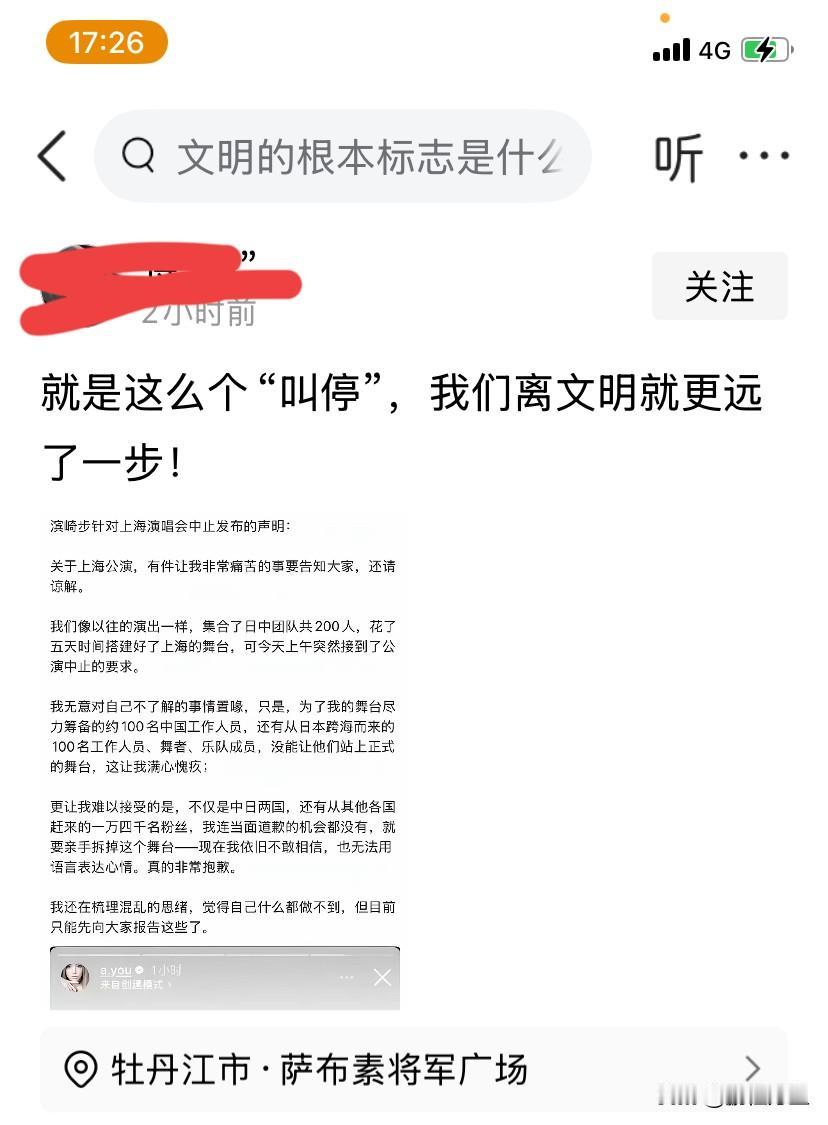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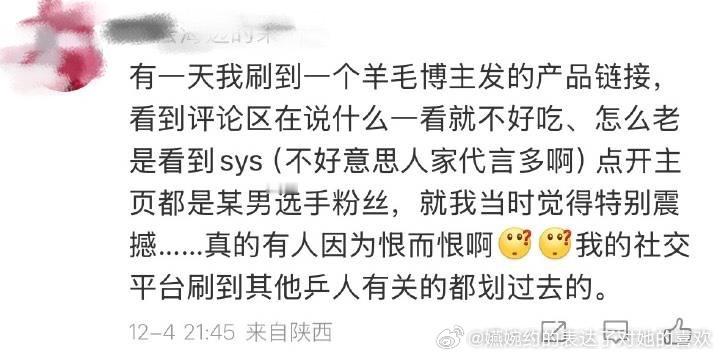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祝早日康复[作揖]](http://image.uczzd.cn/1553643330317612820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