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听不懂,怎么配来这高雅的地方!”可当辜鸿铭演讲后,只对那美国女人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无地自容。 1917年的北京深秋,东交民巷的西餐厅里,两个年轻学生瞅着邻桌那个脑后拖着长辫、身穿旧式黄马褂的老头,怎么看怎么觉着别扭。 学生们故意扯着嗓门拽英文,嘲讽他是连刀叉都不会用的“老古董”,言语间尽是把对方当成了早已发霉的历史遗物。 那老头也不恼,只顾着用最标准的礼仪切完最后一块牛排,甚至优雅地擦了擦嘴角,待他缓缓起身踱步到这俩毛头小子跟前时,出口竟是纯正得令人发指的牛津腔:“我在伦敦享用正宗西餐的时候,恐怕二位还没出生呢。” 这一开口,就像是锋利的解剖刀,瞬间划破了年轻人的虚妄优越感,把那两张脸憋得比盘子里的番茄酱还红。 这位就是辜鸿铭,他那一头显眼的长辫子与其说是对清廷的愚忠,不如说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诱饵。 在英国的火车车厢或伦敦地铁里,他常拿着报纸倒着看,引得旁边的英国青年嗤笑其不识字,谁知他眼皮都不抬,顺势就将手中那份倒置的《泰晤士报》朗读得行云流水,末了还要丢下一句诛心之论:这英文太简单,正着读实在乏味,倒过来才有点嚼头。 那些仗着肤色和国籍就敢在他面前不可一世的洋人,往往都在这上面栽过大跟头,无论是在华府的晚宴还是上海租界的交际场,总有那样一位自以为是的美国女士,看着眼前这位这身绸缎马褂的打扮,便用蹩脚的中文故意问汤好不好喝,讥笑他听不懂高雅的英语。 辜鸿铭应对这种场面的方式极其老辣,他先是祭出母亲——那个马来西亚橡胶园里的葡萄牙女人所教导的“沉默体面”,任由周遭窃笑发酵。 等到他站上演讲台,聚光灯打在他织金暗纹的长袍上,口中引用的却是歌德的《浮士德》,剖析的是康德的哲学,用法语调侃雨果的戏剧,甚至能随口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引经据典。 那一刻,平日里在沙龙高谈阔论的欧洲贵妇和外交官们,手里的雪茄和酒杯都变得尴尬无比,此时他再悠悠地回敬那位女士一句:“请问,您喜欢我的演讲吗?”那标准的伦敦音里带着泰晤士河畔的傲慢,直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就怪了,一个手握爱丁堡大学文学学位、攥着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文凭,号称一生拿下十三个博士头衔、精通九国语言的顶尖知识分子,怎么偏偏成了民国最扎眼的“守旧派”? 其实在他眼里,西方文明那点斤两早就被他那个精密的脑瓜称量过了,当那些英国绅士吹嘘电报机每分钟能传二十个单词时,他却抚摸着讲台,反问五千字的《道德经》流传了两千多年光芒未减,孰轻孰重?甚至连那位剑桥来的汉学家都不得不正襟危坐。 他指着那些断壁残垣的罗马浴场说,当年的大理石柱缝里如今只长野草,而曲阜孔庙的千年古柏依然葱郁,树荫下的中国学童还在朗朗读书,这便是文明韧性的明证。 为了守护这股子韧性,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当年父亲在马来西亚临行前的嘱托——“无论到哪别忘了是中国人”,似乎被他执行得有些过火。 他在北大教书时,学生们看着那条辫子哄堂大笑,他便抛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这好剪;你们心里的洋奴辫子是无形的,那才难剪。” 为了这根心里的“脊梁”,他甚至不惜用极端的诡辩来回击西方标准,当外国贵妇质疑一夫多妻制时,他直接抛出了那个著名的“茶壶论”——只见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见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 虽然这话如今听来颇为荒谬,但在那个特定的舆论场里,却把那些试图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西方人噎得哑口无言。 只是,这种既要在康德与黑格尔的逻辑里穿针引线,又要穿着黄马褂死守传统的姿态,终究让他在新旧交替的浪潮里显得格外孤独。 随着那个被他极力回护的旧时代彻底远去,1928年,这位被戏称为“末代狂儒”的老人,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里寂寥离世。 他带着那一身傲气和那条一直没剪的辫子走了,只留下一堆让人在茶余饭后依然嚼得津津有味的段子,和他那不惜以荒诞行为来对抗文化自卑的倔强背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辜鸿铭训斥毛姆、怒怼伊藤博文的话,香港暴徒应该好好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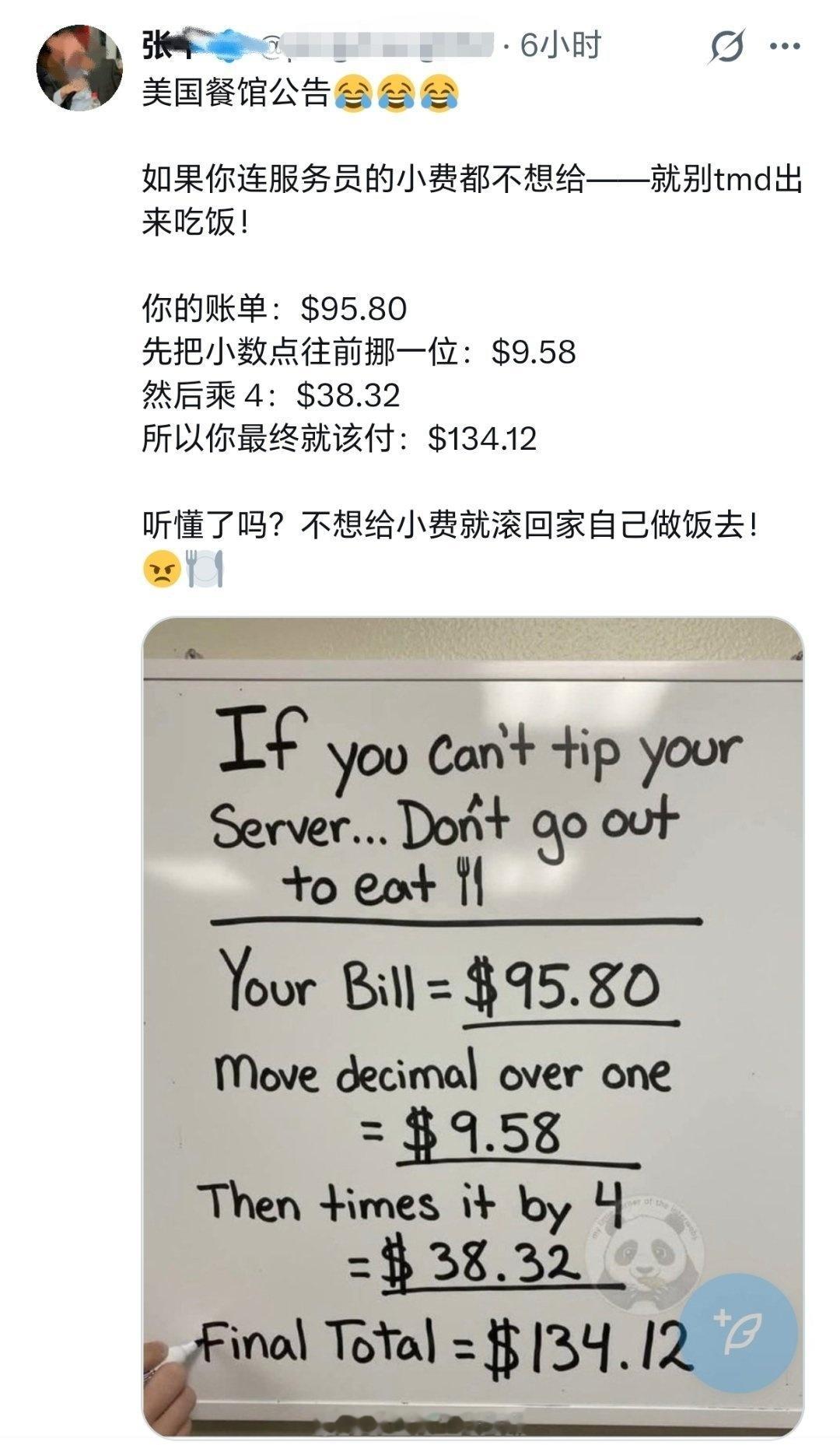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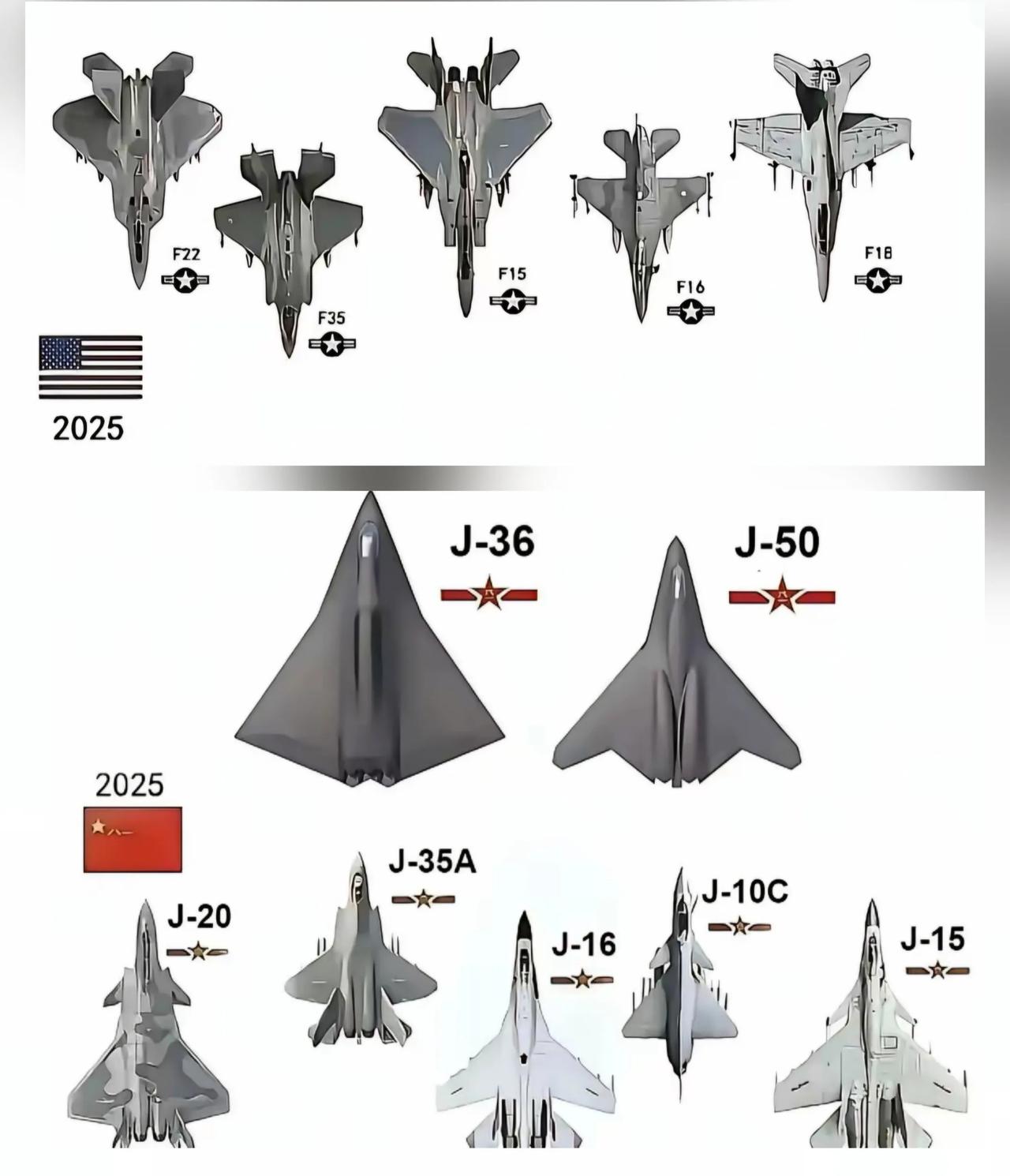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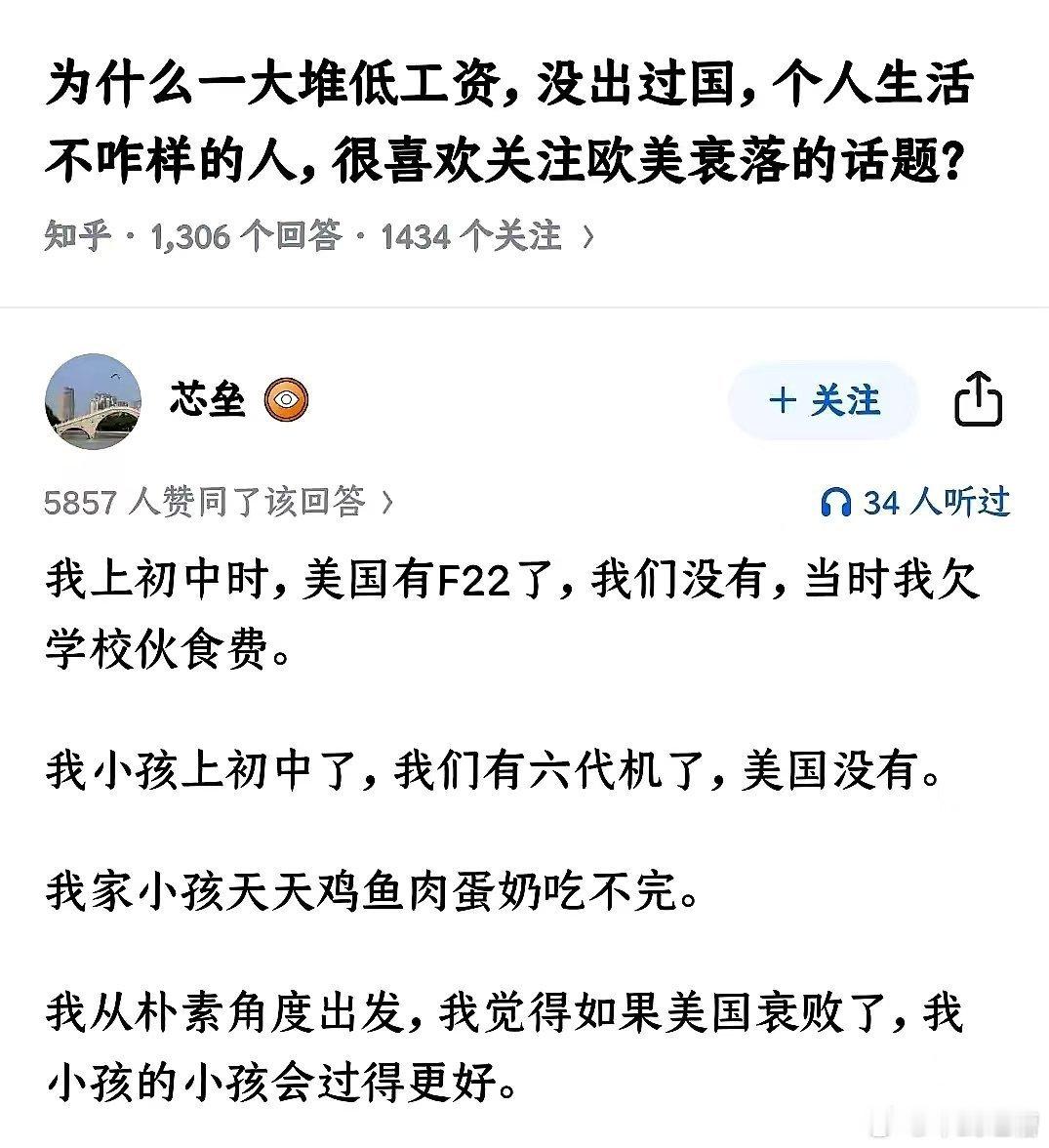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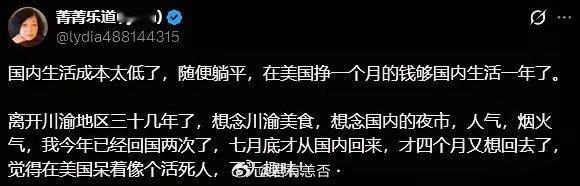



用户12xxx03
图片是张之洞吧?
三清鱼
辜老头真会玩,一会倒看德文报纸,一会又倒看英文报纸,不识字的居然是小编
用户10xxx28
北大教授辜鸿铭一天在教授休息室给火炉子添煤球,之后就坐下了。旁边一个洋教授说,你一个校工怎么能坐这里,你出去。辜鸿铭说,你是教授?你教什么课?洋人说,我教授英国哲学。于是辜鸿铭说了几句拉丁语,见他听不懂,就用纯正的英语说,一个不懂拉丁文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教授哲学,应该出去的是你。于是洋人羞愧的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