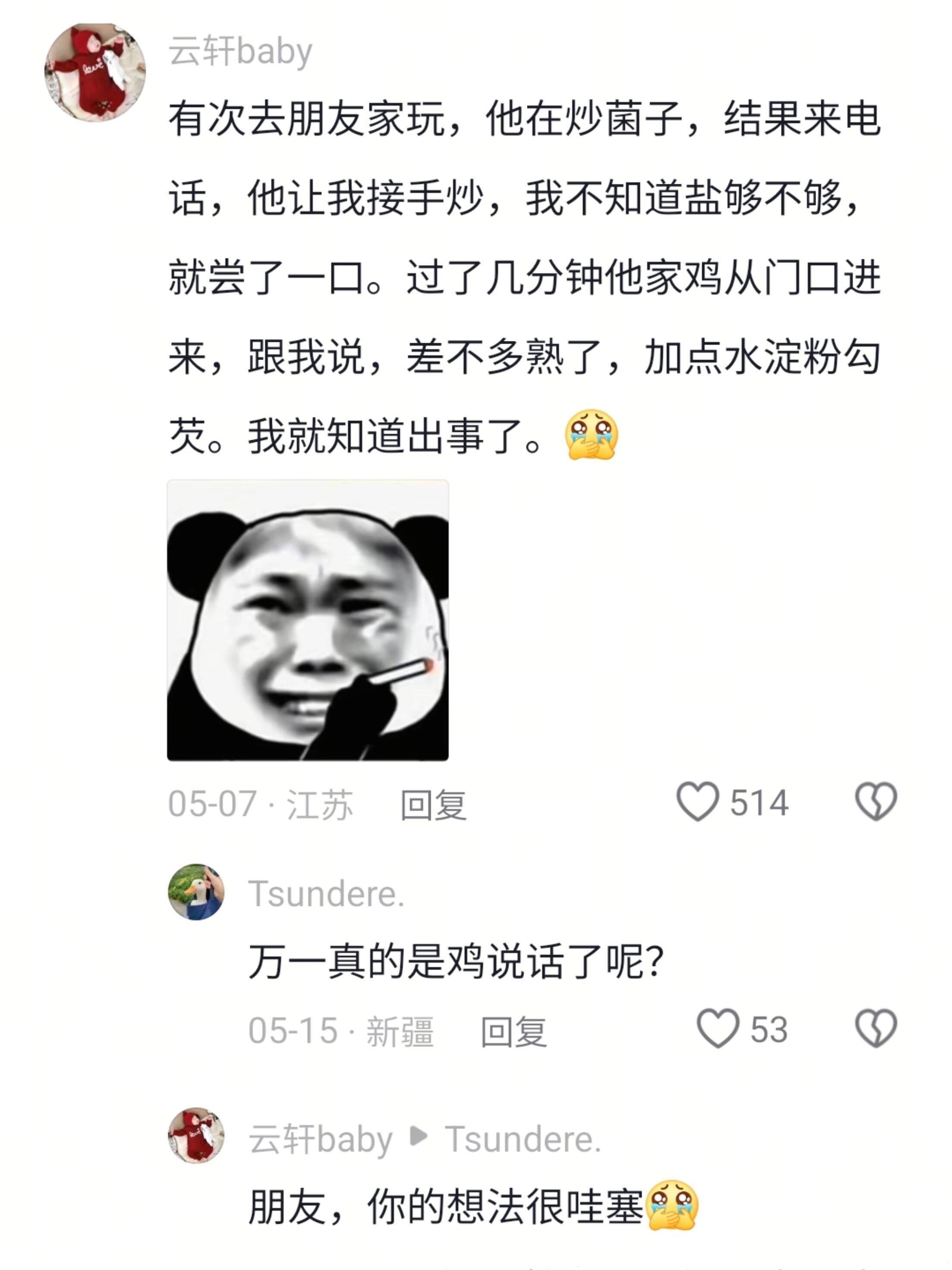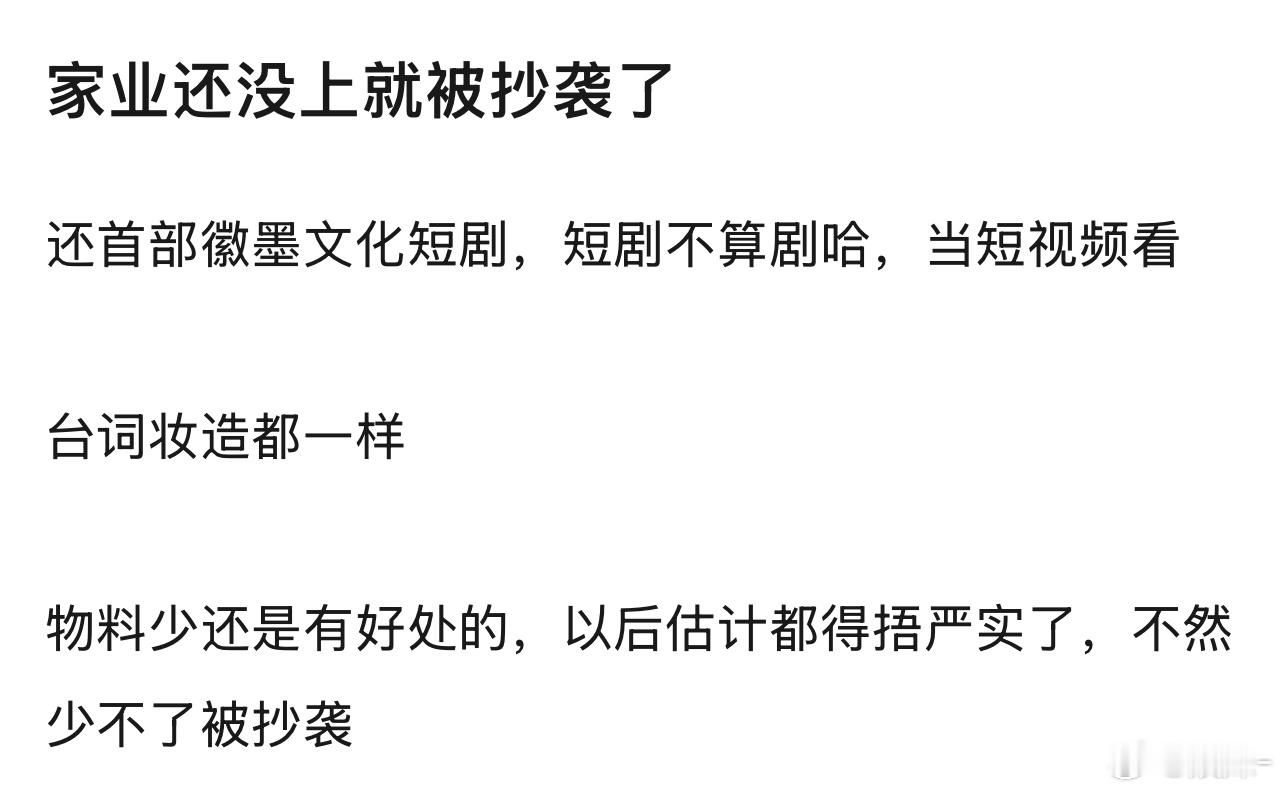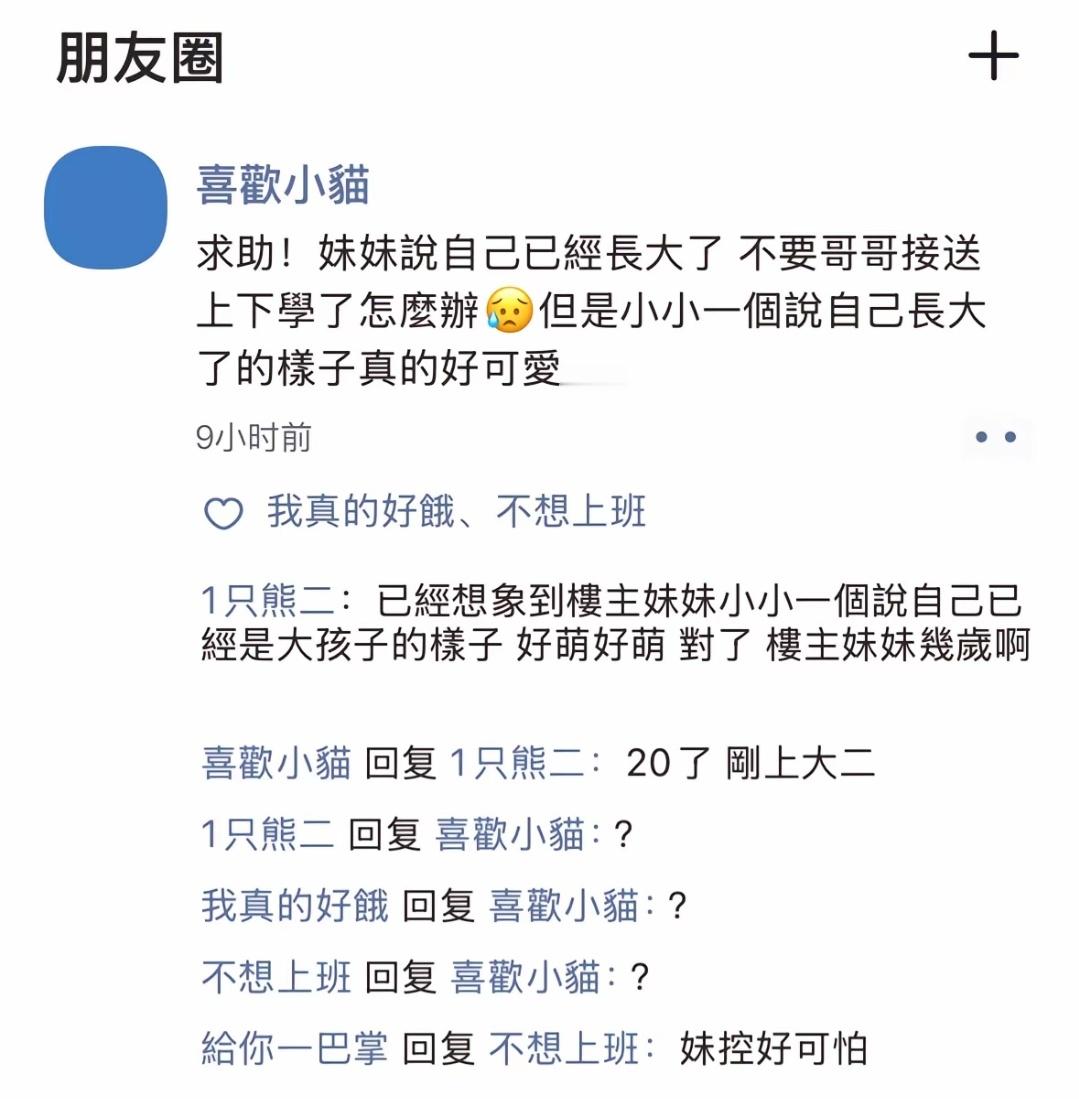1937年,一女人抱着孩子躲在芦苇荡,不料被日军发现了,顿时扑向她,女人抵死不从,日军就夺过她的孩子,并高高举起。可怜的是,危急时刻,躲在不远的丈夫,咬破了嘴唇也不敢吭半声。 那片芦苇荡,本是南京城外长江边的荒僻角落,平日里只有拉纤的纤夫歇脚,那年秋天却挤满了逃难的穷人。姜根福一家八口就藏在这儿——父亲姜老大用破布裹着半袋糙米,母亲怀里揣着八个月大的小儿子,孩子们攥着硬得硌牙的窝头,芦苇秆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极了他们不敢大声哭的抽噎。 躲进苇丛前三天,他们的船沉了。那是条漏风的木船,从淞沪会战打响就漂在江上,日军飞机天天在头顶扔炸弹,江水炸得翻白花,船底板愣是震裂了缝。八月十五那天,船沉在石梁柱,姜老大捞起半袋米和件棉袄,一家人踩着齐脚踝的泥水往岸上爬,村里早空了,锅台上还留着没吃完的米渣,风一吹,门板吱呀响得像哭。 父亲把一家人分两处藏——东边苇丛他带着俩大闺女,西边母亲领三个小子和姜根福,隔了百来米,约定夜里咳嗽三声报平安。他说:“分开躲,留条根。” 可谁能想到,最先出事的是最小的孩子。后半夜,小弟弟饿醒了,哭声细得像蚊子叫,母亲用舌尖舔化窝头喂他,孩子吃两口又哭,声音在静悄悄的苇丛里传得老远。 日军巡逻队就是被哭声引来的。七八个兵,皮靴踩泥水咕叽响,手电光柱在苇尖上扫,像鬼火跳。母亲赶紧把孩子按进怀里,胸口死死压住,可那孩子哭得更凶了,小胳膊小腿乱蹬。光柱“唰”地停在他们藏身的洼地,一个日军哇啦大喊,刺刀就从苇秆缝里伸进来了。 母亲往后缩,脚下是浅水洼,一踩就陷进去,泥水溅了满脸。她空出一只手,照着最近的日军脸就扇过去,“啪”的一声脆响,那兵捂着脸骂,另一个兵扑上来撕她衣襟。她用膝盖顶对方肚子,兵退了半步,她趁机咬住那兵手腕,牙嵌进肉里,血顺着胳膊肘往下滴。 旁边的日军围上来,一个抱住她腰,一个用刺刀挑她肩胛——刀进去半寸,拔出来时血喷了半尺高。她松了口,却反手抓住撕她衣服的兵,头往对方膝盖上撞,兵疼得嗷嗷叫,矮胖的那个日军不耐烦了,弯腰捞起地上的孩子,像拎小鸡似的举过头顶。 孩子在半空蹬腿,脸憋得发紫。母亲疯了似的扑过去,抱住那兵的大腿,指甲抠进裤管,嘴啃他小腿肚。兵疼得腿一抽,枪托砸在她肩上,“咔嚓”一声,骨头裂了。她还是不松,直到另一个兵用刺刀再扎她后背,她才软下去,手指却还勾着兵的裤脚。 那日军狞笑一声,把孩子往空中抛——抛起来,接住,再抛。孩子哭声断了又续,母亲在泥里爬,伸手够孩子的脚,指尖刚擦到鞋尖,就被那兵一脚踹在胸口,咳出的水混着血。她再爬,这次抱住兵的腰,腿缠他小腿,两人歪歪扭扭倒在泥里,孩子“咚”一声掉在地上,再没出声。 二十米外的苇丛里,姜老大眼睁睁看着。他攥着泥块的手直抖,指节发白,嘴唇咬得出血,血珠子滴进泥里,洇开一小片红。大闺女拉他胳膊,他一巴掌打开,却还是没敢站起来——他知道,出去就是全家死绝。 日军走后,苇丛静得可怕。风还在吹,江水拍着岸,母亲躺在血泊里,胸口两个枪眼,像咧开的嘴。小弟弟歪在她旁边,小腿弯着,脸贴着她的胳膊,泥盖住了半张脸。姜根福爬过去,碰了碰弟弟的手,冷的,硬的,像块石头。 父亲用草席裹了母亲和孩子,在江堤边挖了个浅坑。土太硬,他用木棍刨,蚯蚓从土里钻出来,在月光下扭。他把两人并排放进去,盖了层薄土,插了根断苇茎当记号。姜根福看着那苇茎在风里晃,忽然想起母亲白天说的:“等天亮了,咱往上游走,找个没炮声的地方。” 天亮时,雾从江面升起来,笼住苇丛,也笼住他们剩下的五口人。姜老大领着孩子们沿堤走,谁都没说话,姜根福攥着手里的泥块,一直攥到泥干成粉。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夜里,芦苇荡里藏了三十多口人,活下来的不到十个。 八十年代,南京建纪念馆,姜根福去了。他指着照片里的芦苇荡,嘴唇上那道当年咬出的疤还红着,说:“我娘到死,手都朝着弟弟的方向。” 展柜里放着根干枯的苇茎,是后来修堤时从那片浅坑里挖出来的,茎尖还歪着,像在指什么方向。 穷人家的命,在那年头真就不如芦苇秆吗?可姜根福活了下来,带着那道疤,把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说:“得记着,那苇丛里埋着的,都是想好好活的人。” 风又吹过芦苇荡,沙沙响,这次听着像在说:“没忘,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