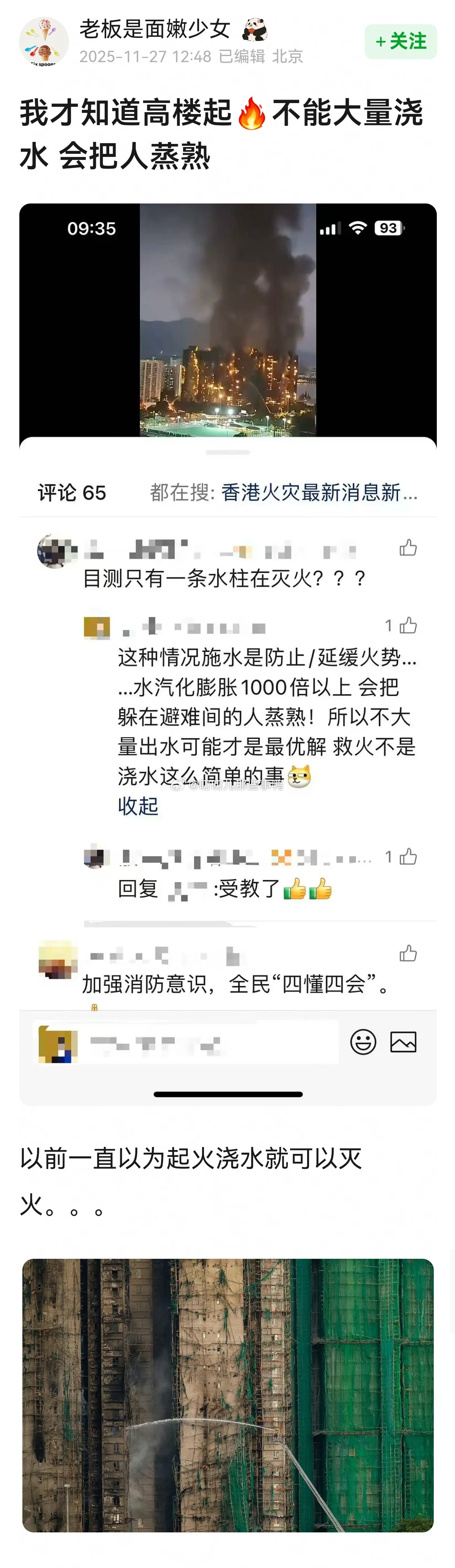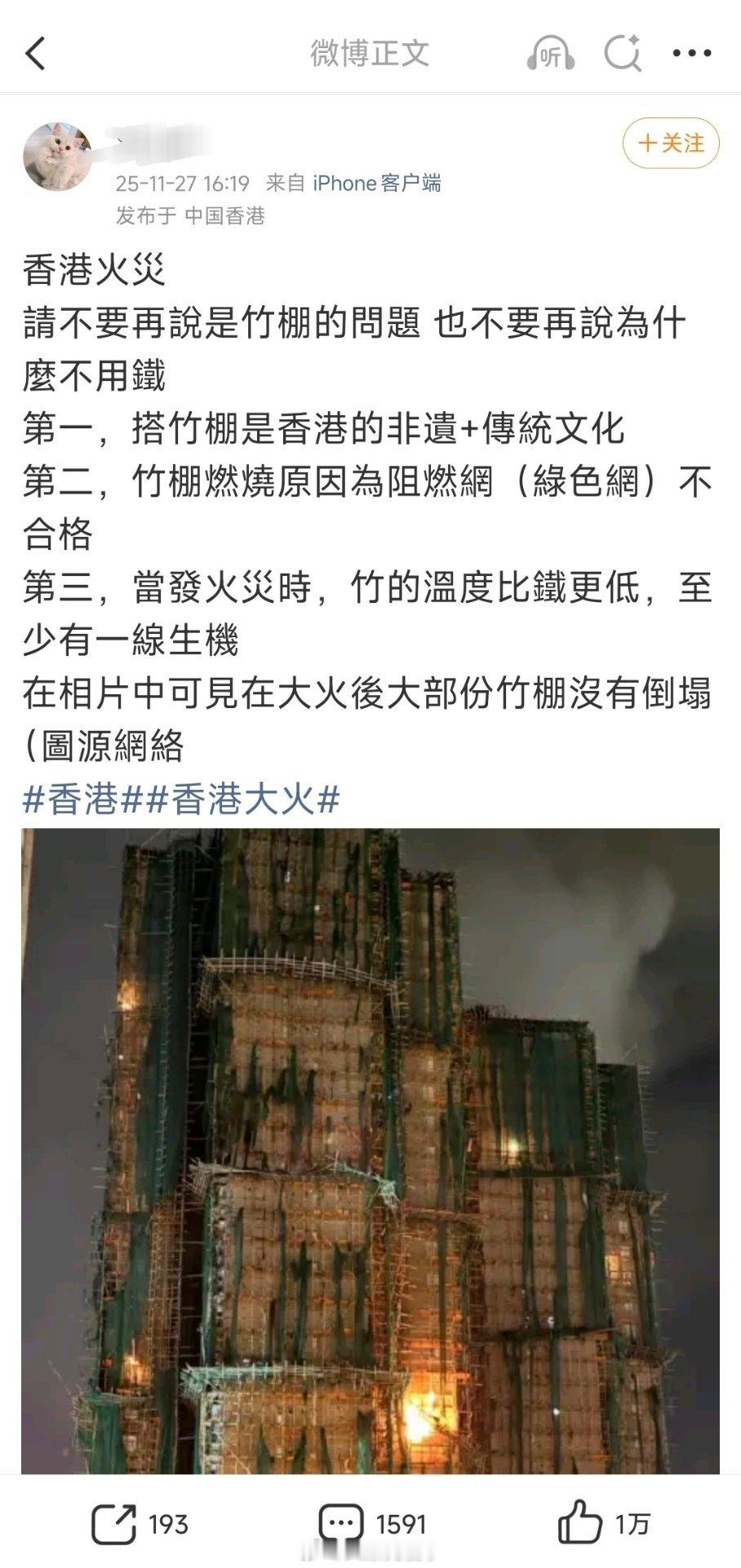一九八四年那会儿,我花了三百块钱买了个媳妇儿,没想到第二年开春,她娘家人浩浩荡荡来了二十口子,直接堵在了我家门口。这事儿得从头说起,那会儿我们这山旮旯里,穷得叮当响,十里八乡的光棍汉能凑成一个排。我爹娘走得早,就给我留下三间土坯房,年近三十还说不上媳妇,眼看就要绝户,心里急得像猫抓。村里有个叫王婆的,专干牵线搭桥的营生,其实就是从更穷的山那边往这边“介绍”姑娘。 一九八四年的风,刮过我们这山旮旯时,总带着股土腥味。 我爹娘走得早,就留下三间土坯房,墙缝里还塞着去年的玉米须,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 那年我二十九,十里八乡的光棍汉能凑成一个排,我是排里最蔫的那个——眼看就要绝户,夜里躺在土炕上,听着隔壁老李家娃娃哭,心里急得像猫爪子挠。 村里王婆是个能人,专干“牵线搭桥”的营生,其实就是从更穷的山那边往这边“介绍”姑娘。 她揣着袋炒瓜子来我家那天,太阳正毒,晒得土坯墙发烫。 “后生,给你寻个媳妇,三百块,保准能生娃。”她嗑着瓜子,唾沫星子溅在我家缺了角的八仙桌上。 三百块,是我攒了五年的血汗钱。 卖了三头猪、二十只鸡,又跟表叔借了五十,才凑齐那沓用红布包着的票子,放在炕席底下压了三夜,每夜都梦见红布包变成了个胖娃娃。 她来的那天,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辫梢沾着草屑,见人就低头。 头半个月,她没跟我说过三句话。 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把鸡粪堆得方方正正;晚上就着油灯纳鞋底,纳得针脚比我娘在世时还匀,纳好的鞋底摞在炕角,像座小小的山。 我试着跟她搭话:“你……叫啥?” 她手一顿,针鼻儿扎了手,血珠渗出来,她慌忙用嘴吮了吮,低声说:“秀。” 秀。我在心里默念了三遍,觉得这名字比山泉水还清亮。 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她做饭,我下地,等开春种上玉米,秋天收了粮,就跟她圆房,生个娃,给老李家续上香火。 没想到,第二年开春,刚下过一场雨,院里的泥还没干,就听见院外有人喊:“李秀!李秀在家不!” 我正喂牛,手里的草叉子“哐当”掉在地上。 扒着门缝一看,黑压压一片人,足有二十口子,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穿件黑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攥着根扁担,脸膛红通通的,像是刚跟人吵过架。 “把人交出来!”汉子朝门里吼,唾沫星子喷在门板上,“我们家秀不是让人卖的!” 我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秀从屋里出来了,她站在我身后,蓝布褂子洗得更白了,手里还攥着半根没纳完的鞋底。 “爹。”她喊了一声,声音抖得像风中的玉米叶。 后来我才知道,秀家比我们这山旮旯还穷,她弟弟要娶媳妇,对方要八十块彩礼,她爹娘实在没办法,才让王婆把她“带”出来——王婆跟她爹娘说,是去山外给人当保姆,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寄钱回家。 那二十口子,是她爹、三个叔叔、五个堂兄,还有村里的几个长辈,走了两天两夜山路,一路打听着找来的。 她爹红着眼圈骂我:“你这挨千刀的,我们秀是好人家的闺女,不是牲口!” 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只会蹲在地上搓手,土坷垃沾了满手。 秀突然开口了:“爹,他对我好。” 她爹愣住了。 “他没打我,没骂我,”秀的声音慢慢稳下来,“早上给我烧热水洗脸,晚上给我掖被角,前天我咳嗽,他走了十里山路去镇上买药。” 二十多号人都不说话了,院子里只有风吹过玉米地的沙沙声。 最后,秀爹叹了口气,把扁担扔在地上:“三百块,你得还给我们。” 我说:“我还,我现在就去借。” 秀拉了拉我的胳膊:“不用,我攒了五十,你再凑二十五,剩下的……让我弟弟先欠着,等秋收了卖了粮食还。” 那天下午,秀的家人走了,她爹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刀子,又像带着点托付。 秀留了下来。 后来我们真的圆了房,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抱着娃在院里转圈,土坯房的墙缝好像都不那么漏风了。 再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我把土坯房拆了,盖了砖瓦房,秀还是喜欢纳鞋底,说买的鞋不如自己纳的舒服。 现在我孙子都上小学了,有时候吃饭,秀会突然说:“当年要不是你去镇上给我买药,我爹说不定真把我拽走了。” 我就笑,给她夹块肉:“那是,我那会儿就知道,不能让你走。” 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是药留住了她,是那时候山里的穷,困住了太多人,也让一点点好,就成了能抓住的光。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自由,今天吵明天好,哪知道当年我们那样的,三百块钱就能买一段“姻缘”,也能毁了一个姑娘的一辈子——幸好,秀没让我毁了她。 偶尔路过当年王婆住的那间破屋,早就塌了,只剩半堵墙,墙缝里也塞着玉米须,风一吹,还是簌簌往下掉。 只是现在掉下来的,好像不那么扎人了。
一名钳工学徒非常喜欢显摆,无论任何物品都要玩个过瘾,师傅多次警告他勿乱动,对于一
【2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