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盟军在追踪德国U型潜艇时,水下设备总传来一阵阵奇怪的碎裂声,“噼里啪啦”就像木柴燃烧,令人烦不胜烦。 这事儿透着一股邪乎劲。他们立刻组织了一批顶尖的科学家,包括加州大学的海洋研究部门,给他们下了死命令:必须查清噪音来源。 科学家们可不信什么鬼神。他们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水下麦克风,跑遍了全球的“噪音污染区”。 他们很快发现,这声音跟德国人没关系。它在某些海域特别强,尤其是在浅海、靠近岩石和珊瑚礁的地方。而且,这声音在晚上似乎比白天更活跃。 调查一步步深入。他们开始在这些“高噪音”区域布网、取样。当他们把样本从水里捞出来,放进实验室的水箱,再把水听器伸进去时…… “噼里啪啦!” 熟悉的声音又来了!清澈的水箱里,噪音源头暴露无遗。 这个让整个盟军海军头痛不已、差点耽误了战局的“纵火犯”,既不是什么高科技干扰器,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海洋现象。 它是一种虾。 这种虾,现在我们叫它“枪虾”或者“手枪虾”。它个头不大,也就几厘米长,但它长了一只非常不成比例的、巨大的“钳子”。 这只钳子,就是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它制造噪音的方式,完全超出了当时人类的想象。 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并不是它两只钳子互相敲击发出的声音。如果是那样,水流一缓冲,啥也听不见了。 它的秘密在于“速度”。 当枪虾猛地闭合它那只大钳子时,速度快得惊人,时速能超过100公里。这个速度在水下会产生一个物理奇迹:它会“甩”出一个极小的真空水泡,这个专业术语叫“空泡”。 这个气泡非常不稳定,在不到一秒钟内就会自行崩溃、内爆。 重点来了。就在这个小到看不见的气泡崩溃的瞬间,它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产生一道强光,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这个声音有多响?在它那个微观世界里,声压能瞬间超过210分贝。 210分贝是什么概念?我们近距离听喷气式飞机起飞,大概是140分贝,就足以永久损伤听力了。枪虾的这一“枪”,比近距离的枪声还要响亮。 更恐怖的是,当气泡崩溃时,其内部的瞬时温度能飙升到几千摄氏度,堪比太阳表面。这股冲击波足以击晕甚至杀死它附近的小鱼小蟹。 这就是枪虾捕食和打架的方式。它不是用钳子“夹”你,它是用“声波冲击”轰你。 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来。 在二战的海底,不是一只枪虾在“开火”。它们是群居动物。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只枪虾,聚集在珊瑚礁和岩石缝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区”。 然后,这几百万只虾,此起彼伏地,不停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它们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巨大的“声学暗礁”。这片背景噪音,在声呐兵的耳机里,就成了那片永不消停的“燃烧的木柴”。 这事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人类在那儿打得你死我活,动用了航母、战列舰、潜艇,发明了雷达和声呐,自以为是地球的主宰。结果,在最关键的侦察环节,被一群还没手指甲盖大的小虾米给“缴械”了。 这简直是自然界开给人类的一个黑色幽默。 它告诉我们,在海洋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里,我们引以为傲的“高科技”,有时候真的非常脆弱。我们试图去“听”敌人,却没想到,海底的原住民们,它们“说话”的声音,比我们的战争机器还大。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盟军的科学家们,尤其是马丁约翰逊博士,在搞清楚是虾在作怪之后,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们很快转变了思路:“既然这个噪音我们消不掉,那它能不能为我所用?” 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意识到一个关键点:既然这片噪音能掩盖德国U型潜艇,那它同样能掩盖我们自己的潜艇啊! 于是,美国海军做了一件非常有前瞻性的事。他们没有去研究怎么“过滤”虾声,反而开始着手绘制“全球枪虾分布图”。 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区,对付日本海军时,这份“噪音地图”成了盟军潜艇指挥官的宝贝。 这些小小的枪虾,在二战中,无意间充当了“干扰敌军”和“掩护友军”的双重角色。 战争早已结束。U型潜艇和那些驱逐舰都生了锈。 但那些枪虾,它们根本不知道人类曾经打过一场世界大战。它们不在乎什么纳粹德国,也不在乎什么盟军。 直到今天,2025年的今天,在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浅海,那几亿、几十亿只枪虾,依然在它们的海底家园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猛烈地扣动着它们的“扳机”。 “噼里啪啦……” 这声音,是它们捕猎的声音,是它们宣示领地的声音,也是它们求偶的声音。 对于现代海军来说,“生物声学”早已成为一门必修课。现代核潜艇追求的是极致静音,而侦测它们,就必须学会过滤掉这些来自海洋生物的、强有力的背景噪音。 那个在二战时让声呐兵烦不胜烦的“噼里啪啦”声,如今是海洋学家们研究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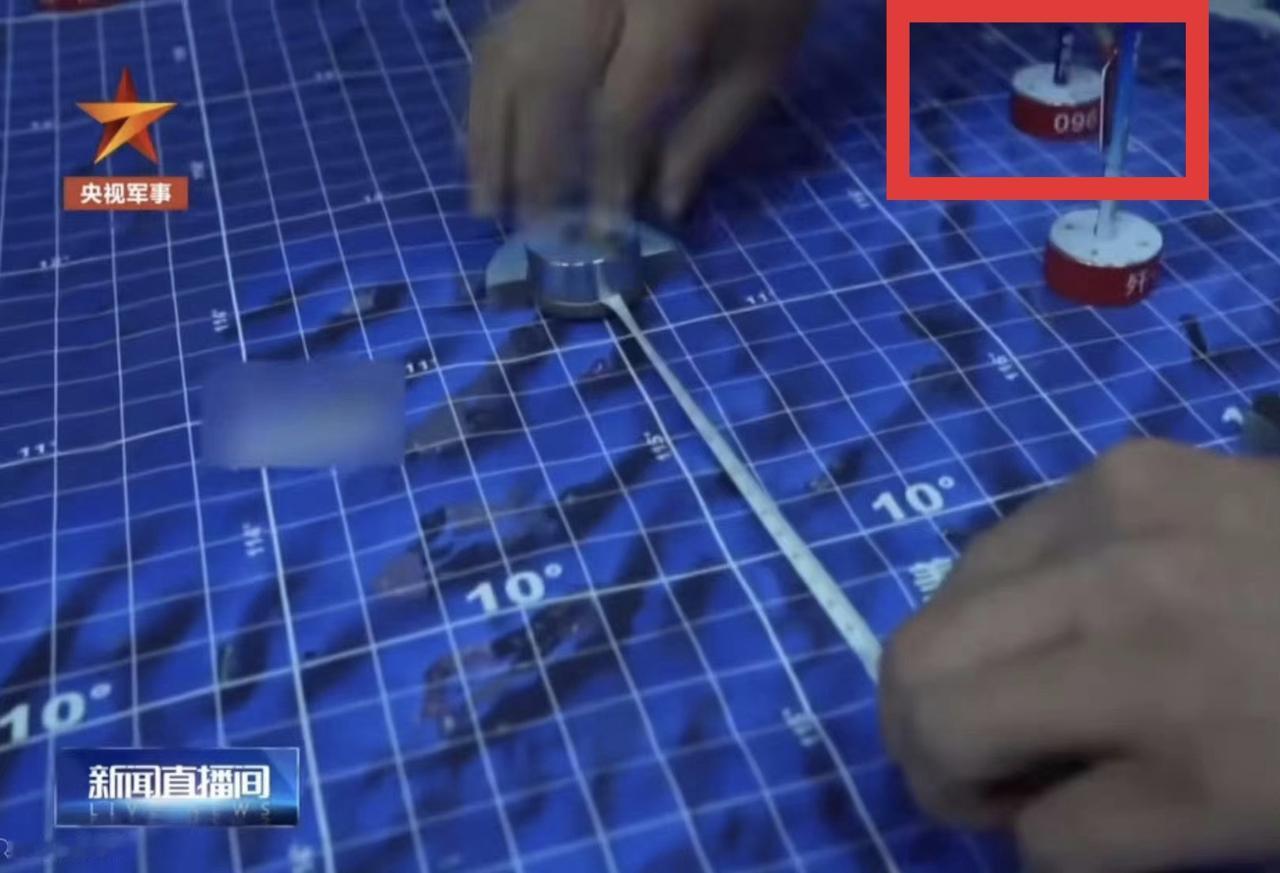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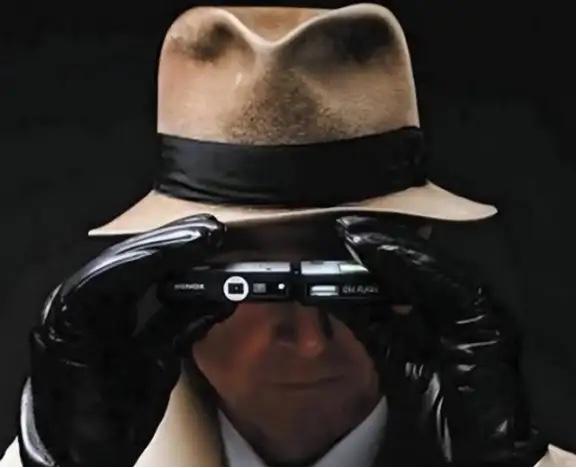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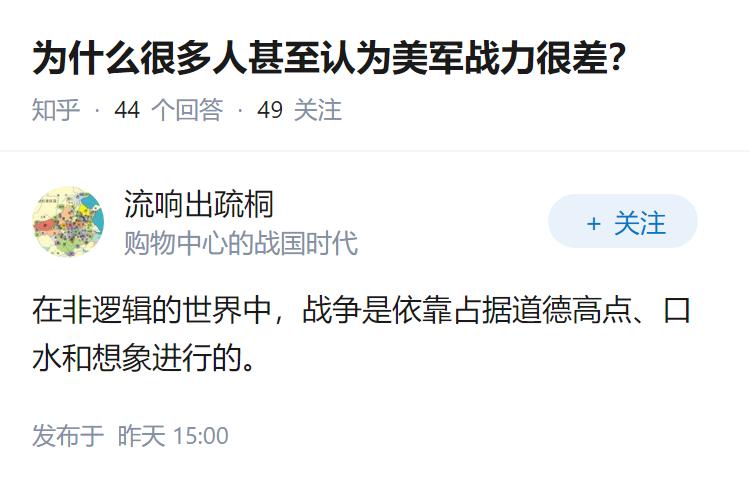

嗯哈
雀尾螳螂虾
用户50xxx31 回复 11-24 02:17
不是
db
群居它们互相不影响吗?
今夜无人打牌
那个叫什么鱼雷来着?仿照这个弄的?
8538383
皮皮虾
油条泡豆腐
扯淡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