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怎么样? 提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必然脱口而出;说起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闲逸也早刻进记忆。这两位北宋的“文化顶流”,不光文章传千古,彼此的交情更是经得起风雨磨的真骨头,既是政坛上并肩扛事的战友,也是文坛里彼此识货的知己,连人生起伏都紧紧绑在一起。 论年纪,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算是前辈。欧阳修刚踏入仕途时,范仲淹已凭《岳阳楼记》的雏形思路和戍边功绩名声在外。两人真正结下深交,是在庆历新政那阵风口浪尖上。1043年,范仲淹牵头搞改革,要整肃吏治、改善民生,刚任知谏院的欧阳修立马站到他身边,成了最硬核的支持者。 保守派看不惯新政,就拿“朋党”说事,这在古代官场是皇帝最忌惮的罪名。当时有个叫高若讷的谏官,本该替新政说话却装哑巴,欧阳修气不过,直接写了封《与高司谏书》,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对方的失职兜底揭穿。这封骂信彻底捅了马蜂窝,保守派趁机诬告欧阳修和范仲淹结党,宋仁宗也被说动了。 别人都怕沾“朋党”的边,欧阳修偏不躲。他干脆写了篇《朋党论》呈给皇帝,直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说君子的交情是靠道义维系,小人的交情才靠利益捆绑,劝皇帝要辨明真假朋党。 这篇文章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可还是没能保住新政。1045年,范仲淹被贬出京,欧阳修也因“外甥女案”的无妄绯闻受牵连,被贬到了滁州——后来写出《醉翁亭记》的地方。 政坛上是生死相托的战友,文坛里更是彼此赏识的知己。两人都看不惯当时浮华空洞的骈体文,力推古文运动,要让文章“言以载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得沉雄悲壮,把家国情怀融进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则以浅白文字写山水之乐,藏着“与民同乐”的初心,两人文风不同,却都踩中了“文以载道”的核心。 最见交情的是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给他写《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的事。碑文中,欧阳修如实写了范仲淹曾与早年政敌吕夷简“欢然相约勠力平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特别不满,觉得不该提父亲和“仇人”的交集,要求删改。 可欧阳修坚决不松口,因为他亲眼见过范仲淹写给吕夷简的书信,知道这段史实是真的。即便面对挚友家人的质疑,他也守着“事信言文”的原则,这份较真反而更显对范仲淹的尊重。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人生轨迹像照镜子。范仲淹戍边时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欧阳修出使契丹时也记录下“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范仲淹被贬邓州成就《岳阳楼记》,欧阳修被贬滁州写出《醉翁亭记》,都是在逆境里把情怀炼成千古名篇。 范仲淹称欧阳修“器质纯美,学问淹通”,欧阳修则说范仲淹“公之功德,不可胜书”,这种互相认可从不是虚话。 他们的交情,不是酒肉朋友的热闹,而是“同道者”的默契。你搞改革我就挺你,你被贬我就陪你,你去世我就守着事实写你。北宋的文坛因他们多了风骨,政坛因他们多了亮色,而这份跨越年龄、经得起风雨的情谊,也和他们的文章一样,成了留传千年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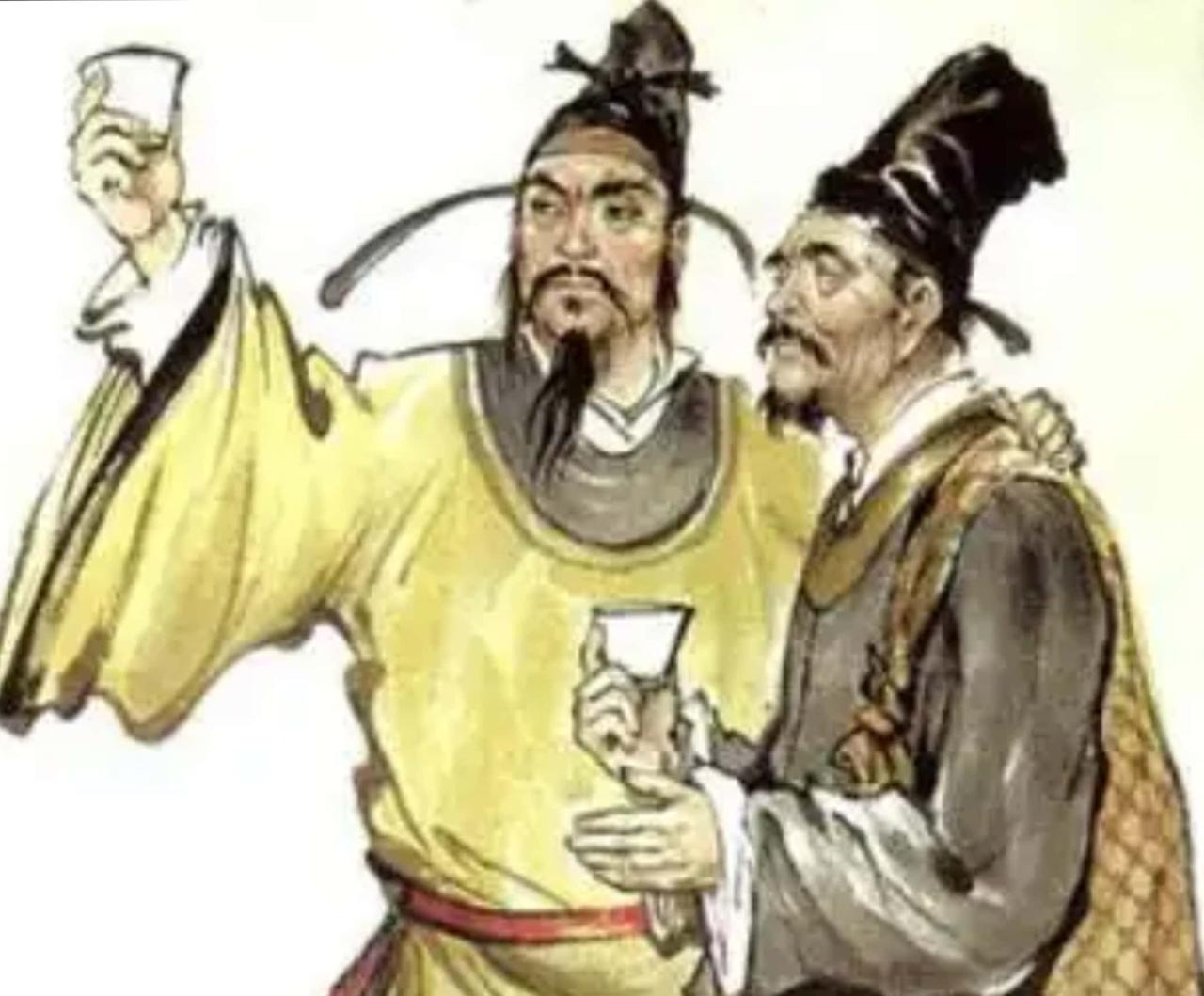

![要不是建文帝太狠,朱棣也不会反[吃瓜]](http://image.uczzd.cn/1715909485931372204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