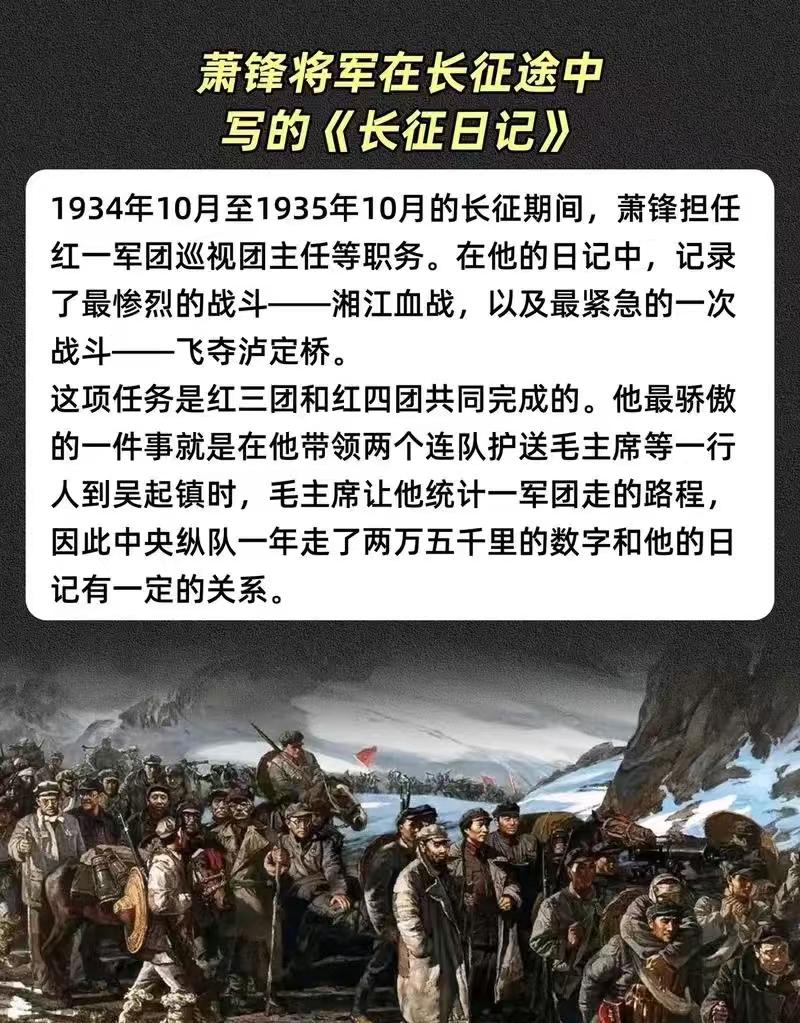长征开始后,红军逐渐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只是借道过境,地方军阀大多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有时甚至只追不堵,还会私下给红军一些帮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的“送客”计划,又比如龙云主动献地图、送药品。 那时的红军刚经历湘江血战,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锐减到三万,疲惫不堪的队伍急需喘口气。而国民党内部却乱成一团:蒋介石想借“剿共”之名,让中央军趁机渗透地方,把李宗仁的广西、龙云的云南都变成“中央地盘”;地方军阀们心里门儿清,表面喊着“剿共”口号,暗地里却打着“送客”的主意——只要红军不占自己的地盘,就犯不着拼尽全力去打。 熟悉民国军阀史的人都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早就和蒋介石斗了十几年。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差点把桂系打垮,后来桂军靠着“保境安民”才稳住广西。1934年红军要来,白崇禧在桂军高级会议上拍了桌子:“红军是路过的客人,蒋介石才是要抢家的豺狼!咱们要是跟红军拼得两败俱伤,中央军一进来,广西就不是咱们的了!” 这话成了桂军的行动准则。红军进入桂北时,桂军在湘江沿岸布了防,却没真下死手。有红军战士后来回忆,过兴安时看到桂军在山头上开枪,子弹却总往天上飘;晚上宿营时,还能听到桂军哨兵在远处喊:“你们赶紧走,别在这儿耽误!”更绝的是,桂军故意把湘桂边境的浮桥留着,没烧也没拆,就等着红军快点过境。 白崇禧还搞了个“三面堵、一面放”的花招。他让桂军在红军来的路上布重兵,摆出要打的架势,却在红军往贵州去的方向故意留空当。蒋介石发电报骂他“剿共不力”,白崇禧就回电说“红军机动性太强,桂军兵力不足,实在堵不住”,暗地里却让部队“只追不堵,别跟太紧”。后来有人算过,红军过桂北的七天里,和桂军的正面冲突加起来不到三次,损失远比湘江战役时小。 反观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倒是追得紧,可桂军根本不配合。薛岳想让桂军在前面堵,自己在后面追,把红军围在桂北,白崇禧却故意把部队往两边撤,还跟薛岳说“桂军要守广西腹地,抽不出人”。结果中央军追到时,红军早就从桂军留的通道走了,薛岳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骂娘。 到了1935年2月,红军进入云南,龙云的“操作”更让人意外。这位“云南王”表面上派滇军去堵,暗地里却找了个亲信,让他装成烟贩,把一张标满滇军布防、渡口和补给点的地图,偷偷塞给了红军联络员。地图是龙云亲手改过的,连哪里有山泉、哪里能找到粮食都标得清清楚楚,比红军自己侦察的还详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龙云还让亲信带了些药品——有治疗外伤的草药,还有几盒奎宁。那时云南疟疾横行,红军不少战士都得了病,奎宁在当时是救命药。亲信跟红军联络员说:“龙主席说了,红军只是借道,别在云南耽误太久,这些药算给你们路上用的。”后来红军巧渡金沙江,靠的就是这张地图,知道哪个渡口没滇军防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江。 龙云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云南是他的“独立王国”。从1927年掌控云南开始,他就不让中央军踏进云南一步,连税收、军队都自己说了算。蒋介石想让滇军全力剿共,其实是想让滇军和红军两败俱伤,然后派中央军“接管”云南。龙云在日记里写:“红军过云南,最多半个月;中央军进来,就再也走不了了。” 红军也摸透了地方军阀的心思,专门搞了“区别对待”的策略。路过桂北时,红军贴的标语是“红军只打蒋介石,不打广西老百姓”“借道过境,秋毫无犯”;到了云南,又跟当地百姓说“红军不占云南一寸地,只为北上抗日”。这种宣传让桂军、滇军更放心——知道红军不是来抢地盘的,就没必要真刀真枪地打。 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从来就不是一条心——蒋介石想把全国的权力都攥在手里,地方军阀想守住自己的地盘,双方的矛盾比国共矛盾还深。红军刚好利用了这种矛盾,为长征减少了不少阻力。 要是没有桂军的“送客”,红军可能要在桂北多打几场恶仗,兵力损失会更大;要是没有龙云的地图,红军巧渡金沙江可能没那么顺利,说不定会被滇军和中央军围堵。这些地方军阀的“小动作”,虽然是为了自保,却在无形中帮了红军一把,成了长征路上的“意外助力”。 后来蒋介石知道了桂军、滇军的“放水”,气得直拍桌子,却也没办法——桂军在广西根基太深,滇军在云南说一不二,他要是真把李宗仁、龙云逼急了,他们说不定会联合红军反蒋。只能在电报里骂几句,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回头看,长征能成功,既有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也有对敌人内部矛盾的精准把握。李宗仁、龙云这些地方军阀,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地盘,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红军长征的“间接推手”。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有时候敌人的“私心”,反而会成为革命的“转机”。 要是当时地方军阀都跟蒋介石一条心,全力剿共,红军的长征之路会难上百倍。可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给了红军喘息和机动的机会。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团结才是力量,要是内部不团结,再强大的势力也会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