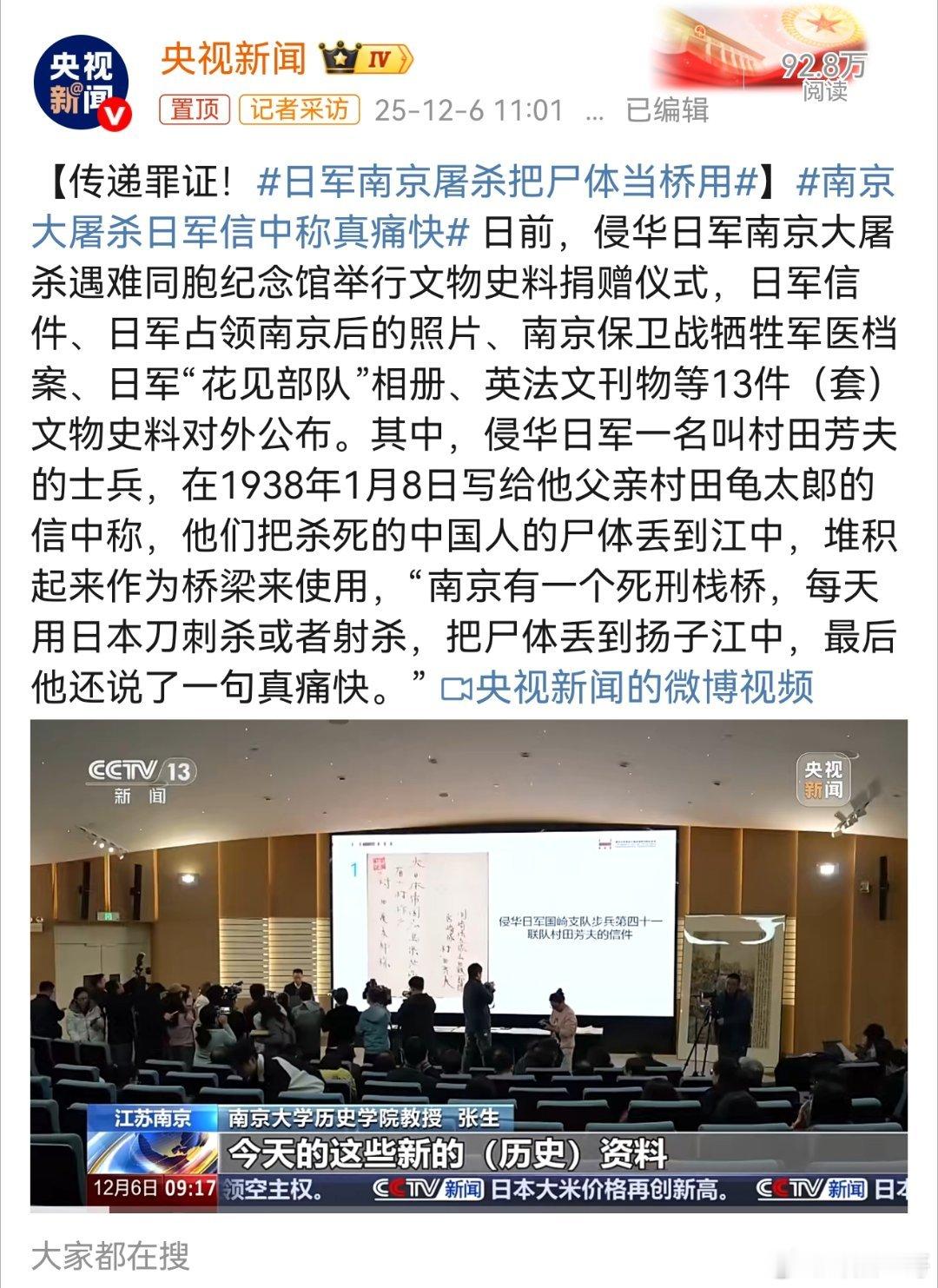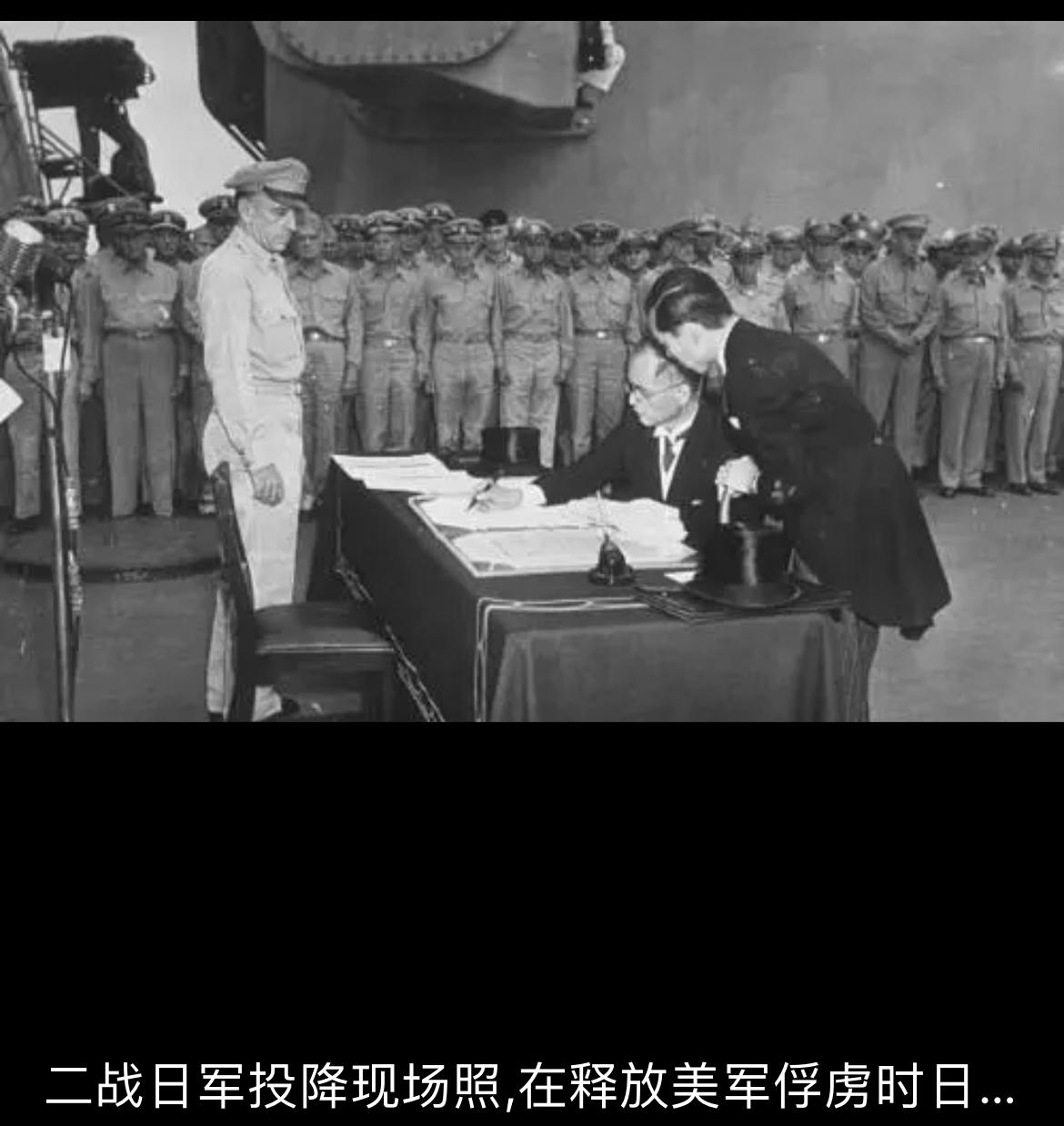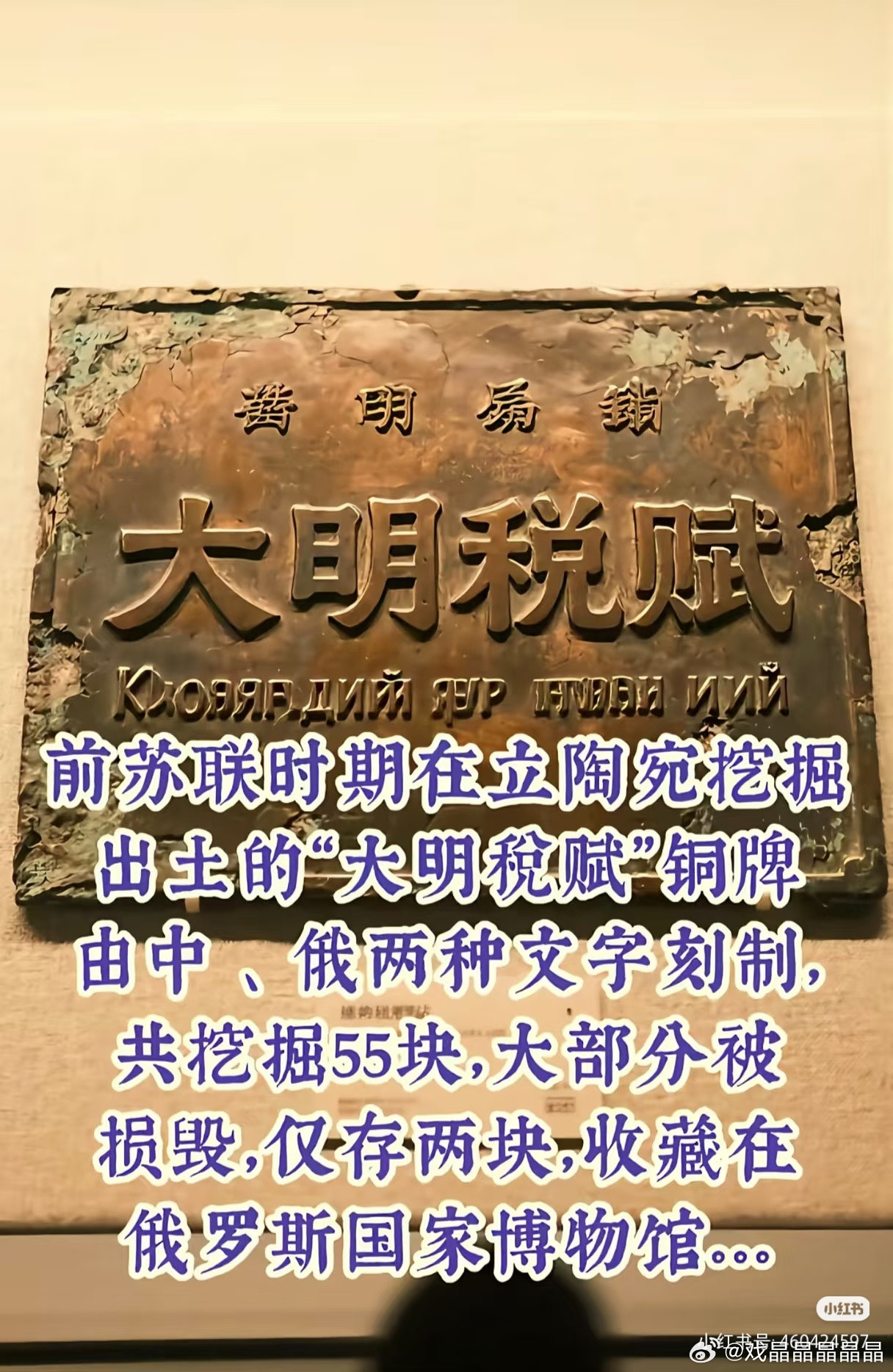明朝末年,一位葡萄牙传教士漫步在南京街头,被眼前景象震撼:街道上人头攒动,每艘船上都满载货物,仿佛欧洲的节日集会,却远比欧洲任何城市都拥挤热闹。 明朝末年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个历史谜团。官方统计显示纳税人口约5805万,但这仅包括成年男性。若算上妇女、儿童、官员和太监,当时中国总人口接近三亿,这个数字与现代史学家的估算相符。 这些人都生活在哪里?嘉靖年间的一份地方税收记录显示,一个小县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就有230多种。万历年间,学者吕坤感叹“天下商人不知几百万矣”。 人口学家曹树基研究表明,1630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1.92亿。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中国已有1.6亿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当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7亿亩,平均亩产1.5石粮食,总产量足够养活2亿人。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新作物正是此时传入中国,为粮食供应加了道保险。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矛盾。就在这人口高峰期的1630年代,北方各省却陷入一片饥荒。原因是气候变化引发了“小冰河时期”,北方连年大旱,南方洪涝不断。 明朝后期的手工业发展令人惊叹。景德镇的瓷器工匠超过十万人,每年生产百万件精美瓷器销往海外。松江府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每年产出6亿匹棉布。 在苏州、扬州等大城市,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这被史学家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明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超同期欧洲国家。当英国富豪拥有几万英镑就算巨富时,中国商人动用几百万两银子进行贸易已是寻常事。 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年收入达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繁华的南京城内,中国商人信用良好、守时可靠。富商们的诚信给曾德昭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提到“这一点我多年在葡萄牙和中国的经商经验均有所证实”。 晚明经济繁荣背后,有一个关键推手:白银。当时中国就像个巨大的“金融吸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 西班牙商人以菲律宾为基地,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将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据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研究,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这背后是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精美商品,而欧洲人只能用白银支付。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除后,中国商船频繁驶往马尼拉,运回墨西哥银元。 仅福建泉州月港,每年就有千余艘商船驶往马尼拉。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将各种赋税统一折成银两征收,进一步强化了白银的货币地位。然而,对白银的过度依赖也埋下了隐患。当欧洲爆发战争,西班牙禁止白银出口后,明朝立刻遭遇通货紧缩。 晚明社会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过程。《苏州府志》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据学者伊懋可的数据,明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至7.5%,曹树基估计1630年城市化率已达8%。 这些新兴市镇各具特色:松江的朱泾镇、枫泾镇以棉纺织闻名;苏州的盛泽镇、湖州的双林镇是丝织业中心。夜晚的手工业市镇依然灯火通明,工匠们加班加点生产商品。 但城市化也带来了新问题。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今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他担忧“田卒污莱,民不土著”,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 更严重的是区域发展失衡。江南地区大量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粮食依赖湖广供应,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当西北农民因没有白银缴税而破产时,苏州米价却一飞冲天。 明朝的繁荣在1640年左右戛然而止。由于白银输入锐减,江南地区爆发严重通货紧缩。叶梦珠在《阅世篇》中记载,崇祯年间米价十年间上涨十倍以上。 1634年后,西班牙菲利浦四世禁止白银出口,明朝白银输入断流。此前一百年间,流入明朝的白银总量不低于3亿两。突然的货币短缺导致经济循环中断,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 1640年左右,苏州地区米价暴涨,大批人饿死,许多豪宅低价出售却无人问津。顾炎武记录下悲惨景象:“浏阳之民折屋弃产,常鬻妻卖子。”他甚至感叹“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 与此同时,北方鼠疫肆虐。1633年始于山西的疫病,至1643年在北京爆发,造成20多万人死亡。李自成攻打北京时,守城明军因疫病从10万减至5万,且多是老弱病残。 明朝末年的故事提示我们,全球化并非现代独有。四百年前的中国已经通过白银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既从中获益,也受其牵连。那段历史既是镜鉴,也提醒着我们思考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