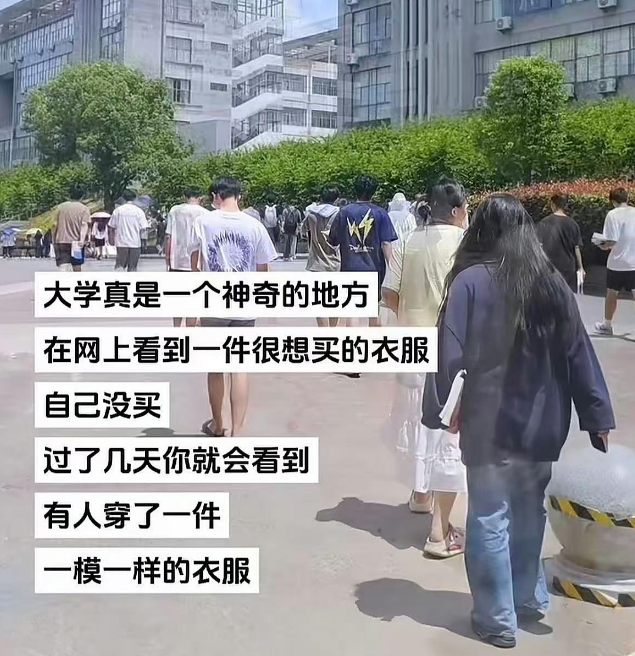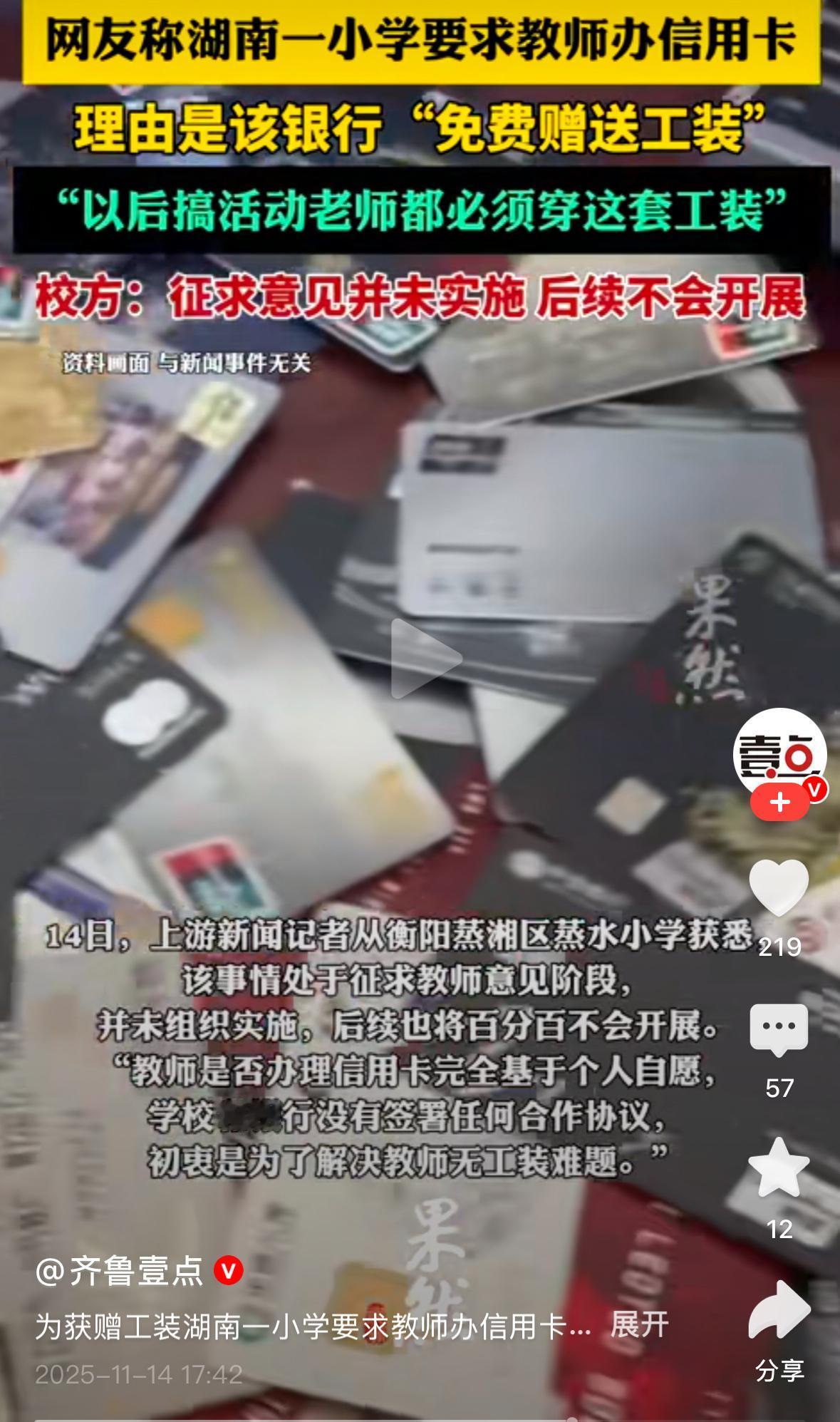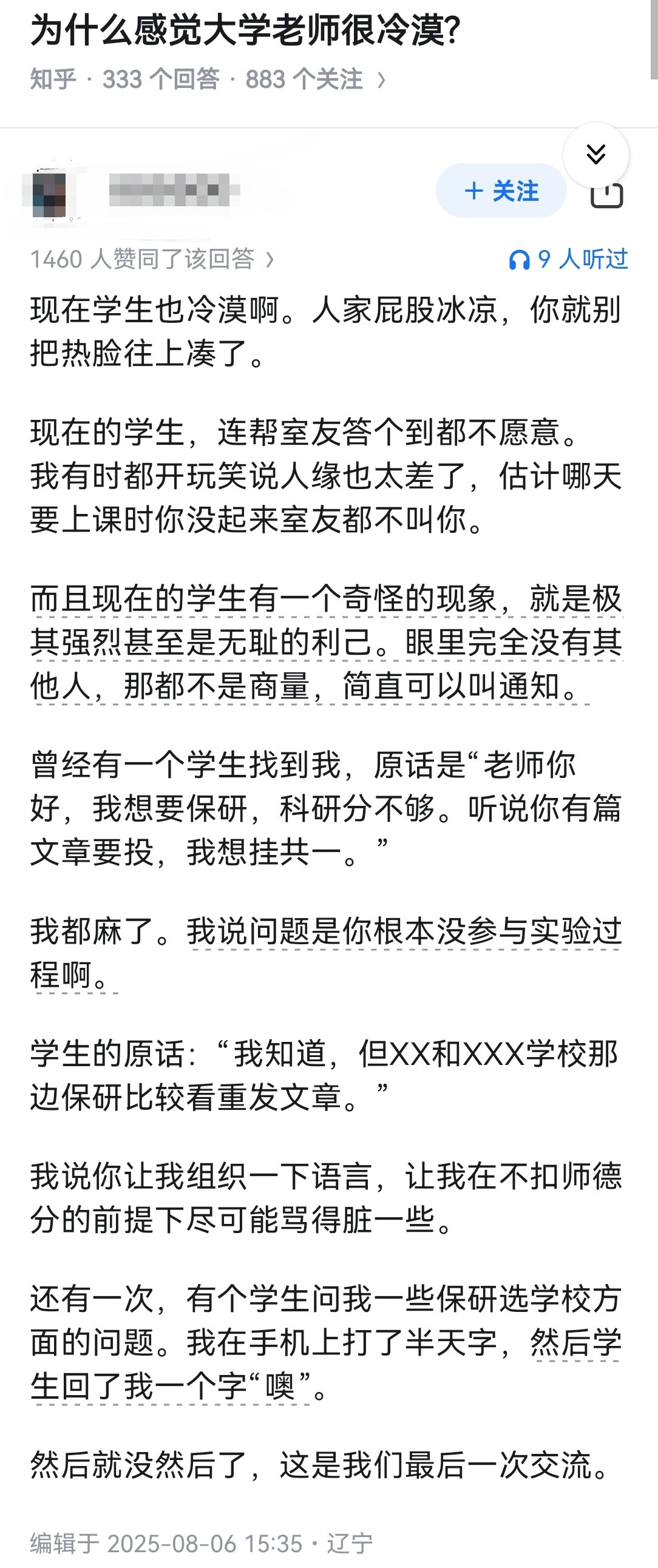2016年,杭州一校长退休,拒绝百万年薪,前往山区支教。谁料半年后,学生少60多个,校长慌忙向上询问,电话那头传来的回应,让他心头一紧:“这种情况,已经很不错了。” 2016年那个秋天,杭州某重点小学的校长周明远退休那天,教育局的领导还特意来送他,说有私立学校开出百万年薪请他去当顾问,让他好好考虑。周校长摆摆手,说早就想好了——去贵州山区的大岩村小学支教。 消息传出去,同事们都觉得他疯了。"周校,您在城里待了一辈子,去那穷山沟遭罪干啥?"他只是笑,从家里翻出旧帆布包,装了两件换洗衣裳,还有满满一箱子书,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三趟中巴,才到了大岩村。 学校就两排平房,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教室里的课桌椅缺胳膊少腿,孩子们冬天只能揣着冻红的手写字。周校长没含糊,第一天就挽起袖子修窗户,找老乡借了锤子钉子,叮叮当当地忙到天黑。 他带的是四年级,开学时满满一屋子孩子,68个,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周校长给他们讲杭州的西湖,讲课本外的故事,还自己掏钱买了篮球和跳绳,每天放学后带着孩子们在泥地上疯跑,笑声能传到山那边。 可没过俩月,周校长发现不对劲。先是最调皮的狗蛋没来上学,他去家访才知道,孩子爹带他去广东打工了,说"读书不如早点挣钱"。没过几天,又有三个孩子跟着父母去了县城,因为"城里学校能学英语"。 他急得嘴上起泡,挨家挨户去劝。有户人家的奶奶叹着气说:"周老师,不是俺们不想让娃读书,家里就指望娃爹在外头挣钱,娃留家里没人管啊。"周校长看着墙上贴的奖状,那是孩子上次考了全班第一得的,边角都卷了边,心里堵得慌。 到放寒假前,他清点人数,黑板上的名字划掉了一大半——68个孩子,就剩25个了。教室突然显得空荡荡的,以前叽叽喳喳的课堂,现在回答问题都没人接话,周校长站在讲台上,感觉心里也空落落的。 他赶紧给县教育局打电话,语气急得发颤:"张科长,我们学校学生少了一多半,这咋整啊?能不能想想办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会儿,张科长的声音透着无奈:"周校长,您别慌。大岩村这情况,算好的了。" 周校长愣了:"这还叫好?" "您是不知道,"张科长叹了口气,"去年隔壁的石头村小学,开学30个学生,年底就剩8个。这几年山里年轻人都往外走,娃要么跟着去城里打工,要么去镇上住校,能留下二十多个,真的很不错了。" 周校长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窗外的山灰蒙蒙的,风卷着落叶打在教室门上,"砰砰"响,像在敲他的心。他突然想起刚来时,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跟他说:"老师,我想考大学,去您说的西湖边看看。"现在那姑娘也走了,跟着父母去了浙江的服装厂。 挂了电话,他在操场蹲了很久。泥地上还有孩子们玩跳房子的格子,是用粉笔划的,被雨水泡得发淡。他掏出手机,翻出刚开学时拍的合照,68个孩子挤在镜头前,笑得露出豁牙,他站在中间,比着"耶"的手势,那会儿还觉得浑身是劲儿。 寒假里,周校长没回杭州。他踩着积雪去家访,把剩下的25个孩子家都走了一遍。有个叫小花的女孩,爹妈不在家,跟着爷爷过,冬天还穿着单鞋。周校长把自己带的棉鞋给她穿上,小姑娘怯生生地说:"老师,我不辍学,我想读书。" 他鼻子一酸,摸了摸她的头:"咱不辍,老师陪着你们。" 开春后,周校长没再纠结学生少了多少。他把那25个孩子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中午带着他们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种菜,说"自己种的菜吃着香";下午放学后,就给他们补英语,用捡来的硬纸板做单词卡。 有回杭州的老同事来看他,见他黑了瘦了,宿舍里除了书就是咸菜坛子,心疼得直掉泪:"放着百万年薪不要,在这儿受这罪,图啥?" 周校长指着教室里读书的孩子,声音不大却特清楚:"你看,这25个娃眼里有光呢。就算只剩一个,我也得教下去——总有人要留在这儿,给他们留点念想,不是吗?"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糊着塑料布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晃悠悠的光斑。孩子们的读书声飘出教室,在山谷里打着转,周校长站在门口听着,突然觉得心里那点慌劲没了。是啊,比起数字,这些声音才更重要。 后来他给张科长回了个电话,说:"我想通了,25个就25个,我好好教。"电话那头笑了:"周校,您能这么想,就比啥都强。" 挂了电话,周校长转身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山高路远,来日方长。"孩子们跟着念,声音脆生生的,像山里的泉水,一点一点,往人心坎里流。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