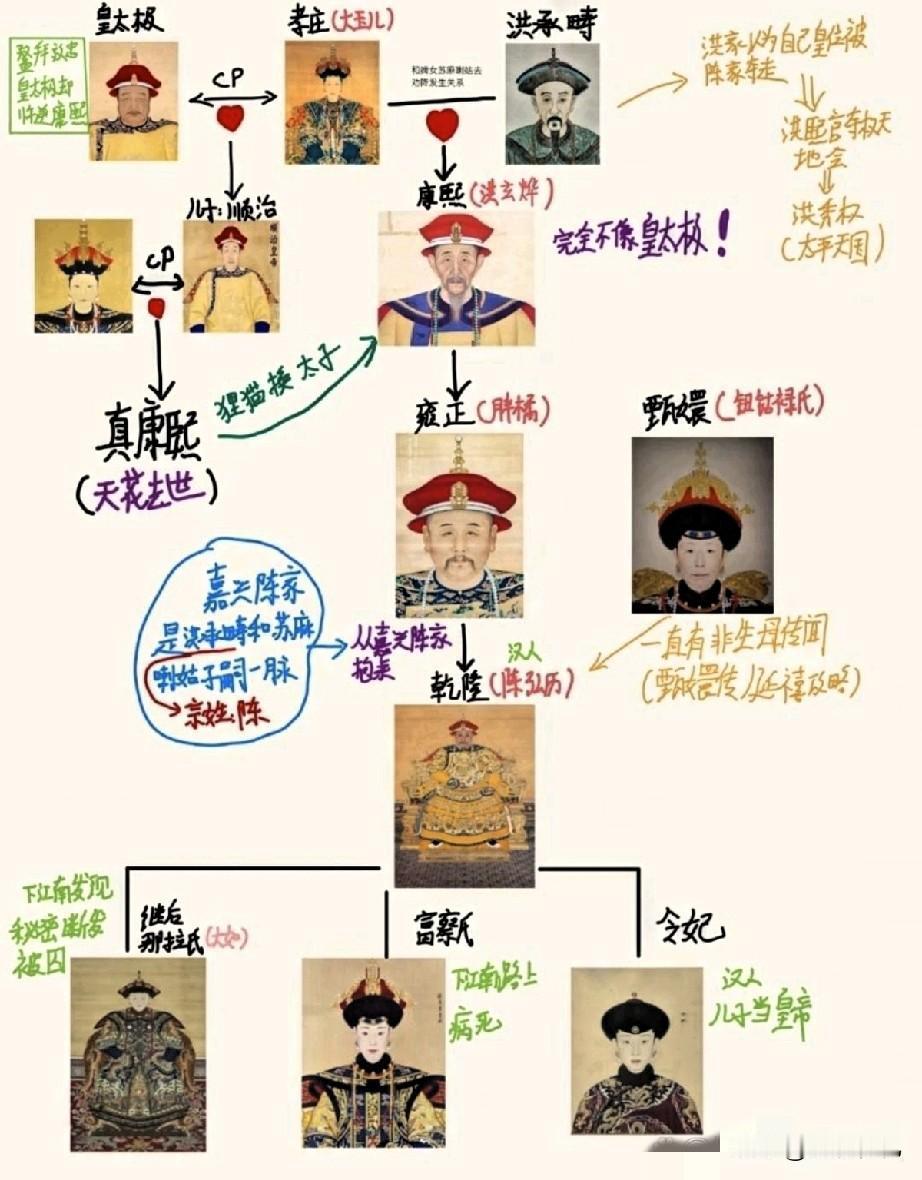1879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午睡之后,路过通房丫头卧室时与之发生关系。而就是这一次丫头便怀了孕,一年后生下一子,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谭延闿。 谭钟麟出身湖南茶陵,寒门子弟,早年家贫。屋檐下常是风雨,他靠一盏油灯苦读经史。他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仕途由此打开。那一年,他三十岁,正是胸怀抱负的年纪。 那名通房丫头,唤作李氏,是江南乡下人家的女儿。家乡闹水灾时,父母把她卖入谭府,换了两斗米活命。 李氏在谭府的日子,连正经丫鬟都不如。没有名分,没有依靠,怀着孕还要干粗活,稍有不慎就会被主母呵斥。别的妾室见她怀了孩子,更是明里暗里使绊子,生怕她抢了风头。她只能缩在府里最偏僻的小房间,白天偷偷攒点好粮食留着,晚上就用破棉絮裹着肚子,盼着孩子能平安降生。 孩子生下来那天,谭钟麟正在处理公务,听说生了个儿子,也只是淡淡说了句“知道了”,连来看一眼都没有。李氏抱着襁褓里的婴儿,眼泪掉在孩子脸上,她给孩子取名“延闿”,只盼着他能平安长大,将来不受自己这样的苦。 谭延闿长到三岁,就跟着府里的少爷们一起读书。可因为是“丫头生的”,他总被其他孩子欺负,说他是“没娘疼的野种”。有一次,一个少爷把他的书本扔在泥里,还推他摔了一跤。谭延闿爬起来,捡起书本擦干净,攥着拳头说:“我娘疼我,我将来还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这话传到了谭钟麟耳朵里,他才第一次正眼打量这个庶子。看着孩子眼里的韧劲,倒有几分自己当年苦读的影子。从那以后,谭钟麟偶尔会教谭延闿读书,可对李氏,依旧没有半分怜惜,她还是那个只能在角落里默默做事的丫头。 谭延闿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也没辜负父亲的点拨。他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五岁考中进士,而且是二甲第三,被点为翰林,比当年谭钟麟的仕途还要顺利。消息传到谭府,李氏抱着儿子的喜报,哭了整整一夜,这些年的委屈和辛苦,好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可即便儿子成了翰林,李氏在谭府的地位还是没什么变化。直到谭钟麟去世,按照封建礼教,庶出子女的母亲不能入祖坟,甚至不能和主母一起接受祭拜。谭延闿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响头,说:“我娘生我养我,辛苦一生,今日我若不能让她入祖坟,我这个儿子,还有何脸面立足于世?” 为了让母亲入祖坟,谭延闿不惜和家族长辈决裂,甚至扬言要辞官回乡。家族里的人拗不过他,最终只能同意李氏和谭钟麟合葬。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大逆不道”,也有人说他“孝顺至极”。 其实谭延闿心里清楚,他争的不只是母亲的一个名分,更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他见过母亲因为出身低微,一辈子受的委屈;见过太多像母亲一样的女子,在封建制度下被践踏、被忽视。所以后来他进入民国政府,一直主张男女平等,还推动过女子教育的发展。 回头再看李氏的一生,她就像封建时代无数底层女子的缩影。被卖入豪门,没有爱情,没有尊严,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女子,却培养出了一个影响民国历史的风云人物。这既是她的幸运,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女子的价值,只能通过儿子来体现。 而谭钟麟,作为一代封疆大吏,他有才华,有抱负,可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他对李氏的冷漠,对庶子的轻视,也暴露了他的自私和局限。或许在他眼里,李氏只是一个发泄欲望、延续香火的工具,却从未想过,这个“工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为人母的深情。 谭延闿的成功,打破了“庶出无用”的偏见,可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幸运儿又有多少?无数庶出子女,因为出身的原因,一辈子只能活在阴影里,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那些像李氏一样的女子,她们的命运,就像风中的落叶,只能随波逐流,无法自主。 直到今天,再提起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也能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个人奋斗的力量。李氏用一生的隐忍和付出,换来了儿子的成功;谭延闿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为母亲争回了尊严,也为那个时代的底层女子,发出了一声微弱却有力的呐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