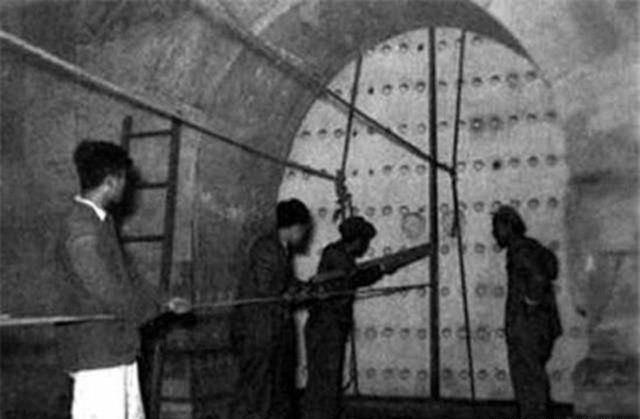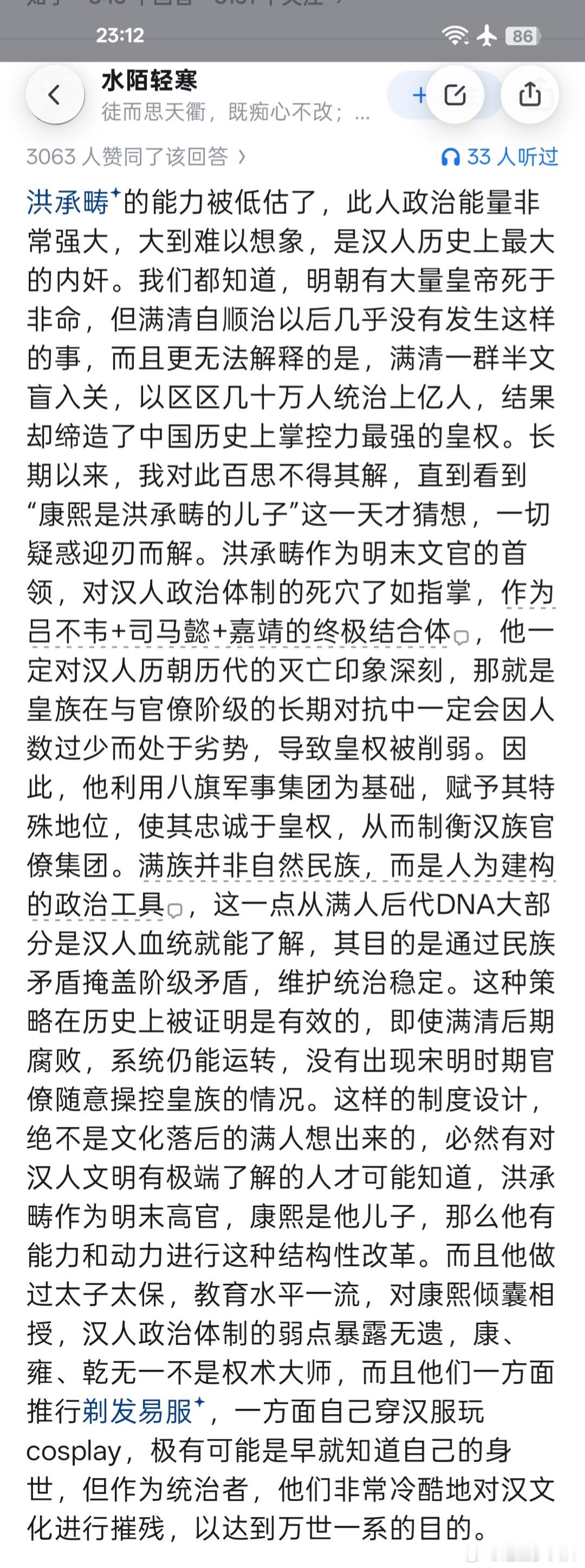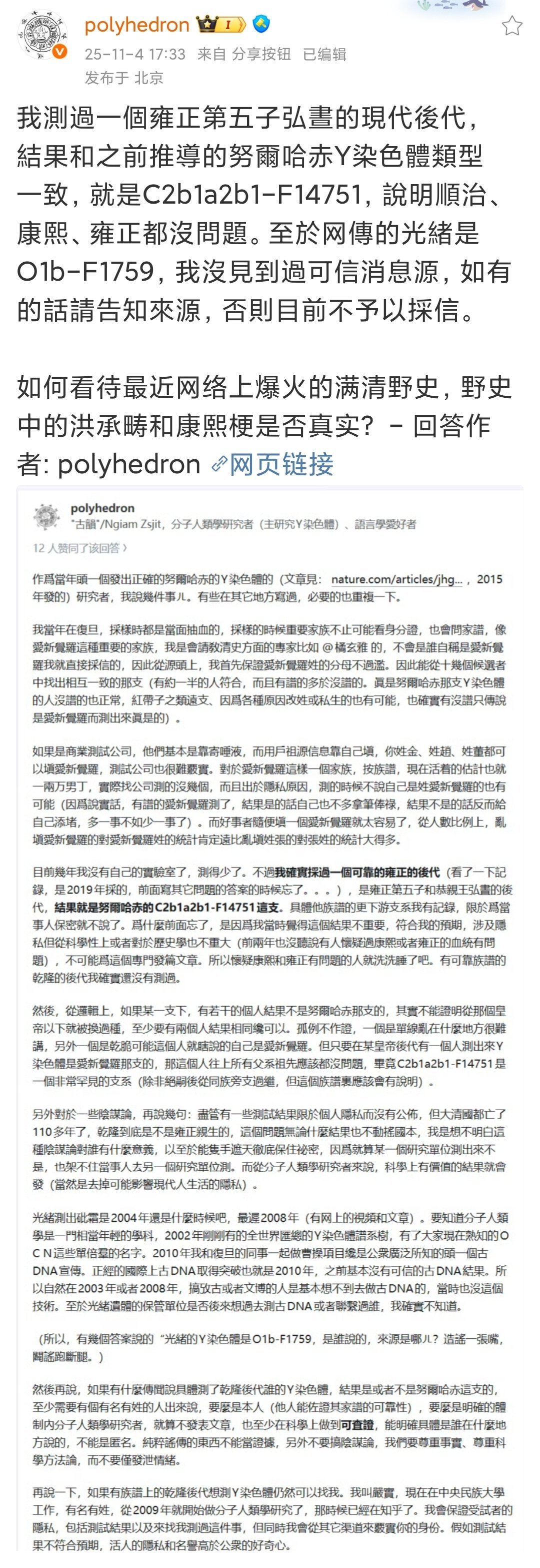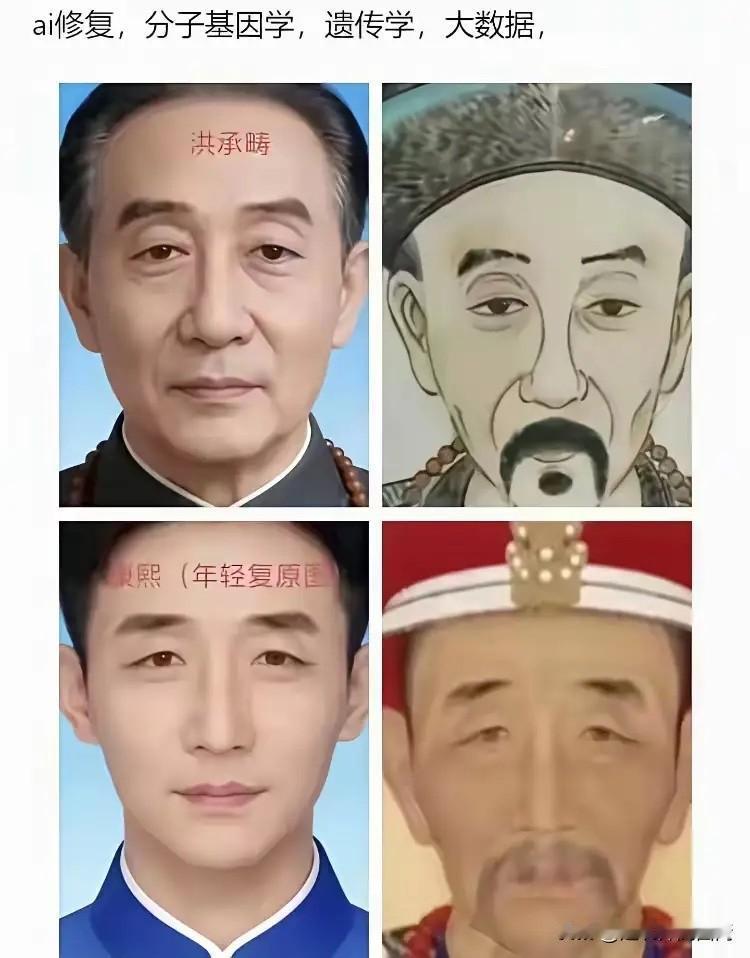皇权时代,朝廷常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当灾荒遍野、赋税如虎,百姓问一句“钱去哪了”,换来的不是答复,而是枷锁。久而久之,“责任”成了单方面的勒索——你要忠君,你要纳粮,你要送子从军,但你无权问政,无权监督,更无权问责。 崇祯元年的陕西,连续三年大旱,地里的庄稼成片枯死,尘土飞扬的路上全是逃荒的流民。老人拄着木棍踉跄前行,孩子饿得哭声嘶哑,不少人只能靠啃树皮、挖观音土续命。可县衙的赋税文书依旧按时送达,差役拿着水火棍挨家挨户催收,哪怕农户家徒四壁,也要把仅有的口粮折算成银子上交。有村民壮着胆子拦住差役,问一句“国库的赈灾粮什么时候到”,换来的却是“妖言惑众”的呵斥,枷锁直接套上脖颈,押到县城门口示众。没人敢再发问,大家心里清楚,这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赋税是皇家的供奉,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兴亡”的考量里。 赋税的去向从来都是笔糊涂账。皇宫里的琼楼玉宇要修缮,皇帝的南巡北狩要耗资,文武百官的俸禄逐年攀升,甚至宦官外戚的私库都能堆金积玉。万历皇帝派宦官到各地征收矿税,短短几年就搜刮上亿两白银,大多流入内廷供其挥霍,而同期黄河决口,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朝廷拨下的赈灾款却经过层层盘剥,到百姓手中只剩零头。乾隆年间,官员贪污成风,军机大臣和珅的家产相当于朝廷十五年的财政收入,而底层百姓却要为一两银子的赋税卖儿卖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是粉饰太平的空话,“用之于君,用之于官”才是真相。 更让人寒心的是,百姓连表达诉求的权利都没有。古代的言官制度本是为了谏言献策,可多数时候只是皇权的装饰品。海瑞写下《治安疏》,直言嘉靖皇帝“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结果被打入死牢,差点丢了性命。普通百姓更无发声渠道,明初颁布的《大诰》明确规定,百姓不得私下议论朝政,违者轻则杖责,重则斩首。有年江南大水,粮价暴涨,几个秀才联名上书知府,请求减免赋税,却被冠以“结党营私”的罪名流放边疆。当“问一句”都成了死罪,“监督”“问责”便成了天方夜谭,剩下的只有百姓的逆来顺受和王朝的自我溃烂。 并非没有清明的时期,贞观年间,唐太宗广开言路,鼓励百姓上书言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才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可这样的时代终究是少数,皇权专制的本质决定了“责任”的单向性。皇帝自称“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无需对百姓负责,也不愿受任何约束。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只要能讨好上司、搜刮民脂,就能官运亨通。而百姓,只能是这套体系里最底层的牺牲品,既要承担王朝兴盛的成本,也要承受王朝衰败的苦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是极具感召力的理念,可在皇权时代,它被扭曲成了压迫百姓的工具。真正的责任,从来都该是双向的: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担起治国安邦的责任;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家国责任。当统治者只知索取、不愿担当,当百姓的权利被剥夺、苦难被漠视,这样的“责任”只会积累矛盾,最终让王朝走向覆灭。明末的农民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百姓在走投无路后的反抗,他们用鲜血证明,单向的责任无法支撑起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 家国同心的前提,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只有当百姓的呼声被听见、权益被保障,他们才会真正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才会主动承担起兴亡之责。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任何时代,单向的“责任勒索”都无法长久,唯有相互担当、彼此尊重,才能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