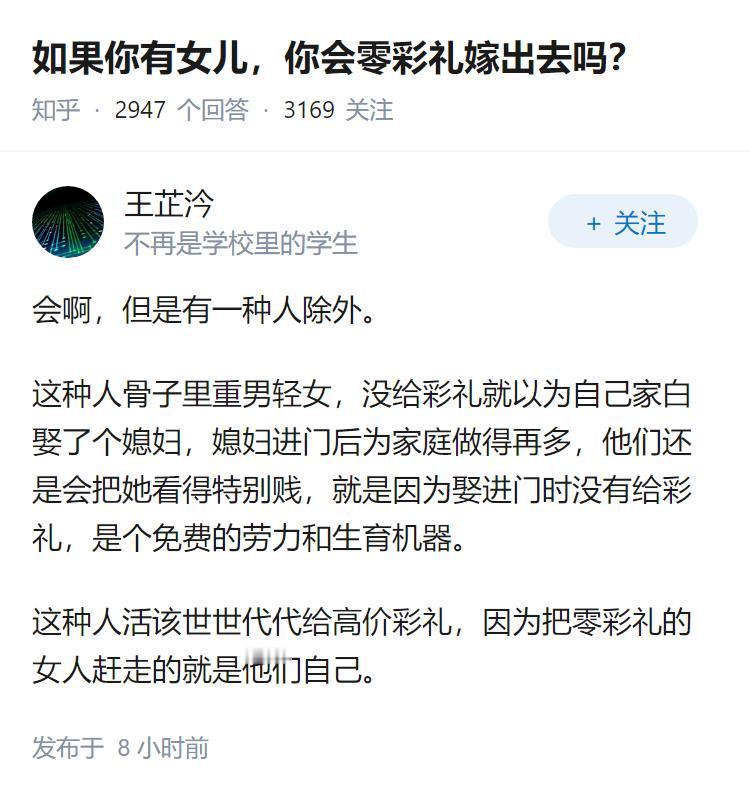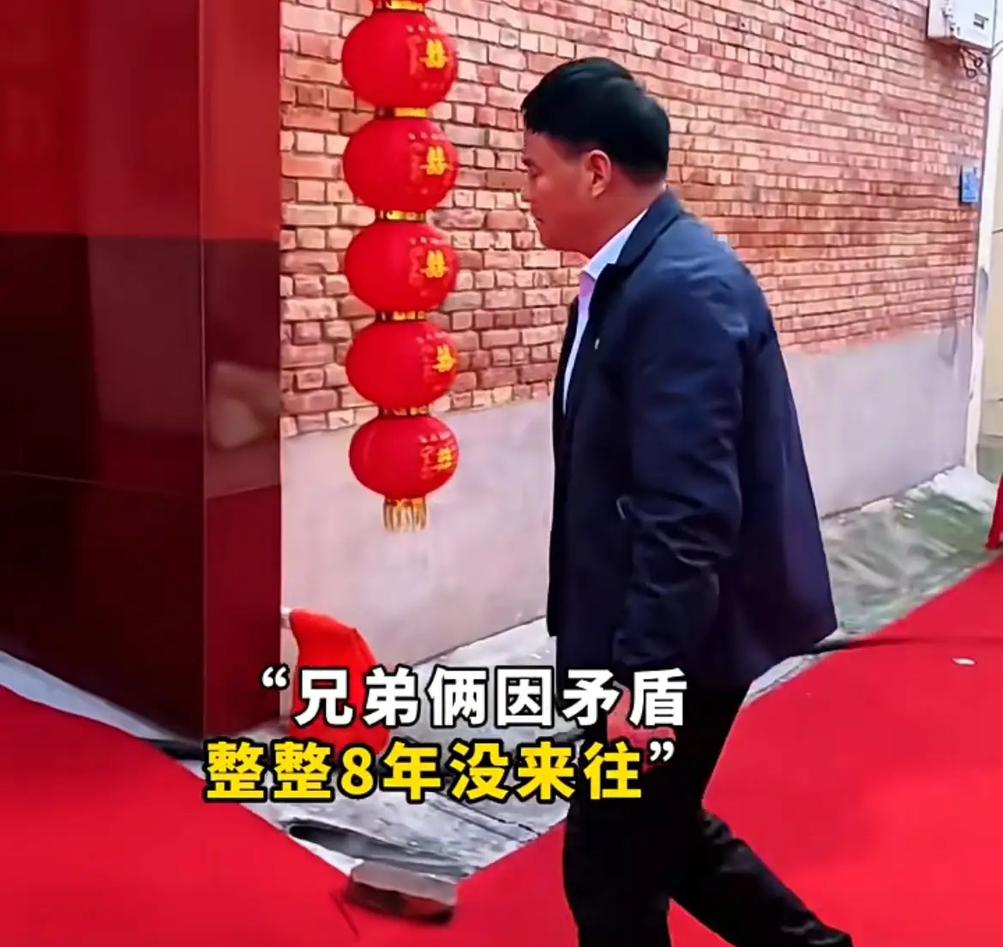出发那天,我把最后一箱行李搬上越野车时,儿子小远正蹲在楼道口数蚂蚁。他的校服袖口还沾着上周在学校走廊蹭到的粉笔灰,却没像往常那样追问“爸爸今天能早点接我吗”——过去半年,他把更多话藏进了沉默里,藏进了作业本上越来越潦草的字迹,藏进了凌晨两点我悄悄推开他房门时,还亮着的台灯。 医生说他是“适应性障碍伴焦虑状态”,建议暂时离开校园时,我正在公司开季度会。手机屏幕上跳出班主任的消息,我盯着PPT上“季度目标完成率98%”的数字,突然觉得很荒谬:我能把项目拆解到每一个节点,却没拆读懂儿子眼底的疲惫。那天晚上,我翻出他小学时的相册,照片里的小男孩举着满分试卷,追着我喊“爸爸快看,我比你上次的奖金还厉害”,再看看坐在对面扒拉米饭、一言不发的他,我做了决定:辞职,带他去徒步。 有人说我疯了,“稳定的工作说丢就丢,孩子的学业怎么办”;也有人劝我“别太惯着,送回学校适应适应就好了”。可他们没见过,小远在景区看到溪流时,会蹲下来看小鱼游半小时,眼里有我很久没见过的光;没见过他在山顶主动跟陌生驴友打招呼,分享我们带的面包;更没见过某天晚上,他靠在帐篷边跟我说“爸爸,今天走的路比上周在教室里坐一天还轻松”。 我不是要逃避教育,更不是要带他“躺平”。我只是想告诉他,人生不是只有“上课-考试-升学”这一条直线,就像我们徒步时会遇到陡坡,会绕远路,甚至会因为暴雨暂停一天,但只要朝着前方走,总能看到新的风景。有次走累了,他坐在路边哭,说“我不想走了”,我没催他,只是陪他坐着看远处的山。后来他自己站起来,说“爸爸,我们再走一段吧,说不定前面有卖冰棍的”——你看,他不是没韧性,只是之前的“赛道”,没让他找到坚持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千多里,小远的皮肤晒黑了,鞋子磨破了两双,却愿意每天晚上跟我聊当天的见闻,甚至会主动记日记。我不敢说这次徒步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知道,这段路会成为我们俩心里的光。未来他或许还会遇到难走的路,还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他会记得,曾经有段日子,爸爸陪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过了千里山河,也一步一步地,重新靠近了彼此。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需要“被拯救”,而是我们作为父母,需要放下“标准答案”,陪他们慢慢走。毕竟比起“考了多少分”,我更想知道“他今天开不开心”;比起“能不能跟上别人的脚步”,我更在意“他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条路还没走完,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重新找回了那个愿意跟我分享小事的儿子,也重新理解了,所谓“父爱”,从来不是替他规划好一切,而是他想走的时候,我能陪在他身边。
我一同学是她父母领养的,她26岁的时候,养母因病去世,她只剩下养父一个亲人。她从
【3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