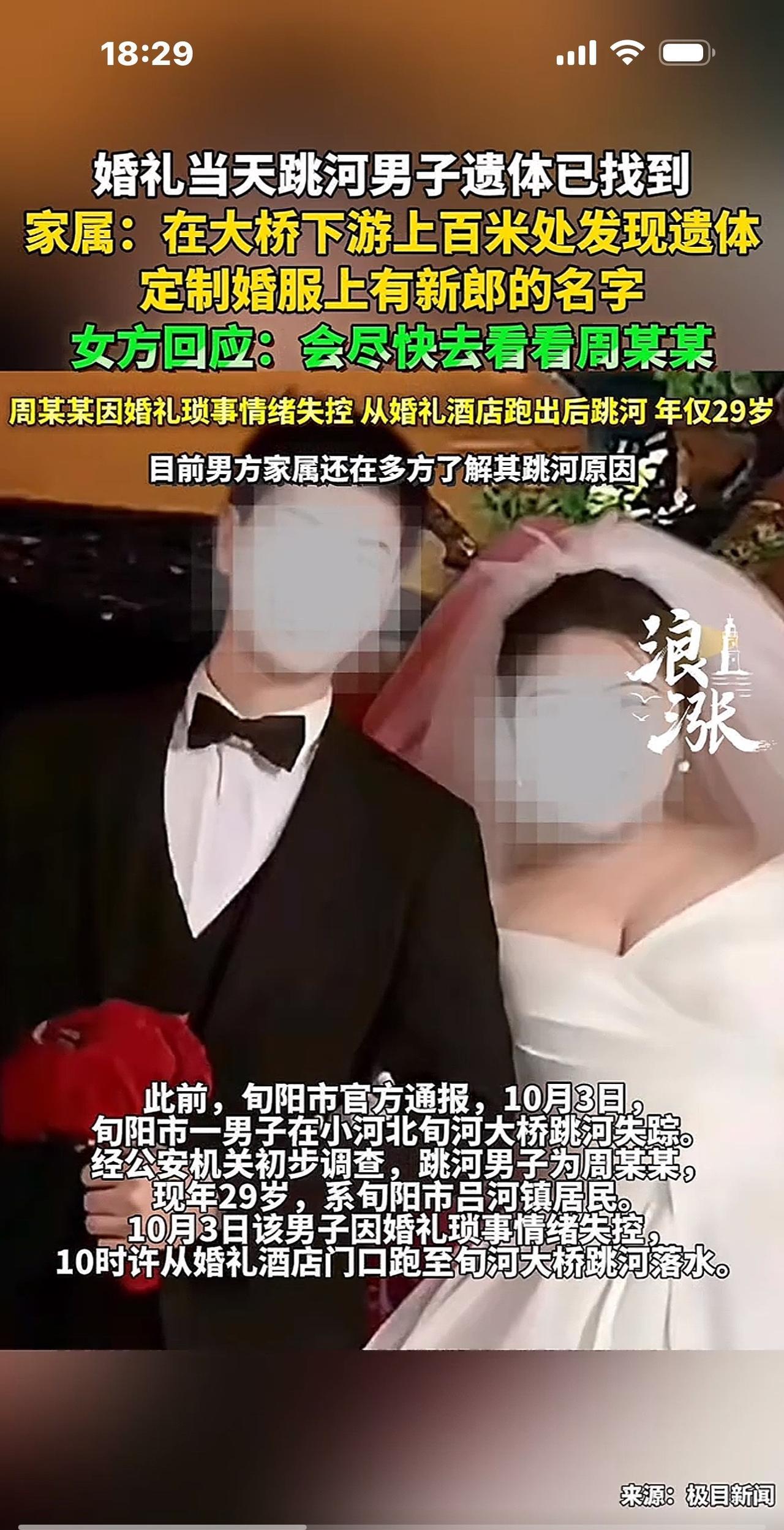安乐死放开,谁会先“消失”?中国的选择很慎重。 有人说,死亡是人的最后一项权利,但当这项“权利”变成一股看不见的推力,逼着穷人、老人、病人走向终点时,它还是权利吗? 在加拿大,有个51岁的女人,不抽烟不喝酒,却因为对化学气味严重过敏,申请了安乐死,她不是绝症患者,只是想找个“能呼吸的地方”住下,可等了两年都没排上廉租房名额。 她说:“我不想死,但我不能活得这么难受。”最后,她走了,不是因为她不想活,而是这个社会没给她活下去的条件。 在荷兰,曾有个阿尔茨海默症老太太,签了安乐死同意书,可执行那天,她忽然挣扎着站起来拒绝,医生和家属却联手按住她,注射完成。 医生后来说:“她签过字。”可问题是,她站起来反抗了,那一瞬间,她还想活。 这类案例越来越多,有的穷人交不起房租,有的老人生病没人照顾,有的年轻人患了抑郁症找不到出路,他们不是主动选择死亡,而是被“合理”地推进了终点线。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安乐死,原本是为了解决极端痛苦的手段,现在是不是被“用歪了”?它成了社会系统失灵的一块遮羞布,让那些“没资源活下去”的人,选择“体面地消失”。 在某些国家,安乐死已经不是“最后的选择”,而成了“最便宜的方案”。 很多人说,中国在这方面太保守,几十年过去,还是没有立法,可如果你回头看看那些“被安乐死”的人,就会明白:有些事,不是晚一步,而是稳一步。 早在1986年,中国就有了第一起安乐死的司法案例,王明成为了不让母亲忍受肝癌痛苦,和医生一起实施了安乐死,结果双双被起诉。 六年后才被判无罪,可讽刺的是,等他自己得了癌症,再次申请安乐死时,没人敢给他“帮最后一把”,他只能痛苦地熬到生命尽头。 这起案件之后,中国社会对安乐死的讨论就没停过,但每次都卡在一个点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机制,保证“不是因为无助才选择死亡”? 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医疗、养老、陪护都保障不了,那所谓的“选择死亡”,到底是不是被逼无奈?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孝”,不仅仅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让老人“无声无息地走”。 这不是情怀,是中国数千年来家庭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根,你可以说它“拖慢了脚步”,但你也得承认,这种慎重,是有底气的。 国家卫健委也不是没讨论过安乐死立法,但每次都得出一个结论:争议太大,社会准备不足,立法风险高,换句话说,现在推这件事,可能不是“进步”,而是“冒险”。 而且,中国的老人不是加拿大那样一个人住一间屋子,没人管;也不是荷兰那样医生说了算,老人的一生,牵着一大家子人,涉及伦理、法律、情感多个层次,不是一个“签字”就能解决的。 既然安乐死走不通,中国就真的无计可施吗?当然不是,这几年,安宁疗护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院、政策甚至医保体系里,它不是让人“早点走”,而是让人“好好走”。 什么叫“好好走”?不是在病床上痛得打滚,也不是插着管子熬成植物人,而是减轻痛苦、保持尊严、有人陪伴、能说再见。 有一项调查,使用了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满意度超过90%,家属满意度甚至更高,这说明,不是所有人都想“快点结束”,很多人只是想“别太痛苦”。 从2017年试点到现在,已经有90多个城市开始布局安宁疗护,安徽淮北甚至把它纳入医保,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 虽然目前全国不到400家医院设有专门科室,但趋势是明确的,中国在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补上那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短板。 而且相比安乐死那一针的“干脆”,安宁疗护更讲究“过程感”,它是一种软着陆,不是推你跳下去,而是拉着你慢慢走到终点。 这也体现出中国式的底层逻辑:让人活得有尊严,也死得有尊严,不是靠一纸同意书,也不是靠医生的判断,而是整个社会对生命最后阶段的集体呵护。 安乐死的初衷,是为了解脱极端痛苦,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它慢慢变成了一种“制度性放弃”。 当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养老体系、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时,安乐死就成了“最省事”的解决办法。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保活着的人有尊严、有资源、有希望,那“自由选择死亡”就是一句空话,人不是不怕死,而是怕“没人管死”。 对比之下,中国宁可慢一点,也要把这些问题想透,把制度补上,不是不尊重选择,而是理解选择背后的无奈。 死亡不是终点,放弃才是终点,而一个国家的底线,不该是“让你体面地消失”,而是“尽可能让你不必消失”。 选择安乐死,不该是因为活着太难,面对全球老龄化、资源紧张和医疗压力,中国没有急着给“死亡权利”开绿灯,而是转身去修补“活下去的通道”。 这条路也许慢,但更稳,因为真正的尊严,不在于“怎么死”,而在于“还能不能选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