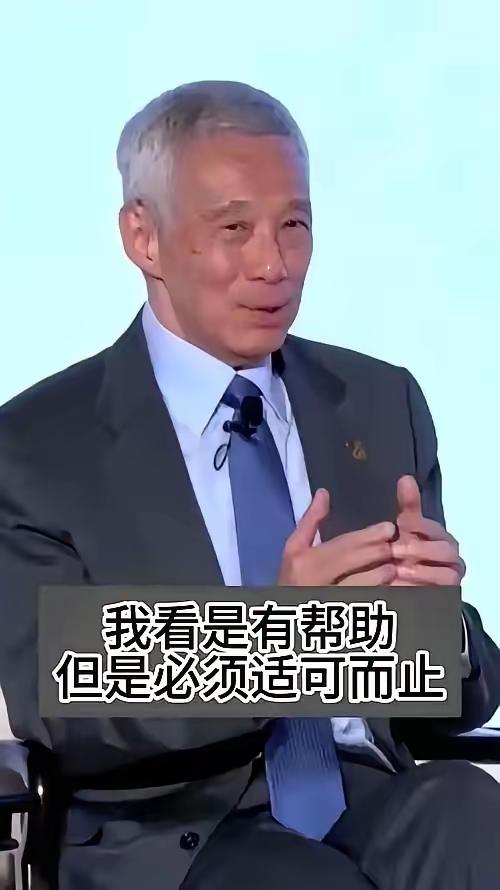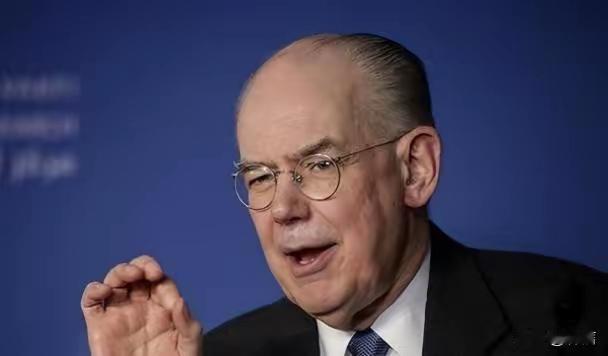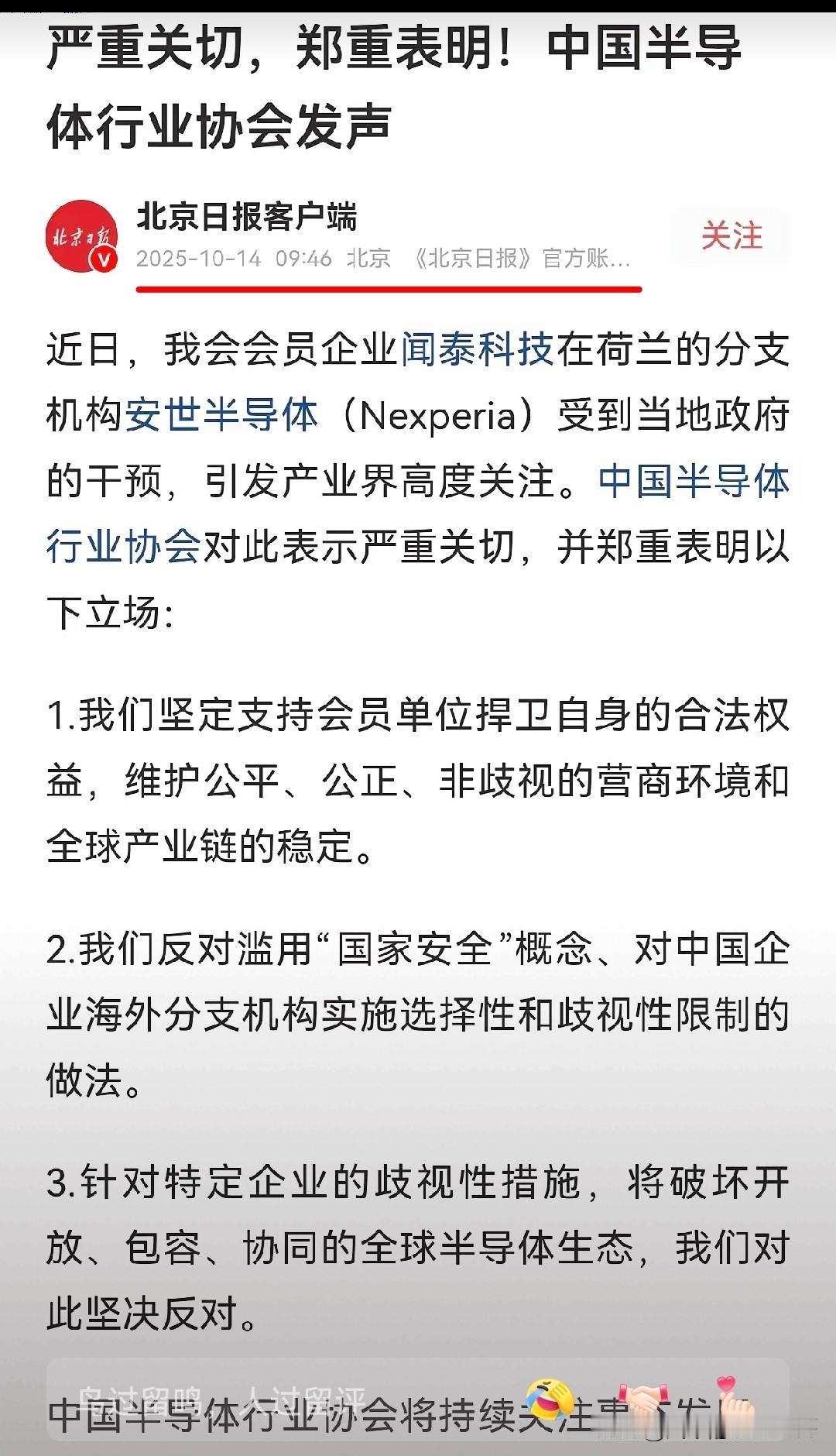一个人能无私到什么程度!法国一男子来到中国40年时间,竟然无偿资助了70多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然是,他所资助的学生,学有所成后必须回到中国! 西安,古城墙的青砖在冬日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间简陋的教工宿舍里,暖气片时好时坏,一位清瘦的法国老人正趴在桌前,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窗外,学生们的欢声笑语隐约传来,而他笔下的文件,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遗体捐献志愿书》。 他叫米里拜尔,中文名米睿哲。 签完字,他小心翼翼地将文件折好,放进一个旧信封里。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只有一行娟秀的法文:我是中国的孩子。 这个出身法国空军司令世家的男人,此刻做出的决定,连他远在巴黎的亲人都无法理解。可对于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他来说,这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归宿。 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一年,米睿哲放弃了家族为他铺就的平坦大道,背着简单的行囊,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了刚刚向世界敞开些许缝隙的中国。他落脚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成为了一名法语教师。 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教室里,他看到的是一双双充满渴望与求知欲的眼睛。但他也看到,这些聪慧的学生,许多人连一本像样的法汉词典都买不起。课本上印着的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对他们而言,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的梦。 一次课后,一个叫张华的学生怯生生地问他,法国的大学是不是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有听不完的讲座和看不完的书。米睿哲看着这个连衬衫袖口都磨破了的年轻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想去吗?” 张华的眼睛瞬间亮了,但随即又黯淡下去:“米老师,我……我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齐。” 米睿哲没再说什么。几天后,他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张华手里,里面是他几个月的津贴,足够支付申请费和路费。他只说了一句:“去试试,钱不够我再想办法。” 为了“想办法”,米睿哲开始过上了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将自己在巴黎的祖宅出租,用租金作为资助学生们的“基金”。在西安,他住在学校分配的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那满满一书架的书。 他身上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是面条和馒头,连买块肉都要盘算许久。 有人不解,劝他对自己好一点。他总是笑着摆手:“我的饭不重要,学生们的未来才重要。”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有才华却家境贫寒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飞向了世界的另一端。 四十多年间,他倾尽所有,先后资助了七十多位中国学生前往法国、英国、德国等地深造。 他从不要求这些学生给予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在每一个学生踏上异国求学之路前,他都会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他会认真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郑重其事地提出他唯一的,也是最坚定的要求: “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中国需要你们。”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米睿哲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他亲眼见过西部山区的贫瘠,也了解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高精尖人才的迫切需求。 他希望这些他亲手送出去的“种子”,能在海外吸取最先进的知识养分,然后回到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这些“种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中,有人成为国内顶尖大学的教授,桃李满天下;有人投身中法贸易,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还有人默默扎根西部,将所学奉献给最需要的地方。 米睿哲在学校执教数十年,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工资。校方多次将工资条送到他手里,都被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他说:“我有津贴,够用了。把这些钱省下来,给学校添置设备,或者给更困难的学生当助学金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用途、数额和方式。米睿哲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悉数“捐赠”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时间流转,当年的翩翩青年已是耄耋老人。 2014年,他当选“中国好人”,站在领奖台上,他依旧穿着那件旧衬衫,言语朴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当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依然是如何将自己最后的一切都留给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他瞒着所有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志愿将遗体用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教学科研。 他觉得,这样才算真正地留在了中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中国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5年,米睿哲在西安与世长辞,享年96岁。他的葬礼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们站满了告别厅,每个人都泣不成声:“米老师,我们都回来了。” 米睿哲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财产,没有一砖一瓦。但他留下了七十多位学成归国的栋梁之才,留下了一段跨越国界、血缘和文化的无私大爱。他用一生诠释了,有一种伟大,它不追求财富与名望,只在于点燃希望,并看着希望照亮自己的故乡——哪怕那个故乡,并非自己出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