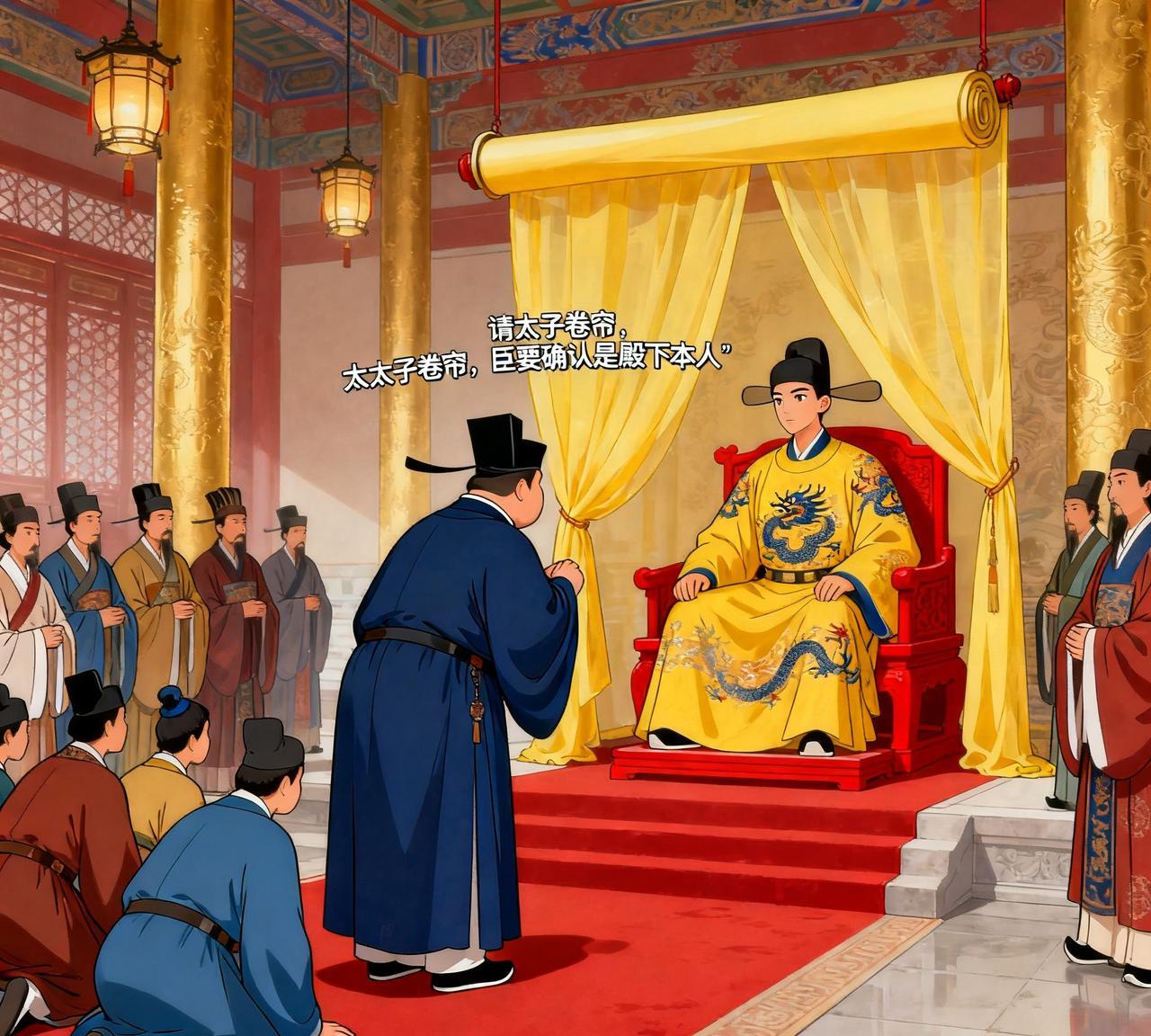646年,病重的李世民下了道命令:处死宰相刘洎。刘洎临死前想写奏疏辩解,却被拦住了。 要知道,李世民早年曾夸刘洎 “鲠亮有谋”,说他正直又有谋略。可就是这样一位宰相,最后却落得如此憋屈的下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事? 先说说刘洎的背景。他是荆州江陵人,属于南方士族。早年归顺唐朝时,曾劝降岭南五十多座城,靠战功一步步往上走。 但唐初朝廷的核心力量是关陇集团,这些人大多是皇亲国戚或世代显贵,靠门第出身就能做官。刘洎 “以战功换仕途” 的路数,从一开始就和他们格格不入。 贞观七年,刘洎因为直接指出尚书省办事效率低,被升为给事中。这让他更敢说真话,可也让不少人记了仇。 到了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朝廷里爆发了太子之争。刘洎站在了魏王李泰这边,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支持晋王李治。 最后李治被立为太子,刘洎自然成了长孙无忌等人眼里的 “异己”。这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隐患。 真正让刘洎陷入危机的,是贞观十九年的一次对话。 那年李世民要亲征高句丽,安排刘洎、高士廉、马周辅佐太子李治监国。临走前,李世民特意叮嘱:“国家安危全靠你们,一定要谨慎。” 可刘洎却回答:“要是大臣有过错,我会直接处死他们。” 这句话让李世民当场警惕起来,他告诫刘洎:“君主不保密会失臣,臣子不保密会丢命。你性格太直又强硬,恐怕要因此出事。” 当时没人想到,这句话会在三年后成为杀刘洎的 “伏笔”。 贞观二十年三月,李世民从辽东打仗回来后就病了,身上还长了毒疮。刘洎和马周进官探望后,出来对其他官员感叹:“皇上病得很重,真让人担心。” 这本是忧国忧民的话,却被褚遂良改了说法。 褚遂良对李世民说,刘洎讲的是 “只要辅佐太子行伊霍故事,把有二心的大臣杀掉,国家就不用愁”。 “伊霍故事” 说的是西汉时伊尹、霍光废立君主的事,在帝王听来,这就是大逆不道。李世民当即传召三人对质。 刘洎把实情说了,还请马周作证。马周的证词和刘洎完全一致,但褚遂良一口咬定 “刘洎确实说过这话”。 最后,李世民选择相信褚遂良,下旨赐刘洎自尽。 这里要说明的是,后世对褚遂良的动机有争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褚遂良是忠直之臣,和刘洎没私怨,可能是修史的许敬宗因私怨抹黑他。 但也有说法认为,两人虽无私怨,却因支持不同皇子,褚遂良是为了巩固李治的地位才这么做。 不管褚遂良的动机是什么,刘洎之死的深层原因,其实是李世民晚年的权力焦虑。 此时的李世民,早已不是早年 “从谏如流” 的明君。他亲眼见过太子李承乾谋反,也经历了魏王李泰夺嫡,对 “强臣辅佐弱主” 的局面特别警惕。 而且刘洎是南方士族代表,和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集团本就有隔阂。在李世民看来,刘洎之前说 “诛杀异志者”,就是不好控制的信号。他担心自己死后,刘洎凭着宰相权力专权,影响李治掌权。 这种焦虑,从李世民对马周的处置就能看出来。马周为刘洎作了证,李世民却没追究他,反而升他做了中书令。 这种 “选择性信任”,说白了就是李世民晚年的心态:为了权力平稳过渡,哪怕牺牲真相也无所谓。 《资治通鉴》里就记载:“皇上晚年越来越信谗言,房玄龄、李靖因谗言被罢官,刘洎、张亮因谗言送命。” 刘洎死了之后,朝堂上一片沉默。很多大臣明知他冤,却因为害怕不敢说话。太子李治曾想求情,也被李世民驳回:“这不是太子该管的事。” 直到三十年后,武则天临朝掌权,刘洎的儿子刘弘业上书申冤,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可那时,贞观盛世的光彩早就没了,满是权力斗争的阴影。 后世史家评价刘洎之死,大多会提到 “君臣关系异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把天下重任托付给一个人,对权力和宠信不能不谨慎。” 但更关键的是,就算在 “贞观之治” 这样的盛世,权力斗争的残酷也从没消失过。李世民晚年对 “强臣” 的猜忌,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不愿分享权力。这种排他性,最终让刘洎成了牺牲品。 还有个细节特别让人唏嘘:刘洎临死前想要纸笔上书,监刑官没给。据《旧唐书》记载,他最后只能喝下毒酒死去。 这种 “死都不能说话” 的结局,像是对专制皇权的讽刺。当君主宁愿信谗言,真相就没了立足之地。 而刘洎死后,李世民又对监刑官发火,这更像权力游戏结束后的作秀 —— 他要的从来不是真相,只是确保李治能顺利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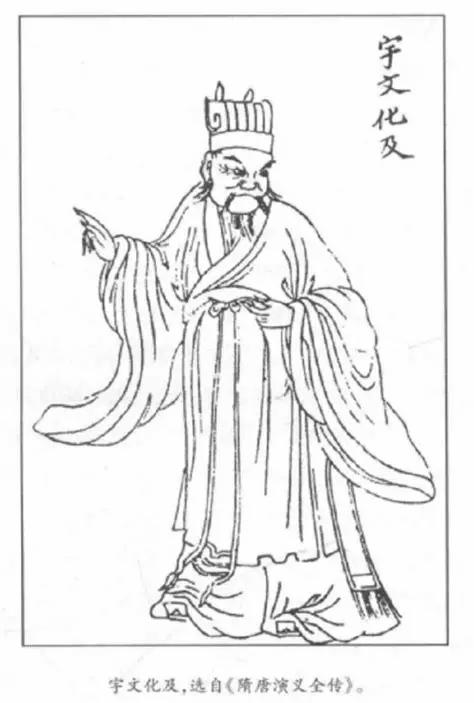

![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吃瓜]](http://image.uczzd.cn/514115608926668554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