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的时候,她被丈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 丈夫拉开弓,一箭射向她的肚子。 这个丈夫,是她亲爹——努尔哈赤——送给她的。那年她才14岁,被当成一个“和平礼物”,送给了政敌布占泰。 你以为这是最惨的吗?不。 四年后,她爹终于带兵灭了她丈夫全族,把她“救”了回来。 当时,她又怀孕了。 她爹看着憔悴的女儿,没多说一句话,转手就把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当作战利品,“赏”给了52岁的开国功臣额亦都。 —— 14岁,放在现在,才上初二,还在为数学题掉眼泪,她已经被塞进花轿,送到敌人的床榻。她的名字,史书只写“和硕公主”,没有闺名,像一件没贴标签的货物。布占泰接过她,也就接过一份短暂的休战协议。新婚夜,红烛高照,她瑟瑟发抖,布占泰却把她按在膝上,当着部将的面说:“努尔哈赤的种,也不过如此。”一句话,把她钉进耻辱柱,也钉进政治的缝隙。 怀孕那年,她16岁,身子还没长开,肚子却先鼓起来。布占泰听信巫言,说“女真骨血,射其子可破敌”,于是有了绑柱、扒衣、拉弓那一幕。箭簇飞来,她闭眼,肚子一紧,血顺着大腿根往下淌,像红河。孩子没保住,她也去了半条命,整整三天,高烧得说胡话,嘴里只喊一个字:“娘……”可她的娘,早死在部族火并里,连骨灰都没处找。 四年后,努尔哈赤的铁骑终于碾到乌拉城下。布占泰兵败,被一刀砍下头颅,她的噩梦却没完。爹来了,她以为自己得救,抱着微微隆起的小腹,跪在尘土里,眼泪混着鼻涕。谁料亲爹只扫了她一眼,像扫一件破斗篷,转头对身边的额亦都说:“这丫头你带去,肚子里那块肉,也算你的。”52岁的老将军,战功赫赫,却也是个刚死了老婆的男人,接过她,像接过一柄宝剑,抱拳谢恩:“臣一定善待。”她听着,胸口像被塞进一块冰,连哭都忘了。 额亦都的府邸,金碧辉煌,对她却是另一座牢笼。老将军夜里覆在她身上,胡茬扎得她生疼,嘴里喷着酒气:“你爹说了,你是福星,给我生个儿子,保我家族昌盛。”她麻木地承受,眼泪顺着耳鬓流进头发,湿了一枕。第二天清晨,她却得强撑着身子,去给老将军端茶,笑靥如花,因为婢女告诉她:“主子不开心,你日子更难过。”她学会把苦嚼碎,咽进肚里,连骨头渣都不吐。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额亦都大喜,摆宴三天,她却像被抽了脊梁,瘫在榻上,眼神空洞。她给孩儿取名“遏必隆”,意为“止住悲伤”,可悲伤哪有闸口?她日夜抱着孩儿,像抱着一块浮木,生怕一松手,自己就被淹死。老将军年事渐高,没几年病逝,她又被当成“遗孀”,继续留在府里,像一件传家宝,被擦拭、被展览,却再没人问她冷暖。 后来,遏必隆长大,成了康熙朝四大辅臣之一,她也被封为太妃,享尽荣华。可宫女们常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廊下,望着南方发呆,手里攥着一块旧帕子,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红花——那是她14岁出嫁前,偷偷绣给娘的,一直没机会送出。她活到了70岁,临终前,她把帕子交给儿子,只说了一句:“娘想回乌拉,看看山,看看水。”可她的骨灰,还是被葬在盛京郊外,和额亦都合穴,政治正确,礼仪周全,只是再没机会去看一眼故乡的河。 史书翻到这一页,字迹冰冷,我却觉得烫手。她是谁?是公主,是礼物,是战利品,是母亲,却从来不是她自己。她的命运,被父亲、丈夫、儿子,一层层套上枷锁,连死后的坟,都得挨着“赐予”她的男人。个人?不存在的。她只是一枚被博弈的棋子,棋局结束,棋子被随手扔进盒里,连名字都懒得记。 今天,我们谈“女性独立”“原生家庭伤害”,听起来时髦,可回望她,才发现什么叫“顶级原生家庭PUA”——亲爹把你送人,亲夫把你当靶子,亲儿子都救不了你。更可怕的是,这种“工具人”逻辑,并未远去。职场里,被当成“背锅侠”;婚姻里,被当成“彩礼交换物”;家庭里,被催着“生儿子继承皇位”,只不过方式更隐蔽,说辞更漂亮,本质却一样:你是手段,不是目的。 写完她的故事,我关掉电脑,去楼下转了一圈。夜风有点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自由的味道。至少,我可以决定自己走哪条路,回哪个家,爱什么人,不被当“礼物”送来送去。这口气,是她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女人,用一生换来的。愿我们珍惜,也愿我们记得:先有“我”,才有“我们”;先是人,才是女人。别再让任何名义的“父亲”“丈夫”“儿子”,把谁变成下一枚棋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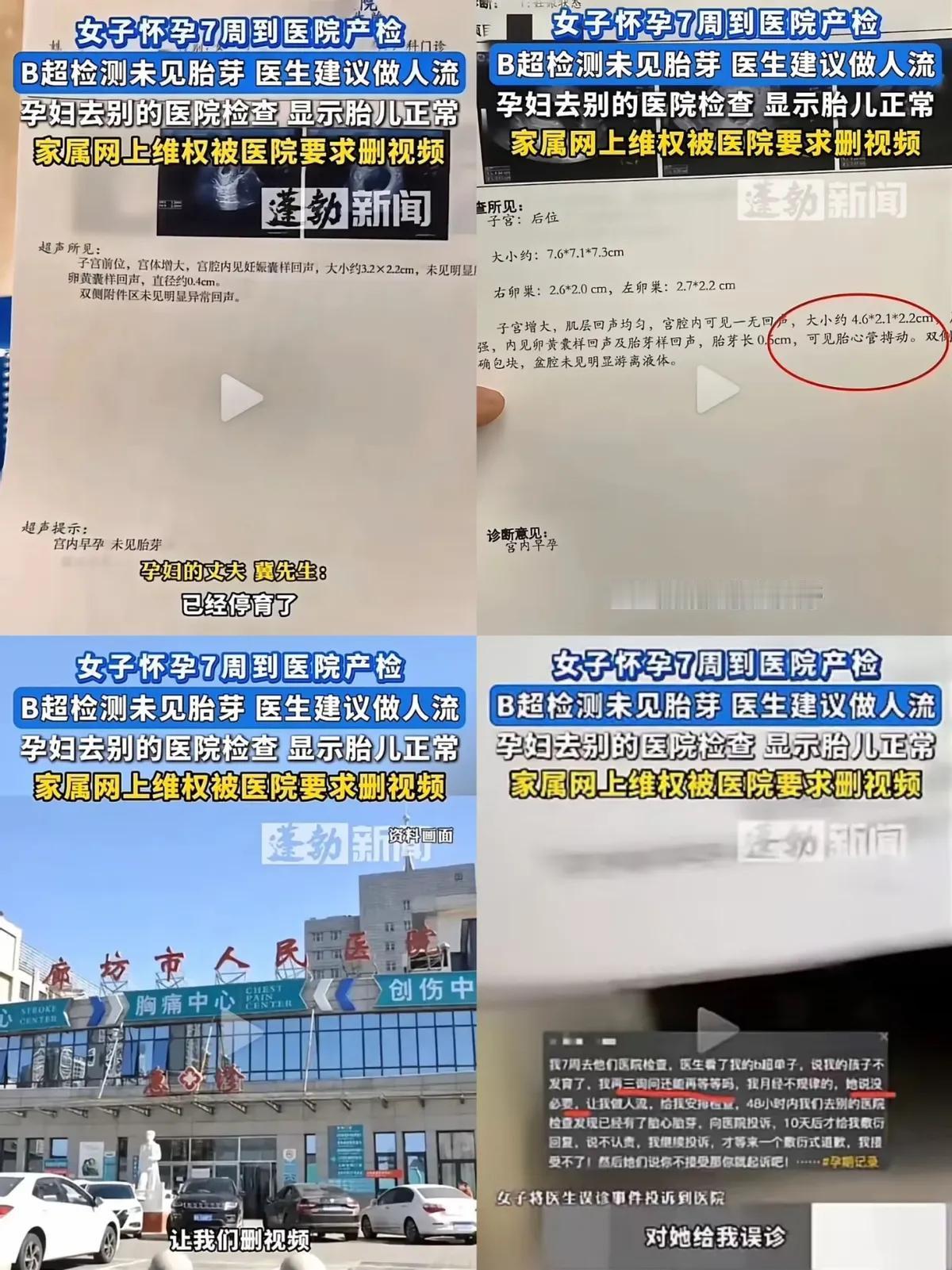


雷鸣洞府君
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以旧时蛮夷陋俗论今之社会,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