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8岁的耿保国不顾妻子反对,借遍亲朋好友又咬牙贷款几十万,终于凑够了120万买下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明清古宅,此后他又把后半辈子的时间,都放在了修缮复原这座老宅上面,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和这座宅子近况如何? 120万,在1997年能在北京二环里买两套三居,耿保国却把它砸进一堆“烂木头”里。老婆气得直哭:“你这是把家往火坑里推!”朋友更直接:“老耿疯了,钱扔水里还能听个响,扔这破院里连个回声都没有。”他咧嘴一笑:“你们等着看,这木头能开口说话。” 说话容易,张嘴难。宅子空了几十年,燕子在里面做窝,蛇在梁上脱皮,一脚踩下去,地板嘎吱嘎吱响,跟鬼片现场似的。耿保国先当起了“拆迁队长”,把半人高的野草一根根拔干净,手上扎得全是刺;又当起“木工”,烂掉的梁一根根换,新的不够,他就跑周边村里收老料,看到谁家房梁要拆,软磨硬泡买下来,回来一比划,尺寸不对,再锯再刨,木头渣子飞一脸。最惨的是钱,120万只够“止血”,真要让宅子“回春”,得往无底洞继续扔。他把家里积蓄掏光,儿子上大学的生活费都砍一半,女儿想学钢琴,他拍拍脑袋:“先弹桌子练手感。” 最头疼的是技术。400年前的榫卯,错一毫米就合不上,他跑去北京故宫、山西博物院,站在展柜前盯结构,一站一天,脚面肿得鞋都脱不下。回平遥,他把老师傅请到工地,管吃管住,工资按天算,人家嫌慢,他陪着熬,熬到凌晨两点,老师傅撑不住先去睡,他蹲在院里,拿锉刀一点点磨榫头,月光照在瓦当上,像给他打手电。第二天师傅一看,榫头严丝合缝,直挑大拇指:“老耿,你这手艺能进宫了。” 宅子慢慢“长肉”了:影壁上的砖雕重新冒头,门口石狮子的牙齿被补齐,二楼漏雨的大洞被一块块青瓦盖住。耿保国却越来越瘦,1米75的个子,不到120斤,胡子一把,远看像从明代穿越来的老工匠。他自嘲:“这叫配套减肥,省钱又健身。” 2003年,平遥申遗成功,古城房价噌噌往上涨,有老板开价800万要买他的宅子,他摇头:“卖了我住哪?”又有人出主意:“改成酒吧,一晚门票上万。”他笑得更狠:“让老祖宗蹦迪?我怕雷劈。”他继续埋头干,把宅子当成大玩具,一块砖一片瓦地抠,抠了整整26年。如今再看,宅子七进七院、祠堂、绣楼、花园、影壁全活过来了,青砖泛着光,椽头画着彩,比乔家大院还气派,却少了商业味儿,多了一股子“人味”——他自己住,自己扫,自己当讲解员,一天最多接待20人,还全是提前预约。门票?不要,临走他送每人一张手写书签:“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去年我去平遥,跟着他转了一圈。午后阳光照在影壁上,砖雕人物像要跳出来。他摸着一扇门板,自言自语:“这木头比我老,可它还能再站400年。”我问他图啥,他咧嘴:“图个叫板——叫板时间,叫板遗忘。我活不过它,可我能让它记得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买的不是宅子,是一张“传票”——把自己传成历史的一部分。 耿保国的故事,说白了,就是“倔”字的实体化。有人倔钱,有人倔官,他倔的是一口气:祖宗的东西,不能倒在我手里。这口气,让他从“耿疯子”变成“耿爷”,也让400年的老宅重新开口说话。如今他70多岁,每天早上5点起床,扫院子、擦门窗,像照顾老父亲。夜里,他躺在正房的火炕上,听瓦片滴雨声,说那是“明代的声音”,比任何催眠曲都香。 26年,他把120万“砸”成一座城,也把“穷”日子过成了“富”历史。有人问他值不值,他反问:“让一块砖记住你的名字,你说值不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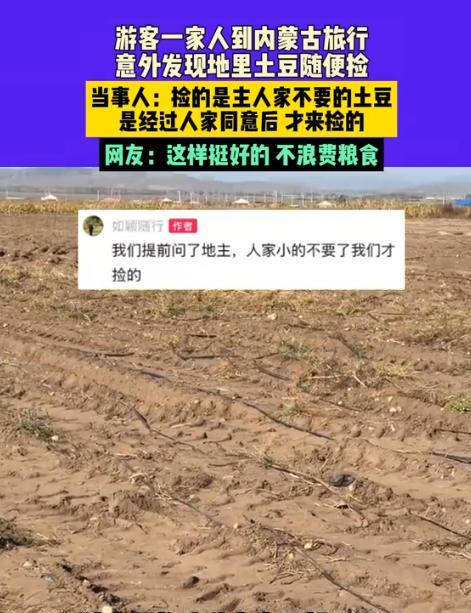


曾经沧海
赞,老人家应该收点修缮的钱